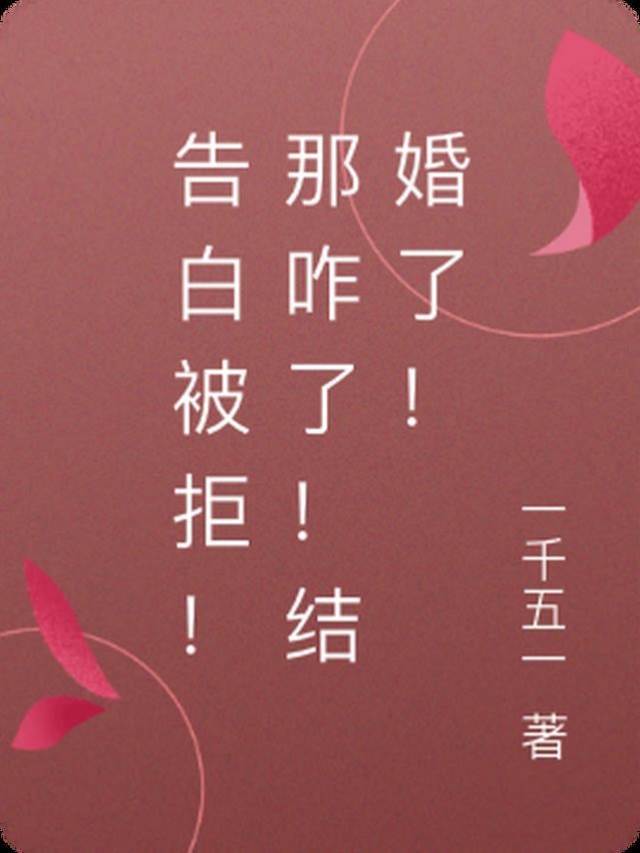《償願》 第33章
煙花表演結束後,梁總就帶著妻告辭。
小姑娘窩在徐晏清的懷裏,已經昏昏睡了,梁總笑著接了過來,神寵溺地親了親兒的頭,而後才抬起頭開口道別:“那我們就先走了,徐總、祁小姐,新春快樂。”
徐晏清也點了點頭,回了句:“新春快樂。”
而後,一家三口便轉走了人海。
直到看不見那三抹影,徐晏清才收回了視線,偏頭看過去的時候,卻發現祁願的目還定格在人海裏。
定定地站著,江風從後來,將耳邊的碎發吹得往前在臉頰上,神微微放空,片刻後,低了低頭,也轉頭看過來。
兩人的視線對上的那一刻,祁願頓了頓。
徐晏清看著,勾挑了挑眉,問道:“你剛剛怎麽就確定那是別人家丟的小孩,而不是我在哪的私生呢?”
這人吶,就是賤得慌。
祁願今天難得沒和他槍舌劍,他倒是自己找話說起來了。
祁願被問得愣了愣,斜著眸子看了他一眼,冷語反譏道:“那是我眼拙了,沒看出來徐總這些年還染上了個四播種的不良習。”
徐晏清也沒惱,隔著呼呼的江風虛瞧了一眼,神也染上了幾分玩味,揚了揚眉,反問道:“你這話裏的意思是,我就擱你這兒冷落了?”
這一句直接給祁願噎得無話可說,抬起眸子,微微氣結地掃了他一眼,就將視線挪去了別,不看他,也不說話。
在這種不著調地鬥方麵,從來說不過他,簡直就是詭辯屆第一把椅。
見不說話了,徐晏清又是一聲輕笑,似是了然地點了點頭:“行,我懂了。”
語罷,就拉著祁願往江堤的出口走去。
祁願微微一愣,胳膊被拉著,腳步有些急,匆匆問了句:“幹嘛去?”
Advertisement
徐晏清回頭瞧了一眼,揚起一邊眉,語氣壞:“你這不是說我冷落你了,那我雨均沾,以後我都住景園了。”
聞言,祁願又是一愣,抬頭看了眼前方的人,半晌後移開視線,任由他拉著走,淡淡說了聲:“隨你,反正也住不了多久。”
這一句說的就像是小孩子之間的攀比吵架,落下風的那一方總想從別的方麵找點優勢,以此來氣氣對方。
哪知道,話剛說完,徐晏清就發出了一聲嗤笑:“誰說住不了多久,房子是我買的,那不是想住就住?”
這話又結結實實堵了祁願一把,張了張,氣結地說了聲:“等你結婚我就把它賣了。”
明明是一句正兒八經的實話,不知為何,出口的那一刻,聽起來竟然還帶了點兒醋意的嗔。
連祁願自己都是微微一愣,而後抿了抿,不再吱聲。
“嗯,那你就搬來雲庭。”
輕飄飄的一句,有點漫不經心,卻又無比真誠,像是自言自語,但音量卻足以讓邊的人聽清。
“咚”的一聲,祁願心頭被敲了一記,倏地抬頭看過去,問道:“你說什麽?”
瞬間,二人前進的腳步都停了下來。
江堤上的人群已逐漸散去,喧囂盡歇,隻餘風聲呼呼地吹著。
徐晏清背對著祁願立了會兒,而後緩緩轉,輕蹙著眉頭看向,眸清而堅定,須臾才開口道:“你把景園賣了,那就搬來雲庭。”
這看似無關痛的一句,卻昭示了他的選擇與想法。
他改變主意了。
上次從醫院離開後,小江驅車送他回去,他坐在車裏沉默了許久,在車子駛過淮戲大門口時,他才苦地笑了笑,問了小江一句:“囚著個心已不在自己上的人在邊,是不是很卑劣?”
Advertisement
小江被問得也是一愣,心下忖度了一番,才低聲回道:“小願小姐是個心的人,在氣頭上說的話,您也不要往心裏去。”
他當即就哼笑了一聲,閉上眼睛靠在椅背上。
嗬,心。
真是好一個心。
小江從後視鏡看了他一眼,片刻後,抿了抿,才鬥膽說起了另一樁事。
“就三年前,路先生和褚小姐,不也是生生掰扯出了分嘛。”
這話一出,徐晏清就緩緩睜開了眼。
路闊和褚雲降,是在他認識祁願之前就有糾葛了的。
這倆人說得好聽點,郎有妾無意,說得難聽點,那就是強取豪奪。
這份起初的時候,所有人都覺得是路闊圖一新鮮,看上了個市井家庭的小姑娘,覺得對方有幾分姿,子也烈,讓人比較有征服。
哪知道,這越往後,事態的發展就越讓他們看不了。
路闊這小子起初也不在意,也是覺得自己就是圖一新鮮,長這麽大,最不缺的就是往自己上撲的人,忽然出現一個整天就對他齜牙瞪眼的,自然是要降一降的。
哪曉得就是這麽一時的好勝心,生生折磨了彼此好些年。
連他自己都給搭了進去。
其實徐晏清對褚雲降的印象不深,一來是因為路闊和糾葛的時候,他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國外,隻偶爾打電話的時候,會順帶提一。
但路闊大多都是含糊其辭,支支吾吾,他還嘲笑過他:“萬花叢中過,總算到了支帶刺的鏗鏘玫瑰了。”
那時候路闊還揶揄他:“你等著的,你最好祈禱別到啥難擰的瓜。”
他也笑嗬嗬地答:“自然不會,祁願乖得很。”
哪知道,還真一語讖。
當年路闊對褚雲降的評價一直就是三個字“倔擰軸”,現在想想,用來形容現在的祁願都算是輕的了。
Advertisement
的“倔”裏,還帶著傷人的“狠”。
前些天路闊勸他放手時,他還有些恍惚。
當年路闊和褚雲降鬧得最不可開的時候,他也這樣勸過他。
那時路闊坐在包廂沙發的角落裏,低垂著眉眼煙,脖子上還掛著一道道抓痕,細長鮮紅,神看起來落寞又消頹。
那一刻,徐晏清覺自己就好似在勸一個已經沉淪的癮君子,他又驚又肯定地說:“路闊,你上了。”
這種話以往他們侃笑時也不是沒有問過,但路闊大多都是愣一下,而後一副玩世不恭的樣子朝他們丟盒煙:“瞎講什麽,這話說了你們信嗎?”
但那天,他以肯定的語氣說出口的時候,路闊並沒有否認,隻一人坐在哪悶悶地煙。
再後來的事,他就不清楚了,他也沒心思去過問了。
因為,那也是他和祁願鬧得最兇的一段時間。
他將囚在景園,依舊如往日一般,同食同寢,每晚抱著睡,醒來後親一親的額頭,他再去公司。
可他也是眼睜睜地看著一點點消瘦,一點點沉死寂。
林瑜曾氣得衝去辦公室,指著他的鼻子罵他:“徐晏清你就是個禽,你還是個人嗎!”
他那時候煩到極致,來保安將拖了出去。
是,那就當他是個禽吧。
總比,這輩子和祁願再也沒有瓜葛的好。
那時候,家裏對他和祁願的反對的聲音也越來越大,兩邊的力,讓他又躁又惱。
他甚至想過,會不會,孩子會是個穩住兩邊最好的方法。
既堵住了徐家長輩們的,也留住了。
自殺的那天,他急匆匆趕去救,在從郊區趕往市區的路上,他滿腦子都是麻木的,闖了一個又一個紅燈,他都覺自己好似變了盲,這個世界都是灰蒙蒙的一片。
Advertisement
終於,在一個十字路口,從側麵疾馳而來一輛重卡。
接著,就是刺的鳴笛聲和剎車聲,他楞楞地看了一眼,而後慌忙打了方向盤。
一陣天旋地轉後,他覺有一溫熱的順著額角下,脖頸痛到失去知覺,視線也是殷紅一片。
意識模模糊糊中,他好似看見宋瑤自殺的那天,躺在一個白瓷浴缸裏,手腕沉在水底,鮮從刀口彌散出來。
倏地,那張臉一下子變了祁願的。
他費力的出手機,給小江打了個電話,嚨裏像是被一團腥鏽堵住,隻說了三個字:“救祁願。”
而後便陷了黑暗。
那一次,他在ICU住了兩個月,出院後第一件事就是去景園,可祁願已經不在了。
而路闊和褚雲降結束是在祁願走後一年,原因他不清楚,他沒心思問,也覺得沒必要問。
褚雲降當時的家庭基礎和社會地位,遠比祁願還要差,結束是遲早的事,路家是絕對不可能允許這樣的生進家門的。
那時候,他和路闊基本都很再去各種局,也就近兩年才重新回歸。
再說起路闊和褚雲降之間的事兒,小江用“生生掰扯出分來”也不為過,畢竟,也的確是路闊一廂願,扭了這段緣。
那晚,他又沉默了許久,一個不恥想法悄悄滋生。
或許,不並不重要,留住就好。
而他,也有將這一切實現的能力與手段。
他改變主意了。
留住吧,折磨也好,怨恨也罷,在他承認自己還他的那一刻,全都不作數了。
……
猜你喜歡
-
連載938 章
厲少,你家影後又被拐跑了
那天與厲修年美麗的“邂逅”,蘇小悠便入了厲修年的坑。意想不到的是,厲修年身份不一般,咳嗽一聲!整個A市都要因為他顫三顫!麵對強勢如此厲修年費儘心機的製造“偶遇”,還有那隻對你一人的小溫柔,順利一點點收攏蘇小悠內心。蘇小悠:我要好好拍戲,努力賺錢,玩轉花花世界,迎娶高富帥,走上人生巔峰!厲修年:小悠,錢我有,你隻需要…來娶我。蘇小悠:厲先生,我從小無父無母窮的一批恐怕配不上你。厲修年:那便認祖歸宗,以後,我便是你的人生巔峰。
84.4萬字8 7324 -
完結1181 章

嚴爺家的小祖宗不能惹
【女強+玄學+甜爽】她說,她能壓制他身上的煞氣,他默許了他們交換來的婚約。訂婚宴剛過,她失蹤了。六年后,她帶著孩子回來,并在陰陽巷開了一間陰陽風水鋪。棺材鋪和香燭鋪送來棺材小件和金銀紙錢花籃,圍觀人群:怕不是砸場子的?明落塵笑著說:“百無禁忌,升棺發財,金銀滾滾來。”她算天算地算兇吉,一句話能斷人生死,成為風水界的頂級風水師。有人算計他和孩子,她為了他們,把這京城的天捅破了又如何?
224.3萬字8.33 54681 -
完結1007 章

和首富老公離婚後我爆紅了
三年前盛惜嫁給了A市第一首富陸劭崢。 她努力當好溫順本份的妻子,換來的卻是不屑一顧。 盛惜幡然醒悟,搞男人不如搞事業。 很快陸首富就收到了一份離婚協議書。 * 離婚前,在陸劭崢眼裏,盛惜溫柔漂亮聽話,但卻老實木訥毫無情趣可言。 而離婚後—— 公司旗下的直播平臺,甜美豪放的某一姐人氣火爆。 娛樂圈出了個當紅女王,身邊圍繞著各種俊男鮮肉大獻殷勤。 後來,某俱樂部里陸總又偶遇浪的沒邊,笑的不要太開心的女人。 女人感嘆:「果然還是年輕男人好啊,看看這腹肌,馬甲,人魚線」 「……」 陸總一張俊臉都氣歪了。 去他媽的老實乖順,這位前妻路子野的很! 一點也不老實! 當死對頭也拿著大鑽戒,笑的一臉風騷:「嫁給我,氣死你前夫」 陸首富:「???」 一個個都覬覦他老婆,當他是死的?!
88.4萬字8 149977 -
完結1006 章

退婚后被權爺寵上天
醉酒后,她主動招惹了他。男人目光如刃,薄情冷性,將她抵在墻角:“別招惹我,我怕你玩不起。” 后來,退婚、無家可歸的徐挽寧,跟他回了家。 結婚后, 徐挽寧成了后媽,養著別人的孩子,也明白他娶自己,不僅是因為自己聽話好拿捏,還因為她長得像一個人。 提出離婚時,他從身后擁住她,嗓音喑啞,“不離,行不行?” 她只勾唇輕笑:“二爺,您是不是玩不起。”
178.3萬字8 66443 -
完結12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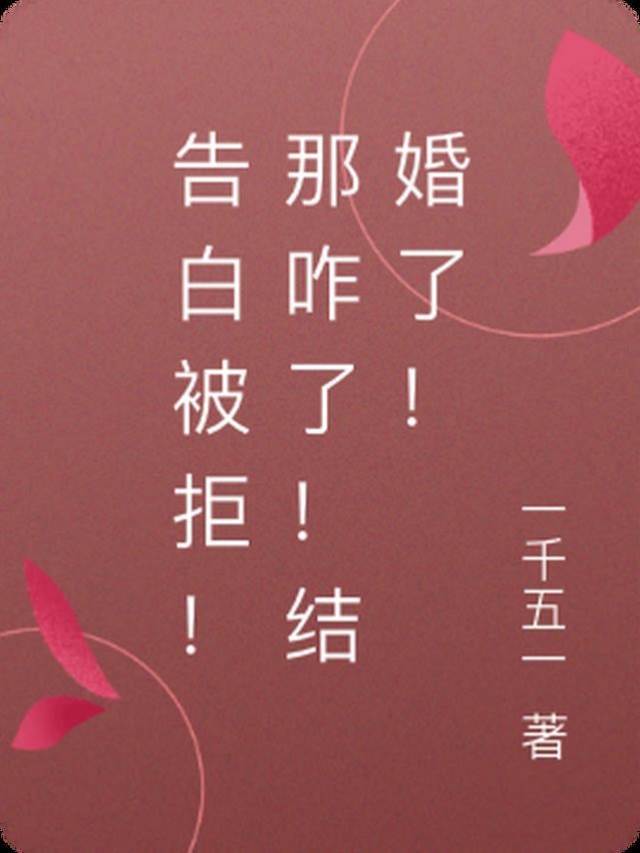
告白被拒!那咋了!結婚了!
【明著冷暗著騷男主VS明媚又慫但勇女主】(暗戀 雙潔 甜寵 豪門)蘇檸饞路遲緒許久,終於告白了——當著公司全高層的麵。然後被無情辭退。當晚她就撿漏把路遲緒給睡了,蘇檸覺得這波不虧。事發後,她準備跑路,一隻腳還沒踏上飛機,就被連人帶行李的綁了回來。36度的嘴說出讓人聽不懂的話:“結婚。”蘇檸:“腦子不好就去治。”後來,真結婚了。但是路遲緒出差了。蘇檸這麽過上了老公今晚不在家,喝酒蹦迪點男模,夜夜笙歌的瀟灑日子。直到某人提前回國,當場在酒店逮住蘇檸。“正好,這房開了不浪費。”蘇檸雙手被領帶捆在床頭,微微顫顫,後悔莫及。立意:見色起意,春風乍起。
26.9萬字8 988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