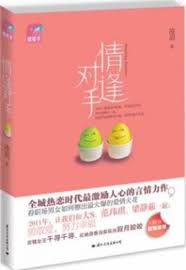《再度招惹》 第83章 chapter83
許校程整個人都是僵住的,好半晌不能回神。
心突然之間空了那麽一瞬,這種覺似曾相識。
當初,他對蘇印說出分手,隻得到哭泣的挽留的那晚,他也是這種覺。
走不下去了,會分開吧。
分開就意味著失去。
低頭看著離自己這麽近的人,看著齒啟,一句句說出這些話。
許校程看著,他出手到了的額頭,撥開額前被汗水打的頭發,觀察著這張臉上的表。
這張臉,甚至連剛才的紅都沒有散盡,可是的眼神裏麵卻已經全是冰冷了。這種冰冷和他們最初重逢的時候如出一轍。
指尖描繪著小巧致的臉部廓,靠近了,開口:“蘇印,你再說一遍。”
蘇印直視著他,覺得有些好笑,在這一刻竟然從許校程的眼中看到了傷。別開了視線,頭轉的作帶著突出了|的鎖骨,上麵帶著曖昧的痕跡。
蘇印笑笑,“我向你道歉,對不起。不應該和你這麽不清不楚的,我以為你也喜歡這樣的方式,還樂在其中呢。如果讓你不痛快了,我道歉總可以了吧?”
嘲諷的語調,像是在說,看看吧,至我比你麵。
至會麵的提出分手,還會道歉。
許校程還是有些難以置信的看著。
屋子裏的一切都安靜了,隻有他們的呼吸聲。蘇印甚至能到他目裏的······應該是憤怒,可是又很悲傷。
在幾乎將人溺斃的悲傷裏沉默。
這一刻,他們之間更像是一種無形的對峙。
蘇印很想直接給他一掌,質問他現在過的幸福嗎?質問他一家三口的日子過的如何,被那樣可的一個孩子追在後“爸爸”的覺如何?
可是看著他,想著兩人在蕪昌的相,想著最近以來的一段日子······就這樣,讓過去的一切都在這一刻結束,被困住的覺太難了,不想再困在裏麵。
Advertisement
在這一刻,恍惚明白。從來不會有同。
就算他知道了過去,知道了那個孩子,他也不能知曉曾經的切之痛。
“蘇印,你不是這樣的人。”他一字一句道。
“我不是這樣的人?”蘇印已經快要抑製不住笑意了,笑的時候眼睛彎彎的,格外好看。“那我是哪樣的人?許校程,我們都分開多年了,你還能確保我是怎樣的人不?”
他盯著看了一會兒,雙手捧住了的臉,“你是不是,還在記恨我當初以那樣的方式離開了?”
許校程看著,觀察著臉上的表,他覺得自己此刻就像隻無頭蒼蠅,完全不明白蘇印這突然的轉變。
他所能想到的隻有這一點,就是當初以那樣絕的方式和蘇印分開,還說出了“膩了”這樣的話。蘇印是在賭氣,一定是心裏不舒服,所以在賭氣。
想到這一點,他一時間有些難言。
“蘇印,當初是我犯了錯,是我做的不對……我太年輕又太自以為是,對不……”他說到一半停住了,因為還是冷漠。
的冷漠讓許校程明白,他完全沒有解釋的必要。
他低著頭,沉默了好一會兒。
不是不願意低頭。
他知道,就算是他現在說一大籮筐的話,在麵前如何沒有尊嚴的低頭都沒有用了。
就給他自己留一點底和尊嚴。
也給他們留份麵。
許校程扯扯角,神終是恢複了淡然。
他鬆開了手,從滿是蘇印味道的床上坐了起來,從散落一地的服中拿出自己的,不不慢的穿戴好。
坐在床邊,慢慢的扣著扣子。
“蘇印,你確定你說的都是真心話?”他再一次確認。
蘇印看著他,沒回答。說的話不是真心,還是一直在心裏的。知道自己很冷靜,很冷靜的說出了這些。
Advertisement
許校程笑笑,拿過不遠座椅上的外套。穿戴好,又回到了床邊。
他低頭看著,半晌附下來,蘇印偏頭去躲,卻被他扣住了肩膀。
他打量著,低頭在的額頭印下一個吻。
“玩就玩兒吧,我信你。”他說。
他提著西裝外套出門,背影高,步子卻顯得淩。
“我信你。”他重複。
蘇印沒說話,看著他出了臥室。
躺在床上,聽著外麵的門也被關上的聲音。
房間裏麵一下子安靜下來。
在那裏躺了好一會兒,手攥又鬆開。做了自己想做的一切,原本以為會釋然,可是卻發現自己並沒有輕鬆多。
起,去浴室洗了澡。
再出來,看著淩的床鋪,幾步走到床前。
把那些床單被套統統拆下來,團一團丟進了浴室的垃圾桶裏。
再出來,卻發現自己在臥室一刻也不想多待,去了臥室,窩進了沙發裏。
客廳的擺鍾滴滴答答的走著時間,十二點過去,除夕夜也過去了。
-
沈然偶遇許校程是已經休完年假以後了,他去會所辦事,恰好看到許校程也在。
沈然談完了事,就一直站在會所門口等。看許校程和對方正在談。那人不知說了什麽,許校程微微點頭示意。
沒一會兒,他們談完了,等別人都走後,沈然才進了房間。上前的時候就調侃了一句:“許總就是厲害,年假剛休完就出來賺錢了。”
許校程將手裏的文件放好,答他:“也還行。”
沈然笑了一聲,“剛才那位宋總是我們沈氏先接的。”
許校程答:“嗯。”
沈然:“你們現在簽訂合約了?”
許校程上前拍了拍沈然的肩膀,頗為語重心長道:“合作這事兒得各憑本事。”
沈然:“······”還就真不留一丁點的麵子唄。
Advertisement
“聽說除夕那天和家裏鬧的很不愉快?”沈然問。
自小和許校程一起長大,沈然什麽話都敢問。
“從哪裏聽說的?”許校程反問。
“許思淵說的。”沈然坦然回答。
許校程拿杯子喝了一口水,而後打量著沈然,“許思淵得出國。”
沈然道:“別啊,你都把他送我了,現在就是我的。”
許校程有些無語,“你到底是用什麽方法,他留在公司的?”
一向不管束無法無天的許思淵居然就乖乖待在沈然公司了,許校程著實有些驚訝。
沈然故作神的笑笑,沒有回答。過了一會兒,他的神又嚴肅下來。看著許校程道:“我倒是想和你說說那位蘇印的事。”
許校程放杯子的作僵了僵,可是片刻又恢複了淡然。
“有關於的事就別說了。”許校程說。
那晚除夕夜從家出來後,許校程在樓下站了好幾個小時。他的緒從最開始的不解,約的憤怒,到最後平靜釋然。
許校程想通了,其實很多事過去了就是過去了,哪怕再努力也是回不去的。
他和蘇印的那一段,是最濃墨重彩的一筆,他們在平淡的日子裏也曾刻骨銘心過。分開後他想要忘過,最後卻都以失敗告終。
再一次重逢,他們又一起走了一段的路,可是很多東西都已經變了。
就像蘇印最後說出的那些話時候,他最切實的就是無力。是對他們丟掉的這六年的無力。
沈然頓了幾秒,說:“咋?又分開了?”
許校程沒回答他的問題。
“我就知道你們走不到一,我還就提醒你了,今天我說的這話你還真得聽聽。還記得上次我跟你提過的一個徐陵的人,他是蘇印的老師,也是的未婚夫。”
Advertisement
許校程轉,看著沈然,神冰冷又怪異。
“沒想到吧?我也沒想到。剛開始我還覺得奇怪,蘇印之前不是陳雋朋友嗎?怎麽還有一個未婚夫了,這算怎麽回事?就在幾天前,我見到了一個澳大利亞的朋友,他跟我說徐陵和喜歡自己的一個學生,為了培養那個學生,可是花了大手筆。那學生對徐陵是什麽態度倒不清楚,但估計也是不簡單。但那學生還年輕,不願意過早定下來,徐陵就說:你可以玩兒,我不會手,玩夠了就回來。”
沈然說的有些激,說完之後還不忘補問一句:“那學生是誰,不用我多說吧?”
自然不用多說,就差直接拿著蘇印的份證念了。
許校程抿著,想起除夕夜那晚蘇印的話,當他問他們之間算什麽的時候,漫不經心的答了一句:“玩兒吧。”
現在看來真的是玩兒。
沈然還沉浸在自己的思緒裏,半晌低聲罵了一句,“你說徐陵這老男人就真這麽大肚量,讓未婚妻可勁兒的在外麵玩兒?還玩兒夠了再回到他邊。怎麽?他真當自己是一代聖啊······蘇印也是,怎麽就······”
他話還沒有說完,許校程已經出門了,顯然是不想聽他再說下去。
沈然跟在後,歎口氣又搖搖頭。心想許校程這是造了什麽孽,遇到一個蘇印。
前幾年過的沒人樣,蘇印回了北京,兩人蕪昌一行回來後多了一點煙火氣。可是還沒煙火氣兩天,又分分合合鬧的這麽多。想想都覺得心累。
他走快了幾步,追上許校程,低頭思考了一會兒,說:“你也別嫌我話多,實在是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想想,你和蘇印那都多久之前的事了?是人都會變的,這麽多年過去了,肯定也會變。你也變了。年輕時候談個,何況還是兄弟你的初,自然忘不了。可是忘不了歸忘不了,人得向前看。你看你們這都分分合合多次了,這就說明是真不合適。”
許校程停下步子,看了一眼沈然。
被他這麽一看,沈然就閉了。
“我說的都是實話。”沈然說。
猜你喜歡
-
完結143 章

無法抗拒的他
蘇雲被綠了,怒甩渣男。 將真心收回后再不肯輕易給人。 戀愛麼,何必那麼認真。 何勉偏要蘇雲的心,徐徐圖之。 何勉:「要不要和我談戀愛,不用負責的那種」 蘇云:「……好」 後來。 何勉:「你不對我負責沒關係,我對你負責就行」 蘇云:「為什麼是我?我有過去的」 配不上你。 何勉:「沒事,誰都有瞎的時候,我不怪你」
3.6萬字8 8361 -
完結29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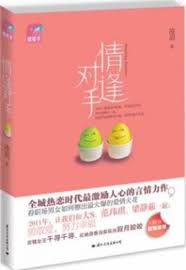
情逢對手
我們兩個,始終沒有愛的一樣深,等等我,讓我努力追上你
55.5萬字8.18 3380 -
完結736 章

退燒
(雙潔,1v1,互撩) 沈宴是江城最有名的浪蕩大少,所有女人都想投入他的懷抱。 可他玩世不恭,什麼都不在乎。 直到 他雙目血紅,箍住女人細腰的手臂上青筋暴起,用卑微的語氣祈求:池歡,不要走…… 原來他心裡那場火,只肯為一個人而燃燒。 池歡和秦駱離婚的當晚,頭腦發熱找上了沈宴。 本以為只是一時纏綿,卻不想,自己早已步步走入沈宴的領地之中。 待她清醒時,才發現這是一場預謀多年的夜宴之邀。 膚白貌美天生媚骨VS八塊腹肌極品尤物
101.1萬字8.18 1494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