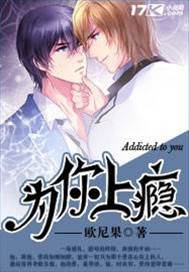《酥酥》 第145頁
殷著費疑舟,又突發奇想地湊近了點兒,打探道:“那你呼吸比正常人慢,心跳是不是也比正常人慢?”
“按理說是這樣。”費疑舟靜了靜,又漫不經心道,“要不要上來聽一下?”
“大可不必。”殷被口水嗆住了,汗兩秒,然后才又接著好奇發問,“你們經常保持高強度運的人,心跳比正常人慢又是什麼原因?”
費疑舟聞言,眼底繾出一無奈的好笑。結婚第一晚,他忍住不,忍得快發瘋,居然在這兒滿臉好奇與對知識的探索,讓他科普掃盲。
費疑舟懷疑是故意的。
口中卻還是很自然地回答:“因為常年運的人心強大,心室容積大,心臟神經調節能力強,氧利用和能量代謝都高,這些都減了心臟負擔和心率需求。”
“嗯,我懂了。”殷恍然,繼而又發自心升起一敬佩,對他予以稱贊:“你知識儲備很富。”
Advertisement
“過獎。”費疑舟淡淡地應,“多看了幾本書而已。”
“你材也蠻好。”殷順帶又多夸了一句。畢竟很清楚,吹金主爸爸的彩虹屁,百益無害,“看得出來平時很自律。”
“謝謝。”費疑舟對的各類夸獎照單全收,平靜地回答。
片刻,見眸子還是閃著,完全沒有困倦將眠的征兆,便低頭傾,近些許。
“大晚上的你不閉上眼睛睡覺,神這麼好。”他說,嗓音稍顯低啞,像裹著粒未燃的火星。
這麼近的距離四目相對,殷微怔,又在他眼底看見了已不算陌生的沉沉濃霧。
心跳驀地掉一拍,大腦出再次敲響了警鐘,意識到況不妙。
沒辦法,殷只能老老實實地解釋:“我不是神好,是因為第一次和異睡一張床,比較張。確實有點睡不著。”
費疑舟聞言靜默兩秒,應:“那巧的。”
Advertisement
殷茫茫然:“什麼巧?”
大公子平靜地說:“我也是第一次和異睡一張床,也有點張,睡不著。”
聽到這番話,殷腦子里瞬間回響起梁靜的告誡——他就是在立純戰神的人設,要走你的心,徹底征服你,讓你得死心塌地死去活來。
思及此,殷不由深沉地瞇了瞇眼睛,盯著費疑舟淡漠矜貴的俊臉,在心里說:你丫裝純裝得還像。
不過,大佬喜歡裝,那就裝吧。人各有志了屬于是。
他裝是他的事,不拆穿是有素質。
殷沒有對費疑舟的話語提出質疑,也沒有表出一一毫的不信任或者唾棄。只是溫地、淑地、端莊地朝他彎了彎,笑著說:“你放心,只要你給我點時間,我們躺一起多睡幾次,我絕對就慢慢習慣了。”
費疑舟耷拉著眼皮看著,問:“那你現在是睡還是不睡。”
Advertisement
殷一雙大眼眨兩下,很認真地往他湊近幾公分,低聲:“這取決于你做還是不做。”
“……”費疑舟盯著,挑眉。
接著便瞧見這姑娘紅著臉蛋吸氣吐氣,做了個深呼吸,仿佛下定極大決心般,出兩只纖白的手,比劃到他眼皮底下,啪啪啪,鼓了三下掌,故作老地說:“就是這個。懂否?”
“……”費疑舟眉峰再挑高半寸。
“你這樣一直吊著我,也沒個準話,我心里很怕的。”殷著他,語氣聽起來頗為嚴肅,“誰知道等我睡到一半,你會不會突然……”
“大發”這個詞已經滾到了皮邊上,滴溜一圈兒,又被生生給咽了回去。殷微頓,干咽了口唾沫,非常識時務地換了一個詞:“你會不會突然,心來,要潛規則我。”
費疑舟直勾勾盯著旁的姑娘,這副明明青窘迫滿面紅,卻要裝腔作勢扮老手的姿態,落在他眼中沒有毫的造作討嫌,只有可。
Advertisement
又或者換個更準確的說法。
即使矯造作,他也只看到乖巧。
他覺得有意思,因而更近,修長指尖繞起一縷的黑發纏過兩圈,慢條斯理地把玩。口中緩慢地說:“你這說法不準確,我們是夫妻,你跟我做這檔事可不潛規則,說得通俗點可以圓房,說得文藝點‘云歡雨合’。”
殷默,心想反正不都是一個意思。
“我們這行說這個說習慣了,你理解就好。”殷頓了下,乖乖聽從指示改變說辭:“那請問,你今晚到底要不要和我……圓房?”
費疑舟瞳如霧,輕輕欺近潤的瓣,在半指之隔停下,低聲懶耷耷地問:“那你是怎麼想的?”
小士:如果覺得不錯,記得收藏網址 或推薦給朋友哦~拜托啦 (>.
猜你喜歡
-
完結21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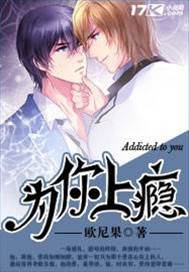
為你上癮
一場婚禮,游戲的終結,真情的開始。 他,林浩,愛的如癡如醉,放棄一切只為那個愛在心尖上的人,最后落得身敗名裂!他的愛,是笑話。 他,時炎羽,愛的若即若離,利用他人只為完成自己的心愿,最后痛的撕心裂肺,他的愛,是自作多情。 沒人能說,他們兩的愛能走到哪一步,錯誤的開端終將分叉,再次結合,又會碰撞出怎樣的火花?
54.2萬字8 6917 -
完結2513 章

前夫請彆念念不忘
離婚前——阮星晚在周辭深眼裡就是一個心思歹毒,為達目的不折手段的女人。離婚後——周辭深冷靜道:“如果你反悔了,我可以考慮再給你一次機會。”阮星晚:“?”“謝謝,不需要。”
211.8萬字8 93731 -
連載268 章

心肝,別不要我了好不好
初遇時,你是南邊寒冷中的笙歌,在一個又一個夜晚治愈著處于地獄的我。七歲的南笙在寒冷的夜晚撿到了巷子角落里的殷寒,向他伸出了白皙溫暖的手,她說的第一句話:“小哥哥,你好好看呀!愿意跟我回家做我的老公嗎?”殷寒不知道的是當他握住那寒冷中的那抹溫暖的時候,他命運的齒輪開始了轉動。南笙帶殷寒回家八年,六年里每次叫他,他都說我在,但是他不知道為什麼,后面的兩年里,她卻變了,一次又一次的滾,你好臟,你別碰我都 ...
48.7萬字8 263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