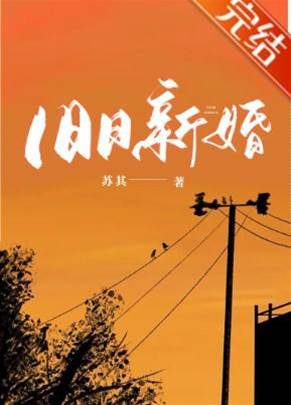《寵到懷孕:老婆,我比他會疼你》 第86章 前世,我很悔恨
“我沒。”顧晚晚否認。
厲宴承抓起床頭花瓶裏的玫瑰花,隨手砸過去。
玫瑰花刺,落在顧晚晚上,疼的鎖眉。
“顧晚晚,我有沒有對你說過,不準司染?”前世,司染就是被顧晚晚氣的得了胃癌,這世他可不允許這種事再發生。
顧晚晚知道再否認也沒用了,拚命搖頭,臉慘白:“我隻是找人教訓司染一頓,畢竟你對那麽好,卻對你不屑,我為你鳴不平,我從來沒想過要殺了。”
“找殺手隻是教訓一頓?你把我當傻瓜!”厲宴承低頭,聲細語,卻讓顧晚晚惡寒。
上散發玫瑰花的香味,手心的花刺在握手後,滲鮮,抖,楚楚可憐,可卻無法引起他的心。
他眉眼愈發冷冽:”顧晚晚,若不是留著你還有用,我一定會把你送給墨寒嶼,讓他好好折磨你。”
顧晚晚劇烈抖,知道墨寒嶼對司染的疼,更知道要是落到墨寒嶼手裏,會遭怎樣非人的待。
Advertisement
“你還用以前的法子去勾引江宵琛,把他拉攏到我這邊來。”厲宴承輕聲道:“我知道他一直對你念念不忘。”
勾引江宵琛,那就必須要和江宵琛上床。
可是他的未婚妻,是未來的厲家啊。
他真的不在乎嗎?
“晏城哥,你知道江宵琛要我什麽嗎?”顧晚晚下哽咽的聲音。
“嗯。”厲晏承道:“他饞你嘛。”
既然知道,為什麽還要去做這種事啊。
“晚晚,我是那麽淺的人嗎?司染不是也跟墨寒嶼了嗎?我不是照樣對司染過往不咎嗎?”厲宴承道:“晚晚,你為我做的,我會記在心底,不會辜負你。”
顧晚晚被他的承諾到,眼睛散發,“晏承哥,有你這句話就夠了,我願為你做任何事。”
厲宴承溫掉的眼淚,“那去洗浴,打扮的漂亮點去找江宵琛吧,滿足他所有要求。”
顧晚晚像個提線木偶起,往浴室走去。
Advertisement
厲宴承離開,對汪吩咐:“繼續嚴監視,有任何風吹草都要告訴我。”
汪:“知道了,墨。”
之後,顧晚晚和江宵琛的照片,源源不斷傳到厲宴承手裏。
他淡定翻看照片,引來汪的憤憤不平:“爺,顧晚晚現在太囂張了,幾乎每天都去見江宵琛,他們本不避人,圈子裏的人也都知道了,您打算怎麽辦?”
“我默許的。”厲宴承開口:“我需要江宵琛的支持。”
汪:“……可是您這麽做,是不是太憋屈了?顧小姐還是你名義上的人。”
厲宴承把一疊照片收起來,低:“你說染染會不會同我?會不會可憐我?”
汪:“???”
“你說過很善良,應該會對我產生一點憐憫吧?”
麵對他期待的目,汪隻好點頭:“司小姐應該會。”
厲宴承笑意濃烈:“我該去見了。”
他約司染出來,司染一口拒絕:“你要是有病就去治病,不要來擾我。”
Advertisement
“我為以前對你做的事道歉。”
“你做的錯事太多了,你道歉道的過來嗎?”
厲宴承啞然,許久道:“你拿刀捅我,我沒報警,也沒舍得傷害你,染染,我對你已經足夠寬容。”
“噢,然後呢?”司染冷淡道:“我還要謝你不?”
“……不用,我隻想你出來見個麵,我們許久沒見了。”
“不見。”
厲宴承隻好道:“我知道誰前段時間找殺手傷害你。”
司染沉默片刻,“是顧晚晚吧?”
“我有證據,你要嗎?”
“厲宴承,你到底在下什麽棋?”他怎麽會那麽好心把顧晚晚的證據給,一定有什麽謀。
“墨寒嶼可以為了你,將你大伯一家收拾的幹淨利索,我也想保護你。”厲宴承的聲音出深,好似一個大種。
若是前世,司染會被撥,可這世他的這些招數對沒用了。
“好,約在哪裏見麵?”
厲宴承說了時間地點,司染答應前往。
Advertisement
他掛斷電話,讓汪給他挑選服:
“你說染染喜歡我穿什麽服?”
汪看他興的模樣,忙給他出謀劃策,最終他選定黑襯衫,黑長,袖扣挽起,帶上司染以前選的袖口,他的打扮完全按照司染的喜好來,他從來沒有那麽在乎自己的容貌過,前世的記憶裏,染染不止一次誇他長的好。
他要好看給看。
今晚,他會鄭重告訴染染,他對前世的事很悔恨,真心想和重新開始。
厲宴承到了包廂。
包廂裏不僅坐著司染,還有墨寒嶼。
猜你喜歡
-
完結233 章

豪門未婚夫有了讀心術
下一本預收:《重生頂流的隱婚嬌妻》文案在后。本文文案:唐暖是一本甜寵小說里炮灰女配,作為圈子里出了名的草包花瓶,卻有一個頂流豪門的未婚夫。結果未婚夫的初戀女神歸來,直接揭穿了她假千金的身份。她不僅被唐家掃地出門,還會被葉家退婚。眾人都等著看她糾纏葉殊宴的笑話。葉殊宴也這麼覺得,因此準備了足夠的賠償,結果一場意外醒來,他忽然就有了讀心術。還沒搞清楚情況,一個清晰的女聲傳來:【他的讀心術有效范
36.4萬字8 8357 -
完結128 章

豪門太太重生后擺爛了
周圍親朋都覺得羅箏箏命好,大學一畢業就嫁入豪門,雖然丈夫英年早逝,但兒子聰明能干,能繼承家業,她也能享一輩子福。美中不足的是年近四十還被污蔑為小三,被人拿著去世
38.1萬字8 14578 -
完結17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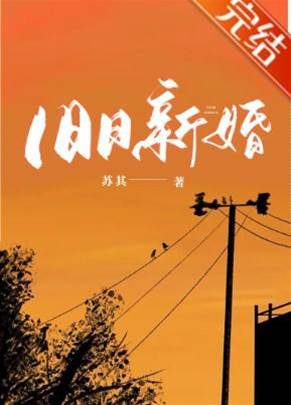
立冬/舊日新婚
秦南山是聞依最不喜歡的男人類型之一,刻板嚴肅,沒有喜好,沒有激情,像密林深處一潭死水,石頭扔進去,波瀾不驚。 一夜混亂,聞依更新認知,不全無可取之處。 一個月後,聞依看着試紙上兩道鮮明的紅槓,陷入沉思。 從懂事起,她從未想過結婚生子。 - 秦南山二十八歲,A大數學系副教授,完美主義,討厭意外,包括數學公式和人生。 聞依找上門時他一夜沒睡,逼着自己接受這個意外。 領證、辦婚禮、同居,他們被迫進入一段婚姻。 某個冬日深夜,聞依忽然想吃點酸的,換好衣服準備出門。 客廳裏穿着整齊加班的秦南山看向玄關被她踢亂的鞋子,眉心緊擰,耐着性子問:“去哪?” “想吃酸的。” “非吃不可?” “嗯。” 男人垂眸看錶,十二點零七分。 他心底輕嘆一聲,站起來,無奈道:“我去給你買。”
31萬字8.18 1927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