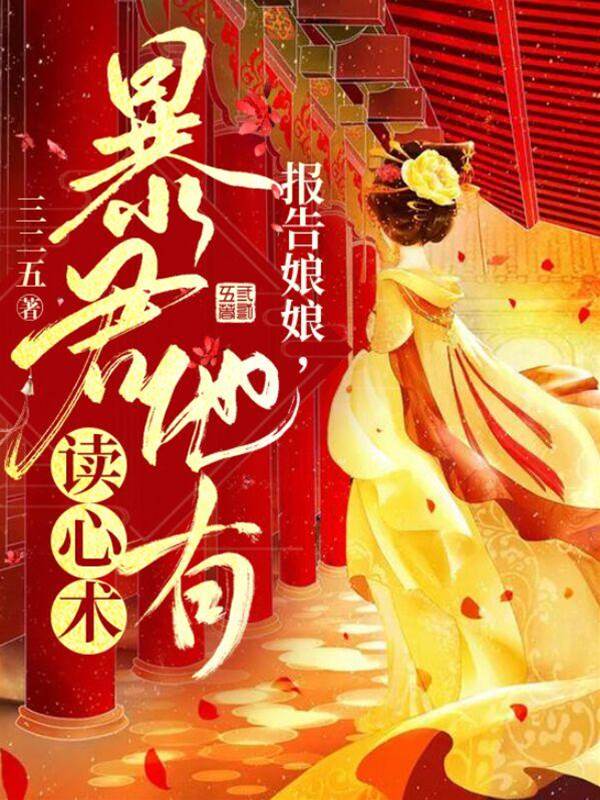《芙蓉帳暖,清冷小叔不經撩》 第50章 患得患失,才能讓人意識到在乎的是什麼
“先前未見時,希兒還有些擔憂,不過今日得見,我認為,梁公子品行端正,的確是不可多得的良人。”
謝希暮聲音細微,面頰染上酡紅,猶如傍晚天邊橙紅落霞,不勝收,令謝識瑯神思一滯。
謝端遠算是得到了滿意答復,笑著拍了下謝希暮的腦袋,“好丫頭,雖說現在不著急定下婚事,但梁鶴隨不日便要外放,
你趁著這段時日,多跟他相相,日后婚便是兩個人的事了,多了解他的為人總是不錯的。”
謝識瑯靜靜地注視謝希暮,子聽到謝端遠的話,也只是怯點了下頭。
時辰不早了,謝端遠年紀大了要早些休息,阿順便將謝希暮準備的紅豆糕送了過去。
“老族長,如今春有時日了,食些紅豆糕對腸胃好。”
謝識瑯盯著那盤造型圓潤的紅豆糕,忽地想起荷包滾出來的那顆紅豆。
謝端遠嘗了口,“味道真不錯。”
阿順笑道“老族長不知道,這段時日,姑娘一直幫著院里的小廚房做紅豆糕,一院子就能聞到紅豆味,姑娘還擔心備的紅豆,免得哪個院子里的吃,便先將這籠蒸好的先送給您。”
這就說得通了。
難怪荷包里會有紅豆,想來是謝希暮做糕點時不慎掉進去的。
謝識瑯腦子里全是他抓住謝希暮質問的模樣。
恐怕那時,小姑娘都在心里罵他是瘋子。
越這樣想,他的子就越發僵,尤其是在謝希暮面前,越發無地自容。
Advertisement
“小叔叔的臉怎麼這般差?”
謝希暮輕飄飄瞥了眼謝識瑯,將阿順手里另一個食盒給他,“這個是給明理院的,阿蟒不食甜,底下那盤是給他的,今日天晚了,我就不專門去送一趟了,麻煩小叔叔自己帶過去。”
謝識瑯艱難地接過食盒,小姑娘已經揚長而去。
他在原地愣了一會兒神,謝端遠提醒,他才緩過來,重新追了出去。
謝希暮今日離開得快,等謝識瑯追到朝暮院時,主屋的門已經閉上了。
天
晚了,謝希暮慣來恤下人,這個時候都讓下人回屋了。
他緩緩走到門前,輕叩了幾下,“希兒,我能跟你說說話嗎?”
屋燭火晃了下,謝希暮的聲音清晰,卻沒有開門,“小叔叔要說什麼?就這樣說吧,深更半夜的,咱們男有別,合該避嫌才是。”
這話說得謝識瑯心里很不舒坦,深吸一口氣,緩緩道“對不起。”
里頭的回應來得慢,“小叔叔何故道歉?”
謝識瑯盯著屋子里那團燭,啞聲“先前在祠堂里的時候,是我…魯莽了。”
“……”
謝希暮輕聲道“上次我說過,就當那夜的事從沒發生過,我始終是恩小叔叔的,若非你將我養大,今日我又哪里有機會能遇到像梁公子這樣的好人。”
提及梁鶴隨,謝識瑯眉頭皺了起來,“希兒,你與梁鶴隨始終只有一面之緣,莫要因為和我賭氣,隨意做主自己的終大事。”
Advertisement
謝希暮忽然笑了聲,淡淡的似是佛堂醇香的紫檀,令人心尖上發。
“小叔叔,我既然說了那夜的事當作沒發生,在我眼中便是過往云煙,如何還會生你的氣,又如何還會和你賭氣,
再者,梁公子在我看來當真是不錯,我的確是想與他多加相。”
謝識瑯默然。
若非是同他賭氣,又何至于連屋子都不讓他進。
別瞧謝希暮子弱弱的,其實骨子里倔得很,若真是覺得自己了委屈,亦或是心中負氣,從不會主說出來。
他同相了這些年,如何不清楚男有別不過是的托詞。
“……”
夜間風大了起來,曉真是等謝識瑯走了才屋子。
“方
才丞相的表可難看了。”
曉真回想方才所見,忍不住嘆了口氣“姑娘,我真是越來越看不懂了,你并不是真的想與梁公子在一起,為何又要故意氣丞相?
今日還跟著梁公子跑了,丞相當時的臉氣得比小廚房那口陳年老鍋都黑。”
謝希暮聽了曉真的話,展開好一陣聯想,不笑了出來。
“僅憑平日里的相,可不能讓人看清自己的心,
就像風箏一樣,線要是牢牢握在手里,風箏人是意識不到其實風箏是會飛走的,只有將線剪了,需要自己跳起來去抓、去搶,患得患失,才能讓人意識到自己究竟在乎的是什麼。”
曉真好像明白了,又好像不太明白,“那這風箏到底還要飛多久,才會回到風箏人手里。”
Advertisement
謝希暮聞言眸底淬上幾點笑意,“還早著呢。”
皇帝壽辰將近,由三皇子辦了壽宴,邀朝臣們攜家眷一同赴宴。
謝端遠近來覺得子骨越發差了,尤其是近來春雨連綿,他腳越發疼痛,不便走,不過小輩們多去這種場合也是長見識,便叮囑著謝希暮和謝樂芙去鋪里多挑兩件新裳,以便赴宴。
謝識瑯今日本該出門辦明程的事,聽說謝希暮要出門挑裳,便匆匆趕來正堂。
“二叔,你怎麼來了?”
謝識瑯掩住不定的呼吸,佯裝鎮定瞥了眼謝希暮,“我最近太忙了,很陪你們,今日打算些時間帶你們去買裳。”
話是對兩個人說的,眼神卻是落在謝希暮上。
“可惜了小叔叔一片心意。”謝希暮忽然道。
謝識瑯角微僵,“什麼?”
“是這樣的,今日我本來約了梁小公子來下棋,后來看希兒和樂芙要去買裳,擔心兩個姑娘不安全,便讓梁小公子帶們去。”謝端遠這話說得委婉,其實就是為了給謝希暮和梁鶴隨相擋上一層遮布。
謝識瑯緩緩瞧向謝希暮
,子神無異,全然是沒有將他昨日說得那番話聽進去。
“梁某來遲,讓二位姑娘久等了。”
來者腳下生風,手持玉骨折扇,風度翩翩,笑容亦是可親。
梁鶴隨先同謝端遠見過禮,隨即向謝識瑯作揖,“下拜見丞相。”
不知怎得,謝識瑯一瞧見梁鶴隨面上燦爛的笑容,就覺得刺目,尤其是謝希暮瞧向這人的目,饒是春連綿。
Advertisement
“梁大人。”
謝識瑯深吸一口氣,抑制住眸底的厭惡。
梁鶴隨像瞧不見謝識瑯對他的不喜,往上湊道“先前下只遠遠瞧見過丞相一回,如今離得近些,更能瞧出您俊朗非凡,
大姑娘被您養在膝下,上的氣度與您倒是很像。”
謝識瑯心底更沉,冷冷別開眼,“梁公子倒是與梁老棋師不像。”
梁老棋師道骨仙風,是世俗之輩超群的存在,謝識瑯這話便是在罵梁鶴隨溜須拍馬,俗氣得不行。
梁鶴隨倒像分毫聽不出他的言外之意,又同謝希暮說笑了兩句,便辭行,帶著人離開了正堂。
謝識瑯盯著謝希暮和梁鶴隨的背影,眸底暗越深。
阿梁適時提醒“主子,咱們得去辦明將軍的事了。”
男子這才緩緩收回視線,亦離開了府邸。
到了夜間,謝識瑯才冒著寒瑟濃重的氣回了明理院。
阿梁還提醒謝識瑯要不要去朝暮院瞧瞧,男子頓了下,冷著臉拒絕了這個提議。
他在書房看了片刻折子,門外忽然響起了一陣敲門聲。
阿梁誒了聲,悄聲對謝識瑯道“該不會是大姑娘來見您了吧?”
他手里的折子驟然,正要起,卻又坐了下來。
“同說,我累了,要睡了。”
阿梁不明所以,只能照著謝識瑯的意思辦事,剛打開門,卻被來人嚇了一跳。
猜你喜歡
-
完結1961 章

重生後,我嬌養了反派鎮北王
亡國前,慕容妤是宰相嫡女,錦衣玉食奴仆成群,戴著金湯匙出生,名副其實的天之驕女。亡國後,她成了鎮北王的通房。這位鎮北王恨她,厭她,不喜她,但她也得承受著,因為全家人的安危都掌握在他手上。然而在跟了他的第五年,慕容妤重生了。回到她明媚的十五歲,這時候,威懾四方的鎮北王還隻是她宰相府的犬戎奴。未來的鎮北王掰著手指頭細數:大小姐教他練武,教他讀書,還親手做藥丸給他補足身體的虧損,噓寒問暖,無微不至,把他養得威風凜凜氣宇軒昂,他無以為報,隻能以身相許!隻想借這棵大樹靠一靠的慕容妤:“……”她是不是用力過猛了,現在
208.9萬字8.18 53236 -
完結474 章

小皇叔腹黑又難纏
那一夜,他奄奄一息壓著她,“救我,許你一切。”翌日,她甩出契約,“簽了它,從今以后你是我小弟。”面對家人強行逼婚,她應下了當朝小皇叔的提親,卻在大婚前帶著新收的小弟逃去了外地逍遙快活。后來,謠言飛起,街頭巷尾都在傳,“柳家嫡女不知廉恥,拋下未婚夫與野男人私奔!”再后來,某‘小弟’摟著她,當著所有人宣告,“你們口中的野男人,正是本王!”
137.3萬字8 103194 -
完結46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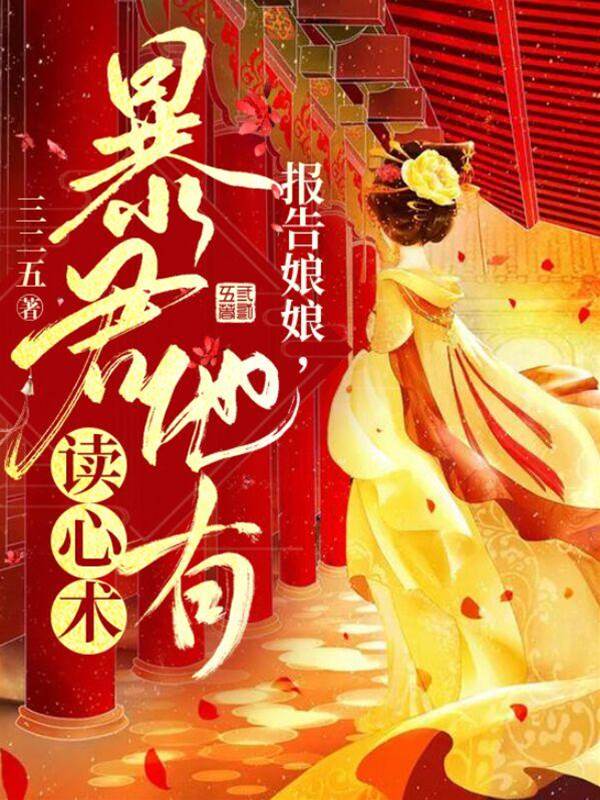
報告娘娘,暴君他有讀心術祝無歡鳳長夜
(雙潔 沙雕 救贖 爆笑互懟)穿越成史上死得最慘的皇後,她天天都想幹掉暴君做女皇,卻不知暴君有讀心術。暴君病重她哭求上蒼,暴君正感動,卻聽她心聲,【求上蒼賜狗暴君速死,本宮要登基!】暴君為她廢除六宮,…
87.7萬字8 22402 -
完結321 章

別人御獸,我召喚老公
許靈昀穿越初就面死局,為了活命,她為自己爭取到參加覺醒大典的機會。別人召喚出來的都是毛茸茸,而她在眾目昭彰中,召喚了只凄艷詭譎,口器森然的蟲族之王。 世人皆知,皇女許靈昀自絕靈之地走出,憑一己之力將燕金鐵騎逼退千里,又將海異人族的殿宇攪得天翻地覆,其兇殘鐵血展露無遺。 但他們不知道的是,當月色拂過樹梢,猙獰可怖的蟲族將少女納入柔軟的腹腔。 再之后,殘暴血腥的蟲族,乖張缺愛的人魚,狂暴兇殘的魔龍,無序的古神混沌之主,都只為她一人——俯首稱臣。
63.6萬字8 291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