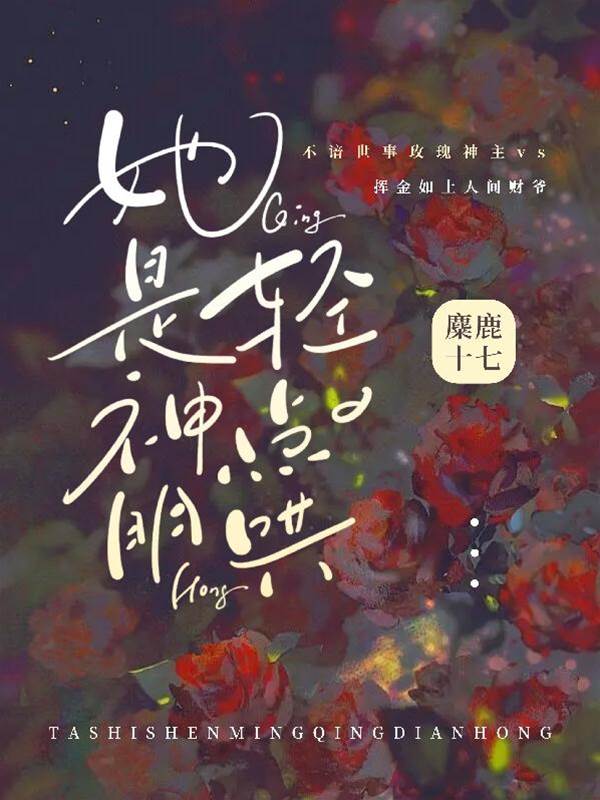《禍水》 第71章 我不是那個男人
病房溫度很高,梁紀深了外套,只穿襯衫西。
照舊一肅穆端正的純黑,線灼白,他逆著燈影,清瘦略窄的側臉也帶點淺淺的影。
“梁遲徽為什麼來外省,你清楚嗎。”
何桑看著他,“梁總來辦公事。”
“他的公事是什麼。”梁紀深平靜的眼底裂痕乍起,像發散的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梁氏集團在外省沒有投資,只冀省的錢都賺不完,不會輕易擴張。周家回歸,上面早不是當年那批人,老周也低調了,梁家本沒有競爭對手,何必多此一舉摻和外省的生意。”
他氣息不穩,低頭平復了許久,“我最后一回警告你,遠離梁遲徽。他做任何事,說任何話,三分真七分假,我都分辨不出,何況你。”
輸瓶的藥水沿著針尖流管,微涼微脹,何桑虛虛攥著十指。
梁遲徽的名聲確實毀譽參半,譽大抵是他明強悍,適合在商場統領三軍,為人慷慨有風度。毀倒是五花八門,商,狡猾沒底線,不仁不義過河拆橋,毀他什麼的都有,唯獨沒有毀他“對人壞”的傳聞。
“梁總沒理由坑我,我沒錢沒——”
“你謙虛。”梁紀深打斷,抬手拽了拽領,鎖骨也熱得緋紅。
他深,再覆上一層紅暈,顯得發,荷爾蒙暴增。
每次歡后,他軀也是汗涔涔發紅,如同水洗過,滴在何桑的鼻頭,小腹,似蠟油炙燙。
Advertisement
最迷那一刻的梁紀深。
簡直催到致命。
何桑也會壯著膽子索取他的溫存,很沉淪在過程里,更容易沉淪在激的前戲和纏綿的后戲里,被他猛烈地著,著,他強韌的舌頭侵略,沒有人不癡迷那樣昏昏醉的滋味。
“畢業在劇場混了三年了,除了我,誰不坑你?”梁紀深住臉蛋,向上撅起,有點恨鐵不鋼。
何桑撇開他手,他笑著,又住。
“你知道林敏嗎?”忽然問。
梁紀深淡淡應聲,“知道。”
冀省話劇圈的幾個一線大花旦,梁延章都捧場了,只不過有的只捧了一場,有的捧了十場。
林敏正當紅那陣,梁延章包過的場,也送了百八十萬的“鈔票花束”,后來林敏和市里的大人在燕郊度假村約會,消息傳出,他馬上收手了。
只打算玩玩,沒打算真格,犯不上得罪人。
基于此,無論梁延章表現得多麼好,多麼親近,何桑的危機也不大。
這種男人一輩子搞人不計其數,自己都記不清了,一個攻不下,攻下一個,不會在一棵樹上吊死。
可梁紀深明白,梁延章對何桑、對林敏,是截然不同的態度。
林敏是,何桑是翁瓊的影子。
多,舍棄就舍棄了,影子太難得。
“林敏出事之后,劇院的演員都擔心會重蹈的覆轍。”
梁紀深目定格在臉上,“你也擔心?”
Advertisement
“沒有人不擔心。”眼睫輕,“三年的地下,那個男人從沒承認過林敏。”
“一開始,是那個男人利用權勢威利,林敏不敢拒絕,不止不敢,到誰頭上,誰都不敢。飯局,聯誼會,商演,哪位老板的壽宴,邀請函遞到劇院,院長答應了,就要去,今天拒絕一個,明天再拒絕一個,上背景的,脾氣大的,院里承擔不起后果,自己也承擔不起失業的后果。”
給林敏作配的二號,是業的黃金b角,外市一位首富追追了很久,那位首富克妻,病死倆老婆了,雖說是迷信,可演藝圈很信奉,開機都得燒香拜一拜,誰愿意嫁克妻的男人呢,二號始終沒接。首富的親舅舅辦葬禮,白事宴請了去唱歌助興,圈子的規矩,紅白宴不許推辭,二號去了,被灌的酩酊大醉,轉天是院長開車去酒店接回的。
圈里唯一一場艷照門事件,給所有孩們提了醒。
吃小虧,避免吃大虧,撕破了臉,讓他們下不來臺了,斗不贏。
梁紀深默不作聲聽著,好半晌,“說完了?”
何桑音量很弱,“崔曼麗不會是第二個林敏。”頓了一秒,蠕,又抿住。
要說自己,終是沒說。
“你胡思想多久了?”
梁紀深坐在床邊,他沒想到何桑這樣敏,以為沒多心思,原來裝著這事。
又能忍,又逞強。
“我不是那個男人。”他摟住何桑,上幽幽的發香混合著汗味,“永遠不是,還擔心嗎。”
Advertisement
冷漠寡的男人,磁的嗓音在耳畔一聲聲地,一聲聲地喊,真是要了人的命。
“別想太多,先吃藥。”
梁紀深撕開藥袋,溫開水澆融了顆粒,半杯黑乎乎的沖劑。
“張。”
何桑最討厭喝中藥,下意識閉牙關。
“不張等我給你撬開?”
想到梁紀深也這麼摟著宋小姐,喂吃藥,親昵的,溫和的,比對自己更有耐心,心臟悶悶地不過氣,奪過藥碗,“我自己喝。”
男人手一撤,撲了個空,只抓到他的襯袖。
“老實坐好。”
梁紀深舀了一勺,何桑嘬得快,他喂得也快,沒咂出什麼苦味,杯子見了底。
只是喝藥的時候渾不安分,在他懷里磨來磨去的,甚至溢出點。
“磨什麼。”
“我...”
梁紀深結一滾,眼眸黯了黯,“哪。”
何桑沒察覺到男人的聲音不對勁了,“腰椎下面。”
他手指一探,乎乎的。
“怎麼又了?”
“是出汗,子太厚了。”
梁紀深又往下探,掐屁,“這嗎?”
話音才落,他狠狠一發力,掐得眼冒金星,眼中漸漸浮了淚花。
無形之中的勾人,最為窒息。
男人從風口袋掏出煙和打火機,敞開窗,手臂出,大口著煙。
由南向北的順風,煙味飄遠了,腹中那團火熊熊燃燒,愈演愈烈。
梁紀深完這支煙,滴流瓶也空了,他熄滅煙,摁下呼。
Advertisement
護士進病房掛上一瓶消炎,十分羨慕說,“您丈夫不眠不休,在病房守著您。”
酸苦的中藥刺激得何桑作嘔,藥涌上來,又流回去,順了順口,“他不是我丈夫。”
“您的未婚夫一直寸步不離——”
“我和他不。”
護士當場傻了,何桑腳后跟的里面長了一個膿包,正常只需注局部麻醉,這個男人考慮到中途蘇醒會害怕,掙扎中發生意外,提出下半麻醉,連手簽字都是他簽的。
細心,,又英俊。
一手包攬了家屬的活兒,給穿病號服,穿,指節剮蹭在的私,也毫不忌諱。
竟然不是夫妻。
梁紀深不冷不熱瞥了何桑一眼,朝護士道謝,“有勞了。傷口疼,在和我置氣。”
護士又檢查了的后狀況,“何小姐的腳太薄了,剜膿包的刀口也深,痛是會大一點。”
男人蹙眉,“有辦法緩解嗎。”
“冰敷吧,敷腳趾和腳踝,千萬不要沾紗布了。”
護士走后,梁紀深一把扯住何桑,單膝跪在床頭,另一只腳裹著紗布固定在床尾,完全彈不了,扭曲著。
猜你喜歡
-
連載1933 章

影帝偏要住我家
電影首映式上,記者看到夏思雨脖子後痕迹:“這是什麽?”夏思雨不在意的撩了撩耳畔長發:“蚊子咬的。”回家後,薄言把她按在牆邊,聲音戲谑而危險:“蚊子?要再給夫人複習壹下嗎?”*夏思雨是易胖體質,每每因爲變胖被嘲:“胖如懷孕。”某天她又又又被嘲上熱搜,本以爲還是壹次笑話。誰知影帝薄言回複:“謝謝大家的祝福,寶寶已經三個月了。”1V1雙處,霸氣禦姐+高冷男神
202萬字8 7160 -
完結96 章

先婚後愛
婚后第三個月,簡杭和秦墨嶺還是分房睡。這樁婚事是秦家老爺子定下,秦墨嶺對她沒感情。在外人眼里,家庭普通的她嫁到秦家是飛上枝頭變鳳凰。不少人等著看她成為豪門棄婦的笑話。…
37.8萬字8.25 117258 -
完結13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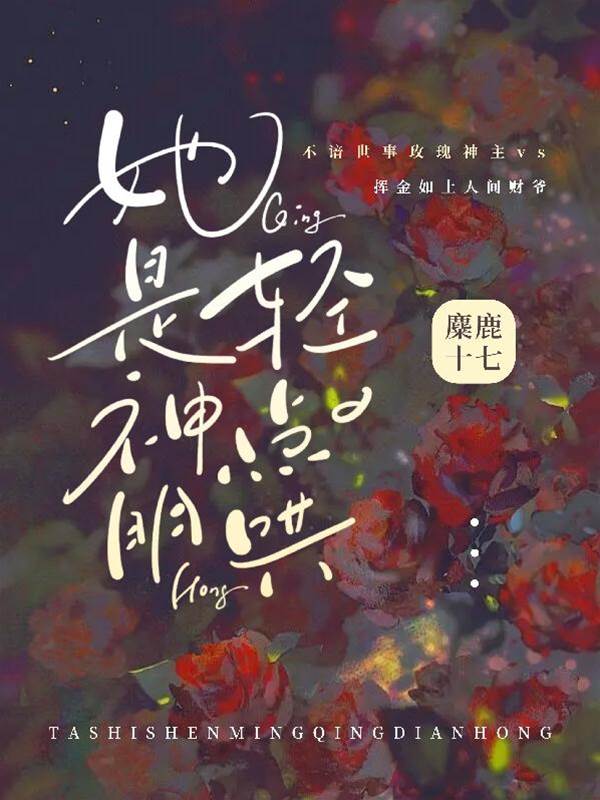
她是神明輕點哄
[不諳世事玫瑰神主VS揮金如土人間財爺][先婚後愛 雙潔+情有獨鍾+高甜]“她牽掛萬物,而我隻牽掛她。”——柏聿“愛眾生,卻隻鍾情一人。”——雲窈雲窈有個好的生辰八字,擋災的本事一流。不僅讓她被靈蕪城的豪門喬家收留,還被遠在異國,家財萬貫的柏老爺給選中做了柏家大少爺柏聿的未婚妻。—雲窈喜歡亮晶晶的寶石和鑽戒,豪門貴胄笑話她沒見過世麵,柏總頓時大手一揮,寶石鑽戒一車一車地往家裏送。—雲窈有了寶石,想找個合適的房子專門存放,不靠譜的房產中介找上門,柏太太當機立斷,出天價買下了一棟爛尾樓。助理:“柏總,太太花了十幾億買了一棟爛尾樓。”男人麵不改色,“嗯,也該讓她買個教訓了。”過了一段時間後,新項目投資,就在那片爛尾樓。柏聿:“……”—柏聿的失眠癥是在雲窈來了之後才慢慢好轉的,女人身上有與生俱來的玫瑰香,他習慣懷裏有她的味道。雲窈卻不樂意了,生長在雪峰上的玫瑰神主嫌棄男人的懷抱太熱。某天清晨,柏太太忍無可忍,變成玫瑰花瓣飄到了花盆裏,瞬間長成了一朵顏色嬌豔的紅玫瑰。殊不知,在她離開他懷抱的那一瞬就已經醒過來的男人將這一切盡收眼底…他的玫瑰,真的成精了。
23.9萬字8 7167 -
完結316 章

救命!離婚后豪門大佬纏歡上癮
多年仰慕,三年婚姻,一直都是一個干凈的身體。 她心甘情愿為他付出一切,甚至于雷暴天氣也拿著合同屁顛屁顛的送了過去,那晚…… 追妻火葬場+團寵+1v1+先婚后愛
46.7萬字8.18 794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