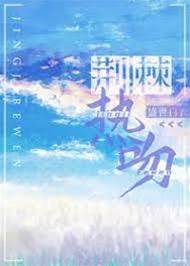《步步深陷》 第53章 攻心計
殷怡沖到馮斯乾的床邊,大聲質問,“你為什麼不正面回答我?”
馮斯乾專注批閱合同,“你不清醒。”
一把奪過他手中的文件,“你答應我留下孩子的,你親口答應的!”
馮斯乾惻惻的目掠過,殷怡同他四目相視,手一,文件頃刻掉落。
他重新拾起合同,“你自己沒保住。”
殷怡踉踉蹌蹌朝半敞的門板摔去,本能抓住門把手,才勉強站穩,“你說得沒錯,是我自己保不住,怪不了別人。”
馮斯乾一言不發打量。
殷怡絕站立,“誰通知我去廠樓的。”
“你認為呢。”
殷怡看向他,電火石間,瘋了似的,“不可能!”激大吼,“他不可能害我!”
馮斯乾冷笑,以此提醒,自己沒有說話。
殷怡頓時連哭聲都止住。
這才意識到是猜忌紀維鈞,是一點點識破了他利用的面目。紀維鈞去廠樓,是準備在招架不住馮斯乾之際,挾持勒索,逃生。殷沛東活一日,馮斯乾都要顧念殷家,保全婚姻,他無法對殷怡的安危置之不理,更不能不理。
“其實你一清二楚。”馮斯乾說完這句,便不再開口。
殷怡跌坐在墻。好一會兒,嘶啞說,“我不會和他來往了。”
馮斯乾翻頁的手勢一頓。
殷怡哭著,“孩子沒了。斯乾——”哽咽喊他名字,“你過離婚的念頭嗎。”
馮斯乾定格在合同上的文字,“沒有。”
殷怡問,“現在呢。”
他瞇著眼。
Advertisement
“假如沒嫁給我舅舅,你會嗎。”
馮斯乾又一次扣住文件,他略有不耐煩,“殷怡。”
“你只坦白會不會。”殷怡打斷他。
許久,馮斯乾答復,“不會。”
殷怡的子徹底下來。
我將殷怡的每一個反應都清晰納眼底,當一個人對舊失,帶給幾乎摧垮的真相,會認命接自己的現狀,甚至這種認命會潛移默化轉為的甘愿,只要這個讓認命的男人有半分值得。
我的直覺和經驗告訴我,以后馮斯乾要離婚,恐怕殷怡也不會離了,視紀維鈞為自己離婚后的退路,而退路已然坍塌,從現實到都崩塌了,殷怡沒有逃這段婚姻的沖和理由了。
我扭頭走回隔壁,殷怡也恰好從病房出來,整個人失魂落魄,可當看到我的時候,像是被什麼擊中,下一秒撲過來廝打我,“韓卿,你報復我,你報復我是不是!”
我單跳著閃躲,“殷怡,你冷靜點。”
得我節節敗退,“紀維鈞癱瘓,是你造的。”
“他自作自。”我扼住殷怡扇打我掌的右手,“如果他完好無恙,出事的會是我,以及你的丈夫。”
“馮斯乾是為了救你!”殷怡使勁掄打擺我桎梏,“你害了紀維鈞,還足我的婚姻。”
“是你雇傭我的!”我力掙扎,“你改變了初衷,可最初易時我問過你,這副局面是你口口聲聲要求我做到的。”
殷怡失去了理智,在場的保鏢沒料到會出現這麼混的一幕,誰也沒膽子貿然行得罪哪一方,都怔在原地,殷怡持續占上風,林宗易的保鏢挪了兩步試圖控制住,被馮斯乾的保鏢阻截,兩撥人馬手對峙,拎著糕點返回的保姆發現殷怡在拉扯我,驚慌失措擋住,“什麼人啊,手打我家太太!”
Advertisement
殷怡搪開保姆,接著舉起的手被馮斯乾遏制在半空。
馮斯乾一推,推開了殷怡,他側吩咐保鏢,“送太太回家,寸步不離守住。”
他面孔比先前更蒼白,微皺著眉頭,似乎在忍什麼,我借著過道
#每次出現驗證,請不要使用無痕模式!
的看清他小包裹的紗布滲出一道新鮮痕,聞聲趕來的護士急忙摁住出的部位,殷怡也被目驚心的漬唬住,愣在那,馮斯乾沒再多言,面容沉走進病房,保鏢隨即關上門。
保姆蹲下撿起被踩爛的糕點,“太太,我再買一份。”
我回過神,面無表從上面過,“不用,沒胃口。”
我一直睡到下午,林宗易傍晚回來,在門外詢問我的況,保鏢如實相告,他抑著緒,掉西裝隨意丟在沙發上,手掀開被子,佇立于床頭俯視我,“你去隔壁做什麼。”
我平躺沒。
林宗易忽然擒住我手腕,他使出的力氣并不大,可他的氣場人,我不得不順從坐起。
“他是死是活和你沒關系。”
我不言語,只一味抿。
我手在林宗易溫熱的掌中,“名義夫妻也是夫妻,多雙眼在監視。”
我垂著頭,“昨天我疏忽了。”
他松開手,解著領帶,在窗下獨自平復良久,轉走向我,語氣和緩了不,不似剛才那般強,“嚇到你了。”
我抱膝蜷在一團雪白的被子里,看著林宗易。
他掌心罩在眉骨上,拇指和四指分開,指腹按著太,“韓卿,我很累。”
我眼珠了。
Advertisement
他卻閉著眼,“我不是干涉你,我擔心這樣的意外發生第二次。”
我抬眸注視他,“劉桐從蔚藍海岸跟上我的,跟到茶樓。”
林宗易睜開眼,“你依然疑心我。”
“你命令手下調虎離山,用什麼調。”我劇烈抖著,“宗易,你的利用太可怕。”
我慢慢下床,“但凡馮斯乾晚一步,劉桐的下場就是我的下場。”
他也注視我,“不是我。”
我掩住面龐,“宗易,你還有什麼計劃,我求你不要不擇手段。”
林宗易重復,“不是我,韓卿。”
我等待他往下說,他卻停住,“我也在查。”
他靠近我,他手背我的剎那,我猛地一激靈,慌張后退。
大約我的表現讓林宗易無從著手,他緩緩收回,沉默抄起西裝,從房間離去。
我聽到他對保鏢說,“照顧太太。”
林宗易踏進電梯,兩扇金屬門合攏,他消失在九樓。
之后的五天,林宗易沒有再現,蔣蕓來過一趟醫院探我,我委托打聽會所和華京的消息,轉天在電話里告知我,會所被查封,無限期停業,男人說業都猜測馮斯乾在幕后出手了,商人之中他上面的人脈最廣,并且都很買他面子。至于華京,暫時沒有大靜,殷沛東在醫院閉門謝客,只有殷怡和一位姓孟的律師頻繁出。
我著手機,“林宗易呢。”
蔣蕓說,“上下打點唄,不過夠嗆,我老公說娛樂場子彎彎繞繞很復雜,林宗易經手的生意也不干凈,托關系要向對方擺明門道的,他沒法亮明,馮斯乾是算準了他的為難,才一擊致死搞他這家會所。”
Advertisement
我終止通話,端詳著輸壺里的褐藥水,保姆將打好包,擱在窗臺上,“太太,先生又來電話了。”
我嗯了聲。
“您和先生吵架了嗎,他每天早中晚按時打電話,卻不親自來。”
我躺下,著窗外的藍天白云,“沒吵。”
保姆很識趣,盛了一碗粥放在桌上,不聲不響出去。
馮斯乾比我早一天出院,他中午辦手續晚上走的,我是第二天早晨回到蔚藍海岸。林宗易沒接我,他派了司機接送,我下車,保鏢跟隨我上樓,出電梯的工夫,我收到馮斯乾的短訊,只一行字今天出差。
我刪除,進屋洗了個澡,兩名保鏢就在客廳和天臺一邊梭巡一邊煙。
我洗完走出浴室,停在客房門口推門而,床鋪是我那天離開的樣子,異常整潔,林宗易這幾日應該沒在家里睡。我猶豫了片刻,電話打過去,他接聽,我說,“保鏢撤了吧,我進出不方便。”
林宗易沒出聲。
我退出客房,徑直回主臥,“以前的仇人聽說我們結婚了,不可能再尋仇了。”
林宗易沒拒絕,“好。”
我說,“你多注意休息。”
他又陷靜默。
我掛斷電話。
外面的保鏢接到林宗易的指令,和我打了招呼就走了,我收拾好行李,帶了幾件換洗,拉著箱子下樓,直奔泊在后門的銀賓利,坐進后座。
馮斯乾全神貫注用筆記本理公務,我戴上眼罩,上車開始睡覺。
12點50分到達機場,在頭等艙休息室吃過午餐,2點半準時登機,我上機后放平座椅,側躺睡覺。
“你很貪睡。”全程無話的馮斯乾突然問了我這一句,他漫不經心端起紙杯,“肚里有貨了。”
我背對他蹙眉,“你缺孩子嗎。”
他喝了一口純凈水,“殷怡的沒了。”他意味深長笑,“所以我更期待林太太生下一個。”
我一聲不吭。
馮斯乾喝完那杯水,繼續辦公審閱文件,我繼續睡。
飛機降落是5點45分,一輛奔馳suv在接機口,一名年輕男子接過馮斯乾的行李箱,“馮董,有一隊考察團在本市,和索文集團有關,您要見一見嗎。”
馮斯乾抬腕看表,“安排到明天。”
男人駕車穿梭過市中心,送我們抵達在城市另一頭的酒店,馮斯乾預定了頂層的觀景套房,進門的瞬間,他一手合住門,一手攬住我腰肢,他鼻息的氣量極重,像一座呈發之勢的火山,我后背著玄關的墻壁,胡擺頭躲開他,“你有傷。”
他臉埋在我順的烏發間,揭過一縷縷凌長發,瓣磨蹭著耳,“痊愈了。”
我抵住他胳膊,“你沒留疤嗎。”
他只顧撥我,回復很簡短,“留了。”
我說,“我腳心也留了疤。”
馮斯乾摟著我,朝靠窗的里間走去,他薄沿著我面頰和頸部游移,我自始至終毫無容,他停下,鉗住我下,“不想是嗎。”
我看著自己折在他瞳孔的模樣,“我困了。”
“怎麼。”他發了狠,“看來林宗易很厲害,平常喂足了林太太。”
我沒有辯駁,他按下一按鈕,燈全部關閉,連天窗的紗簾也落下,馮斯乾極為熱衷在沒有亮的深夜,他要完全主導,釋放自己藏的面目,這張面目他不許任何人窺探了解。
我過他淋淋的頭發,像網一樣剛,發茬很短,刺疼我指尖,那種屬于他的炙熱的汗和冷冽的香味,在浸泡我的靈魂。汗水從他額頭,脖子以及膛甩落,滴濺在我飄的發梢,我為他強悍的力量淪落,也為我們匿于黑暗角落的相融而恥。
我和馮斯乾之間的與,纏與恨,在夾里盤而生,從不見天日。不止我在抗爭七六的人,馮斯乾曾經一定也想過碎它,扼殺在無盡的黑暗里,永遠不與人知,就當它不曾存在這世上。
也許由于它的每一刻都忌而刺激,也或者從來不的人一旦
猜你喜歡
-
完結13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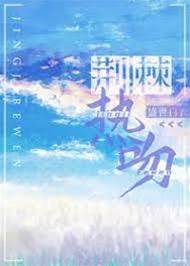
荊棘熱吻
季弦星有個秘密,她在十六歲的時候喜歡上了一個人——她小舅的朋友,一個大她八歲的男人,后來,無論她怎麼明示暗示,鐘熠只當她是小孩。她安靜的努力,等自己長大變成熟二十歲生日那天,她終于得償所愿,卻在不久聽到了他要訂婚的消息,至此她一聲不響跑到國外做交換生,從此音訊全無。再見面時,小丫頭長的越發艷麗逼人對著旁邊的男人笑的顧盼生輝。鐘熠走上前,旁若無人的笑道:“阿星,怎麼見到我都不知道叫人了。”季弦星看了他兩秒后说道,“鐘先生。”鐘熠心口一滯,當他看到旁邊那個眉眼有些熟悉的小孩時,更是不可置信,“誰的?”季弦星眼眨都沒眨,“反正不是你的。”向來沉穩內斂的鐘熠眼圈微紅,聲音啞的不像話,“我家阿星真是越來越會騙人了。” 鐘熠身邊總帶個小女孩,又乖又漂亮,后來不知道出了什麼事,那姑娘離開了,鐘熠面上似乎沒什麼,事業蒸蒸日上,股票市值翻了好幾倍只不過人越發的低沉,害的哥幾個都不敢叫他出來玩,幾年以后,小姑娘又回來了,朋友們竟不約而同的松了口氣,再次見他出來,鐘熠眼底是不易察覺的春風得意,“沒空,要回家哄小孩睡覺。”
51.8萬字8.18 229742 -
完結74 章

沉浮你懷中
[1] 被迫學游泳的那個夏天,談聽瑟見到了父親為她找來的“老師”。 “你就是小瑟?” 聞名商界、閱歷深沉的男人此時渾身濕漉漉的,目光像幽然池水,令她目眩神迷。 他給她高壓生活中片刻喘.息的自由,給了她人生中缺失的在意與關愛,那場芭蕾匯演的觀眾席里他是唯一為她而來的人。 談聽瑟的木偶式人生中忽然燃起叛逆的勇氣,她青澀地學著引誘,故意換下保守泳衣穿上比基尼出現在他面前。 終于那次酒后,他們有了一晚。 “你父親知不知道你做了什麼。”他站在床邊,明明笑著,目光卻冷靜而陌生,“我有未婚妻,你現在準備扮演什麼角色?” 這個男人從不是什麼慈善家,利益至上的商人骨子里是冷血,為了一份人情,對她的好只是冷眼旁觀的偽裝。 [2] 一句氣話而已,陸聞別以為沒必要解釋,直到得知她遭遇了游輪事故,失蹤后生死未卜。 幾年后一支水下芭蕾的視頻爆紅,陸聞別和無數人一起看著大廈LED屏將這支視頻循環播放。 視頻里的舞者,正是令他執念了兩年多、又死而復生的人。 她與嚴家少爺在宴會上言辭親昵,面對他時卻冷冷道:“陸聞別,我們別再見了。” 陸聞別以為自己能做到再也不見。 然而談聽瑟落水的那一刻,他想也不想就跟著跳下去將她救起。 原本光鮮倨傲的男人渾身濕透地半跪在她身側,眼眶被種種情緒染紅。 “你和他什麼關系?” 她微笑,“玩玩而已。” “玩?”他手指顫抖,“我陪你玩。” “抱歉,陸先生。”她濕漉漉的腳踩在他胸口上,將他推開,“我對你這種老男人沒興趣。” 夏日滾燙,她曾沉浮在他懷中。 原來他這些年的人生,還不如她掀起的一小朵浪花有滋味。 【男主說的氣話,沒未婚妻|年齡差十歲】
26.6萬字8 7365 -
完結1738 章

閃婚嬌妻:老公,深深愛
新婚夜。她被逼進了浴缸里,哭著求饒,“顧靖澤,你說過不我們是假結婚的。”他狠狠逼近,“但是是真領證了!”第二天.“顧靖澤,我還要看書。”“你看你的,我保證不耽誤你。”要不是一時心灰意冷,林澈也不會一不小心嫁給了這個看似冷若冰霜,其實卻熱情無比的男人……
304.1萬字8 74320 -
完結1105 章

重生之國民男神
【本文女扮男裝,重生虐渣,酸爽無比寵文+爽文無虐,雙強雙潔一對一,歡迎跳坑!】前生司凰被至親控制陷害,貴為連冠影帝,卻死無葬身之地。意外重生,再回起點,獲得古怪傳承。司凰摸著下巴想:這真是極好的,此生必要有債還債,有仇報仇。*重臨娛樂王座,明裡她是女性眼裡的第一男神;執掌黑暗勢力,暗中她是幕後主導一切的黑手。一語定股市,她是商人眼裡的神秘小財神;一拳敵眾手,她是軍隊漢子眼裡的小霸王。嗯……更是某人眼裡的寶貝疙瘩。然而有一天,當世人知道這貨是個女人時……全民沸騰!*面對群涌而至的狂蜂浪蝶,某男冷笑一聲:爺護了這麼久的媳婦兒,誰敢搶?「報告首長,李家公子要求司少陪吃飯。」「查封他家酒店。」「報告首長,司少和王家的小太子打起來了。」「跟軍醫說一聲,讓他『特別關照』病人。」「啊?可是司少沒事啊。」「就是『關照』王家的。」「……」*許多年後,小包子指著電視里被國民評選出來的最想抱的男人和女人的結果,一臉糾結的看著身邊的男人。某男慈父臉:「小寶貝,怎麼了?」包子對手指,糾結半天才問:「你到底是爸爸,還是媽媽?」某男瞬間黑臉:「當然是爸爸!」小包子認真:「可是他們都說爸爸才是男神,是男神娶了你!」某男:「……」*敬請期待,二水傾力所作現代寵文,劇情為主(肯定有感情戲),保證質量!請多支持!*本文架空,未免麻煩,請勿過度考據!謝謝大家!
221.2萬字8 10214 -
完結498 章

寵妻100式:爹地放開我媽咪
她舍不得,卻要繼續掙扎:“你都是有孩子的人了,為什麼還揪著我不放?”“因為,我愛你?”他抱得更加用力了。她心中一軟,但還是不愿意就范,”你孩子他媽怎麼辦?“”你來做孩子他媽。”他有點不耐煩了,就在她還要說話的瞬間,吻上了她的唇。“你要我做后媽?”
85萬字8 4764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