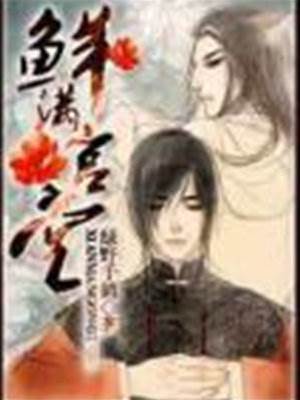《懸日》 第54章 N第章 燃燒余溫
接吻了。
蘇洄的視線被灰白的煙所覆蓋,腦中似有散不去的濃霧,理智被酒控,神志不清,還以為自己真的回到了過去。
只有過去的寧一宵會吻他。
他說自己27歲了,蘇洄覺得他在撒謊,21歲的寧一宵才會吻他。
或者是夢嗎?還是他的幻覺?是不是病又變嚴重了……
困與念織著,充斥在蘇洄每一神經,或許寧一宵真的擁有某種會令他致幻的東西,他的氣味或是唾,蘇洄不確定,但他此時此刻仿佛躺在一整片大而廣袤的草坪,那里下了很大的雨,很濃的霧,草尖著他的皮,很,令他想起來,而寧一宵就在眼前。
所以蘇洄用手掌撐在地面,真的起,出一只手上寧一宵的臉。
他的眉眼垂著,從皮里出酒與,像條泛著水的蛇,攀上來,所有的都如水般涌頭腦,模糊真實與夢境的邊界。
是夢吧,蘇洄有些害怕。
他很怕自己靠近,寧一宵就消失了,變蝴蝶或影子,再也不出現,夢每次都是這樣結束的。
所以他很小心,一雙眼包含潤的水汽,很輕地問:“可以……親嗎?”
眼前的寧一宵并沒有消失,也沒有回答,就這樣看著他,很像過去。
蘇洄忽然掉了一滴淚,在沉重又急促的呼吸下,抬頭吻住了寧一宵的,準確說是很輕地含住了他的下,慌張和畏懼就像是一張輕的薄紗,隔在他們之間。
鼻梁著鼻梁,蘇洄知著這個真實的呼吸,與之融,對寧一宵的還是倒一切,舌尖探進去,激起的卻是自己渾的栗。他幾乎站不住,半倒在寧一宵懷里,卻沒有被他擁抱,蘇洄下意識地到難過。
Advertisement
“抱我……”齒糾纏的間隙,他提出很不像命令的命令,更像是哀求。
但如愿以償了。
蘇洄昏昏沉沉地用這個綿長的吻,在酒的作用下,褪下明知不可為的枷鎖,忘記了這些新的朋友,忘了紐約討厭的冬天、結冰的街道、吃過的苦頭、電擊、封閉,所有可怕的東西都被拋諸腦后。
此刻他變回六年前那個蘇洄,不害怕失敗,想要的一定會得到。
寧一宵沒料到還會有第二個吻。
一別多年,蘇洄將自己的藏得很好,偶爾泄出的一點令人的緒,似乎也并不只指向自己。從蘇洄的表現上來看,他并不特殊了。但寧一宵總是自欺欺人地覺到什麼,很模糊的,折磨著他。
或許那不足以稱之為,但或許很靠近。
哪怕只有一些好,寧一宵也不想放棄,他要的一定要得到。
只是他不明白,蘇洄主與他接吻時,為什麼會掉眼淚。
他吻去蘇洄邊的淚水,咸的,但很快被蘇洄的舌尖勾走,往更深去。蘇洄的手垂下來時不小心到蛋糕,小指沾滿了油。他抬起手,毫無意識地了幾下,完全不知道這畫面有多麼強烈的暗示。
于是這由寧一宵代勞了。
油把一切都弄得很糟。
蘇洄快要接近昏迷了,他有些接不上氣,呼吸急促,伏在寧一宵肩頭。
突然地,客廳傳來聲響,似乎有什麼掉到地上,寧一宵明顯覺到蘇洄的瑟了一下,但還沒有停止親吻他的側頸。
來不及將蛋糕裝進盒子里,寧一宵將蘇洄攬在懷中,另一只手將蛋糕放回冰箱,關上了門。
廚房一下子暗下來,被淡藍的氣包圍。
Advertisement
蘇洄的又燙又,被寧一宵打橫抱起來,手都搭不住他的脖頸。
寧一宵知道他喝醉了,完全不清醒,所以并不打算真的要做什麼,這樣太不公平。
盡管他的理智也被磨得所剩無幾,但至能思考。
“睡吧。”他將蘇洄放回他的床上,自己半跪在一旁,替他將被子打開來,蓋好。
可蘇洄像是本聽不懂他說的話,蜷著靠過來,像小貓一樣用額頭近了他的,小聲呢喃著什麼,但寧一宵聽不清。
他低了低頭,“你說什麼?”
蘇洄用手摁住床墊的邊緣,有些艱難地支起上半,低頭吻寧一宵的膝蓋,又抬頭,用漉漉的眼著他。
“不要走……”
不要消失不見。
脆弱的防線最終還是崩塌,面對蘇洄,寧一宵總是認輸。
在這個新舊接的夜晚,他們毫無預兆地越過了安全線,蘇洄進攻的姿態都是輕盈的,像只蝴蝶。
寧一宵打開了他的羽翼,又一次看到了他骨延上去的紋,那行他悉的英文。
他無端想起克伊形容蘇洄的反差,說他看上去很,卻迷穿孔。
但誰都不知道,蘇洄也會有這樣的一面,浪又純真,危險又脆弱。
這樣的他,寧一宵不愿與世界上的任何人分,某一刻他希全世界的人都消失不見,只剩下他們二人,這樣蘇洄別無選擇,只能與他在廣袤而孤獨的地球共度漫長,直到死去,連墓碑都要連在一起。
蘇洄姿態旖旎,在他耳邊說“生日快樂”,像世界上最好的禮。
于是寧一宵原諒了他不自己的名字,也原諒他不說“我你”,盡管這都在意料之中。
他起,手臂撐起,將黏白的吐在蘇洄的邊,告訴他,你不是很喜歡海嗎?
Advertisement
你自己嘗起來就很像海。
房間里彌漫著黏膩的氣味,仿佛這里流淌出一小片夏天。
蘇洄昏睡在寧一宵懷中,渾塌塌的,不省人事。寧一宵替他稍作清理,換睡的時候發現他還是很燙,不太正常,于是給他測了溫,38度7。
不幸被他言中,蘇洄的確冒,還發了燒。
寧一宵找來退燒藥,花了點功夫喂他吃下去,又用了理退燒的方法,拿出冰袋給他敷額頭,也替他拭了,折騰了兩個小時,燒好不容易退下去,他這才放了心。
通常進躁期,蘇洄的睡眠都很短,有時候本不需要,一整晚都無比興,甚至沒辦法待在一個空間里太久。
但這次喝得爛醉,加上冒發燒,他昏睡了很久,再醒來天已經大亮,半掩的窗簾明亮的雪。
外面好像下雪了。
有這樣的預。
蘇洄頭很痛,就像被什麼鈍狠狠地砸過,昏沉又疲倦,思維一下子有些短路,只迷迷糊糊記得和他們一起喝酒聊天。
被子好暖,蘇洄下意識想放棄思考,閉眼再睡一會兒,于是又往里鉆了鉆。
他覺不太對勁,了,忽然地,一只手臂過來,抱住了他。
很悉、很的背后擁抱。
蘇洄一瞬間清醒了,他甚至不用回頭都知道這個人是寧一宵。
為什麼他們會睡到一起?
蘇洄努力地回想,支離破碎的記憶像拼圖般一點點復原,耳朵也逐漸變紅。
他被恥、焦慮與無以復加的懊惱困住,無法自拔,但還抱有一點點僥幸心理。
萬一真的是做夢呢?說不定寧一宵只是幫忙把喝得爛醉的他拖回房間,然后太累就倒在一起睡了。
Advertisement
畢竟他們都穿得好好的。
蘇洄又低頭確認了一眼,忽然發現不太對,昨天他穿的并不是這套睡。
呢……
下意識的逃避心理又開始作祟,蘇洄小心翼翼地拿開寧一宵的手臂,想溜掉。
但他并沒有得逞,不僅如此,還被寧一宵抓了個正著。
“醒了?”寧一宵的聲音有些啞,很低沉。
他沒完全清醒,半閉著眼,直接出手,覆在蘇洄的額頭上。
蘇洄完全不敢彈。
“……好像還有點燒。”
寧一宵忽然起,靠近了,用自己的額頭上蘇洄的,只是還閉著眼。
蘇洄的心幾乎要跳出口。
就這樣靠了十秒。
“還好。”寧一宵退開了,回到枕頭上,把蘇洄也拉回被子里,“蓋好,再著涼不管你了。”
蘇洄的心跳得愈發快起來,他本沒辦法和寧一宵在同一張床繼續呆下去,心臟好像會炸掉。
寧一宵卻本不管,轉又摟住他,下抵在他肩窩,很親昵的姿態。
“寧一宵,我想出去……”蘇洄試探地開口,很小聲,“我、我們……”
“現在?”寧一宵的鼻息溫熱,縈繞在他頸邊,他的聲音懶懶的,“可以啊?不過他們還在外面吧,看到了可能會誤會。”
他說完,又改口,“也不算誤會。”
完了。
蘇洄懷疑這本不是假的,不是做夢,他是真的做錯了事。
“我……”他不知道應該怎麼說,說些什麼好,“我昨天晚上喝得太醉了……”
寧一宵還是閉著眼,“嗯,繼續。”
要怎麼繼續說啊?
蘇洄腦子一片空白,本不知道怎麼辦。
他只好扯謊,“我好像有點斷片……”
寧一宵聽了,低聲笑了一下,笑聲里著說不清道不明的意味。他手,了蘇洄的下,“斷片的意思是你不記得了是吧?你主勾了我的脖子,親了我,記得嗎?”
蘇洄臉紅得像水桃,一掐就要流水。
“是你先親我的……吧?”
他真的不確定。
“嗯,記得這個。”寧一宵角平直,“其他呢?”
蘇洄說不出話,只想學鴕鳥把自己的頭埋起來認輸。
寧一宵靠近了些,嗓音低沉,忽然換了語言,“blowjht?”
沒等他給出回應,寧一宵又說:“如果還想不起來,我就再用說一遍,會不會印象更深刻一點?”
蘇洄被恥沖昏頭腦,捂住了寧一宵的,像小孩子念經那樣求饒,“別說了,別說了……”
他真的以為是夢,昨晚發生的一切太不真實,太不像現在的他們會做出來的事。
和前任不清不楚地攪到一起,簡直是世界上最蠢的行為,可蘇洄偏偏做了。
蘇洄試圖為自己辯解,“對不起,我昨天神志不清,搞錯了……”
寧一宵順勢咬了一口他的手,很痛,蘇洄下意識松開。
“搞錯?把我認其他人了?”寧一宵臉冷下來。
“不是!”蘇洄立刻反駁,但又沒有其他任何有力的話。
認六年前的寧一宵,算不算認錯……
他不知道。
蘇洄想立刻消失,現在馬上,哪怕突然落一道雷把自己帶走也好。
他把頭埋進枕頭里,決心不起來。
“那是什麼?”寧一宵不打算就這樣放過他,還在追問。
“沒什麼……”蘇洄悶聲悶氣,隨著記憶的逐漸復原,他的腦子便越來越,本沒辦法理智思考。
寧一宵了他的后頸,晃了晃,細白的脖頸上還殘留著他昨晚咬下的痕跡,“蘇洄,你26歲了,什麼時候能學會不逃避現實?”
被中了痛,蘇洄的神經愈發焦灼。
是啊,26歲的蘇洄喝醉了酒,想勾引21歲的寧一宵,結果被27歲的寧一宵狠狠咬住。
可他除了逃避現實,還能做什麼?
“那你呢?”他有些委屈,這又不是自己一個人的錯,“你為什麼要做這種事?”
寧一宵大言不慚,毫無歉疚,“因為你了。”
什麼?
蘇洄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舉手之勞。”寧一宵說。
“好了你別說了,求你了。”蘇洄捂住了自己的耳朵,以鴕鳥的方式在枕頭上逃避昨晚發生的一切。
躁期令他思維比之前更加快,像是有許多許多個自己在腦中吵架,誰都不愿意退讓。
他真的很佩服自己,意志力竟然可以薄弱到這種程度,明明答應了做朋友,也下定決心做一個稱職的朋友,沒想到最后還是被自己一手搞砸。
猜你喜歡
-
完結139 章

穿書后成了萬人迷
喬墨沉穿進了一本萬人迷耽美文。 文中主角愛慕者眾多,他只是其中的癡漢炮灰攻,出場三章就領盒飯。 為保狗命,喬墨沉努力降低存在感,遠離主角。 出新歌,參與紀錄片拍攝,編古典舞,為文明復原古地球的文化,沉迷事業不可自拔。 等到他回過神來注意劇情的時候卻發現原文劇情已經崩得不能再崩了。 萬人迷主角和原情敵紛紛表示愛上了他,為他爭風吃醋。 喬墨沉:???
36.5萬字8.18 6592 -
完結93 章

影帝
老流氓影帝攻X小癡漢鮮肉受 雙向攻略的故事^^ 甜度:++++++
24.5萬字8 5836 -
完結1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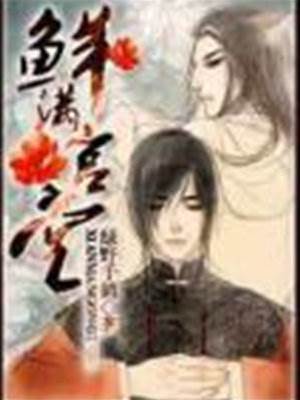
鮮滿宮堂
海鮮大廚莫名其妙穿到了古代, 說是出身貴族家大業大,家里最值錢的也就一頭灰毛驢…… 蘇譽無奈望天,為了養家糊口,只能重操舊業出去賣魚, 可皇家選妃不分男女,作為一個貴族破落戶還必須得參加…… 論題:論表演殺魚技能會不會被選中進宮 皇帝陛下甩甩尾巴:“喵嗚!”
35.5萬字8 7261 -
完結305 章

病美人替身不干了
沈郁真心爱一人,不惜拖着病体为他谋划、颠覆王朝,死后才知,他只是话本里主角受的替身,活该赔上一切成全那两人。 重生归来,一身病骨的沈郁表示他不干了。 这人,谁要谁拿去。 他则是代替了庶弟进宫做那暴君的男妃,反正暴君不爱男色,况且他时日无多,进宫混吃等死也是死。 进宫后面对人人都惧怕的暴君,沈郁该吃吃该喝喝,视暴君于无物。 青丝披肩,双眸绯红,难掩一身戾气的暴君掐着沈郁脖子:“你不怕死?” 沈·早死早超生·郁略略兴奋:“你要杀我吗?” 暴君:“?????” 本想进宫等死的沈郁等啊等,等来等去只等到百官上书请愿封他为后,并且那暴君还把他好不容易快要死的病给治好了。 沈郁:“……” 受:在攻底线死命蹦跶不作不死 攻:唯独拿受没办法以至底线一降再降
70.2萬字8 1596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