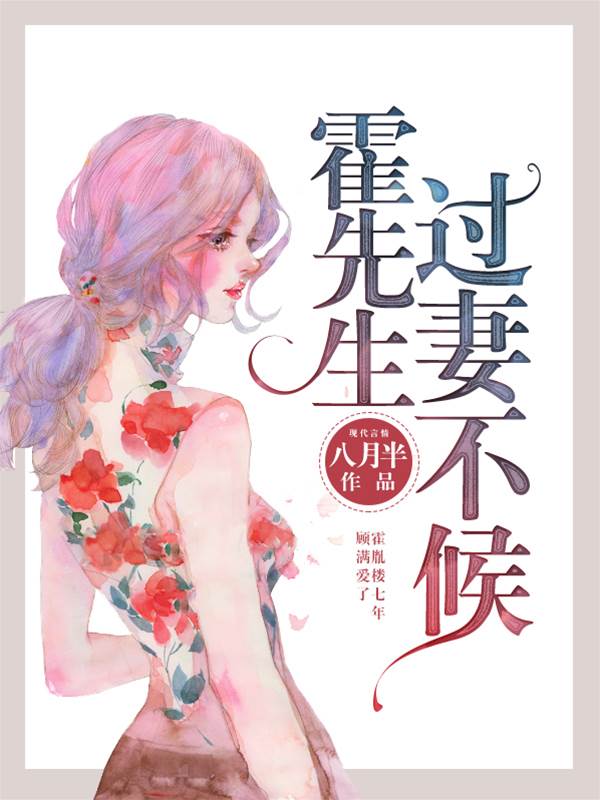《日夜相對》 第254章 小鹿亂撞
“……”手機那端沉默了數秒之久。許迎溫的聲音里藏著幾分說不清的忍:“那你……你什麼時候能忙完?”
“我有一件很要的事,想求你……”
已在盡量控制自己,可有些緒還是毫不自知的流了出來,然后被他敏銳捕捉。
陳敬洲的嗓音沉了沉,追問道:“怎麼了?”
他不問還好,這麼一問便徹底摧毀了構筑的心墻,所有抑的緒瞬間崩潰決堤,卸下所有心防暴了自己的脆弱。
“……陳清野抓走了小默,威脅我去酒店找他,我不想去…我好害怕。”
許迎斷斷續續的說:“可我也不能不管小默……”“如果我報警,一定會激怒陳清野的!他這個人無法無天,什麼事都干得出來,我怕……”
陳敬洲甚至沒聽完許迎說話,神愈發凝重,拿起一旁的車鑰匙,起不發一言的往外走。
他這突然的舉,令桌上三人俱是一愣。
管薇詫異的問:“洲哥,你要去哪兒?”
男人腳步未停,且步伐匆匆。
管薇和母親對視了一眼,來不及多想,立刻起去追:“洲哥!”
管薇踩著一雙高跟鞋追出了餐廳。
眼見男人已彎進了車里,再顧不得形象,快步跑過去試圖把人攔住:“喂!喂——”
Advertisement
管薇使勁兒拍了拍車窗,陳敬洲卻理都沒理,一腳踩下了油門!
車子打了個彎,很快便疾馳而去。
許迎一個人在家里坐立難安,等待著陳敬洲的每一秒鐘,都覺得時間好像分外漫長,索揣好手機下了樓。
室外夜沉沉。
濱海市的雨季,時常是這樣云籠罩的天氣。
許迎只拿了手機出來,也沒法去車上等他。
單元樓門口站了沒一會兒,就覺得酸,便心頹喪的找了個不擋路、不礙事的地方蹲著。
手機屏幕始終未息屏,出的泠泠亮照著發白的臉龐。
像只小兔子似的在個角落,沮喪的垂著腦袋,看上去無助又可憐。
陳敬洲開車趕到,從車上下來,一眼就注意到了蹲在那兒的人。
他頓時鎖起眉頭,加快步伐走了過去。
男人不沾一灰塵的皮鞋出現在許迎的視線中時,還沒來得及抬起頭確認,就先被那雙有力的大手撈了起來。
陳敬洲雙手扣在臂彎里,掌心溫度過那層薄薄的服傳遞而來,無比悉而又溫暖的氣息,令不由自主的心生依賴。
原本的恐懼與慌,好像瞬間被平。
但隨之而來的,是看似平靜之下,那搖搖墜的脆弱。
那是最真實的,最想要心偽裝的自己。
Advertisement
許迎眨了眨眼睛,嚨微堵,一時竟沒能說出話來。
倒是陳敬洲注意到手指上胡纏的紗布,皺起眉頭問了一句:“手怎麼了?”
許迎:“切菜的時候不小心被刀劃傷了。”
他握著的手,拇指指腹輕掐在掌心中,低頭仔細瞧了瞧,又問:“過藥了麼?”
許迎搖了搖頭,說:“傷口不深。”
見他眉心又鎖幾分,跟著補上一句:“不疼了。”
陳敬洲沒再松開手,溫熱的手心將牢牢地攥掌中,思索了一瞬,冷靜說道:“先去酒店。”
許迎:“嗯!”
……
……
希爾頓酒店。
陳清野洗了澡,系好浴袍從浴室出來,拿過手機看了眼時間,又緩步走到落地窗前拉開了玻璃門。
室外濃黑夜中風聲獵獵,偶爾吹進房間時,好像短暫的熄了他心尖火。
他站在窗前的矮幾旁點煙,腦海中旖旎景象揮之不去。
想起年時那無數個混沌夜晚里,他一遍遍不知疲倦地取悅自己。多胺旺盛分泌以后,再清醒時卻只有難言的無盡空虛。
他從來都不缺人,清純的、的,只要他想,多個都有。
但有些東西,一開始沒能得到,日子一久,就了執念。
再多相似的替代品,也無法填補他心頭蓬生長的。
Advertisement
陳清野想要許迎很久了。
從他為男人的懵懂意識覺醒開始,到現在歷盡千帆后心中火種仍然未熄…
他為什麼總盯著不放?
當然是想以他男人的份,好好“把玩”。
陳清野想著,結微滾,把煙送到間,閉著眼睛深深吸了一口。
他等的不耐煩了,心猿意馬、又心難耐。
無比焦躁的摁滅了手里的煙,又回趿著拖鞋去拿手機,想問問“到哪了”。
敲門聲卻恰好在這時響起。
陳清野沒多想,心頭似有小鹿撞,立刻放下了手機去開門。
門一打開,還沒等他看清什麼,來人忽然狠狠一腳踹在了他上!
陳清野措不及防,一晃,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肋骨疼痛難忍,他瞬間白了臉,劇烈的咳嗽了幾聲,咬牙切齒罵道:“你媽的陳敬洲,你這個瘋子!你想死是不是?!”
陳敬洲闊步上前,一把攥住了他浴袍外領!
陳清野被迫起子,抻到了肋骨被踹的傷,臉愈發難看。
陳敬洲眼神冷銳,一向緒不形于的他,此刻面上憤怒昭然若揭。
“是我想死,還是你想死?”陳敬洲說著,輕笑了一下,帶有幾分認真問:“我記得我早警告過你,你以為我在跟你開玩笑?”
“……”
Advertisement
陳清野額頭上冷汗直冒,卻一臉不服。
他張狂不可一世,從未把誰放在眼里,尤其是這個見不得的野種。
篤信不敢把他怎麼樣。
陳清野朝他后看了一眼,視線只在許迎臉上停了一秒,陳敬洲就忽然拽起他往臺上走!
十幾層的高樓上,深夜寒風凜冽,江邊千萬盞璀璨燈火此刻映在陳敬洲冷若冰霜的臉上。陳清野平生第一次到恐懼,再也顧不得肋骨的劇痛,求生本能使他拼命掙扎起來!
“你要干什麼?放開我!你他媽的,陳敬洲,你——”
“敬洲!”
他驚懼的喊聲驀地戛然而止。
被陳敬洲按在臺欄桿上的那一秒,陳清野了下。
許迎跟過來,也嚇得驚了一聲。
陳清野死死地抓著陳敬洲的服不敢撒手。
他半個都在欄桿外了,臉慘白如紙。
陳敬洲卻面無表,只冷冷的看著他,語氣也聽不出任何起伏,問道:“許默在哪?”
猜你喜歡
-
完結79 章

結婚三年我都不知道對方是大佬
夏春心和祁漾離婚了。 祁漾家里有礦山,卻裝了三年“修車工”! 夏春心家里有油田,卻裝了三年“家庭保姆”! 倆人三年的溫溫柔柔、相親相愛: 溫柔賢惠的夏春心:“老公修車辛苦了,你晚上想吃什麼呀?” 溫柔老實的祁漾:“老婆做家政也辛苦了,做個炒雞蛋就行,不想你太辛苦。” ——全是裝的! 某兩次倆人是在外面偶遇到: 祁漾當時開著豪車,沉默了一會兒說:“寶貝兒,這是來我修車廠客戶借我開的……” 夏春心穿著高定,咽了下口水說:“老公,這是我那個女明星客戶送我的……” ——全是謊話! 離婚當天: 夏春心用挖掘機把祁漾的十輛豪車給砸了。 祁漾把夏春心數億的頂級化妝品高定和奢侈包包全扔垃圾桶了。 離婚后: 夏春心:“祁漾,我懷孕了。” 祁漾:“………………” *斯文敗類嘴又毒狗男人X灑脫帶球跑病美人 #離婚帶球跑,追妻火葬場#
30.2萬字8 21374 -
完結646 章

君夫人的馬甲層出不窮
第一豪門君家有個瘋批少爺,傳聞發瘋時還殺過人,人人避而遠之。林星瑤頂替堂姐,成了瘋批少爺的沖喜新娘。大家都說,林星瑤這輩子算完了。沒過兩天,瘋了三年的君少忽然恢復神志。大家又說:“君少眼光高,肯定要離婚。”誰知君少寵妻入骨,誰敢動他老婆,立…
113.6萬字8 94857 -
完結3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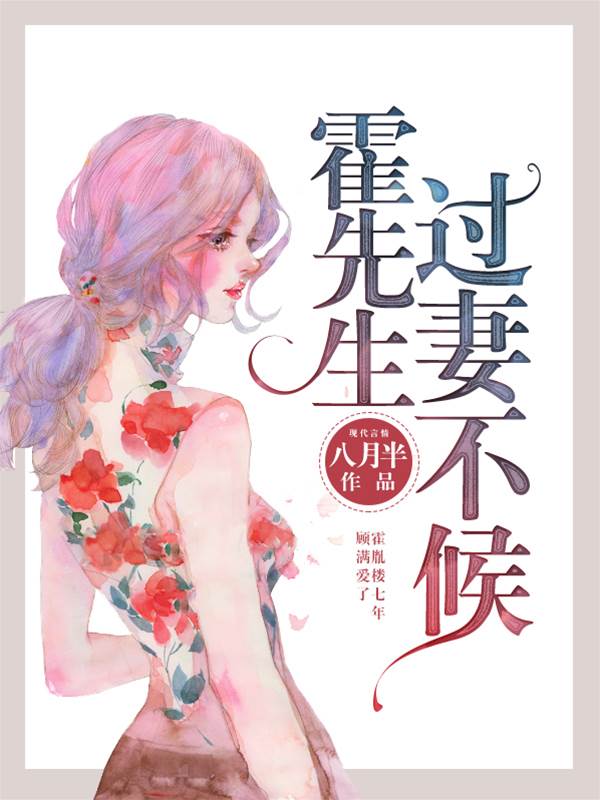
霍先生,過妻不候
顧滿愛了霍胤樓七年。 看著他從一無所有,成為霍氏總裁,又看著他,成為別的女人的未婚夫。 最後,換來了一把大火,將他們曾經的愛恨,燒的幹幹淨淨。 再見時,字字清晰的,是她說出的話,“那麽,霍總是不是應該叫我一聲,嫂子?”
29.6萬字8 83353 -
完結612 章

三億離婚!首富,夫人她是真豪門
離婚後,霍司爵才發現,他從沒真正的認識過他相處三年的小妻子。她不是個又窮酸又愚蠢的無知孤女嗎?可是為什麽。全球限量款豪車是她保鏢的座駕。億萬總裁是她身邊的跟班。保姆家裏的愛馬仕都堆成山。國際影帝為她先殷勤。首席大佬把她當座上賓。霍司爵看著處處跟自己作對的貌美前妻。“沒關係,等我跟京市公司強強聯合,一定能讓你重新對我俯首稱臣。“可是沒多久……“霍總,不好了,對方公司說不跟我們合作,因為,你得罪了他們家的團寵首席女總裁。”“……”怎麽辦,打不過,就隻能加入了唄。霍大總裁成了前妻身邊俯首稱臣天天求原諒的乖乖小男人!
107.2萬字8.18 2969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