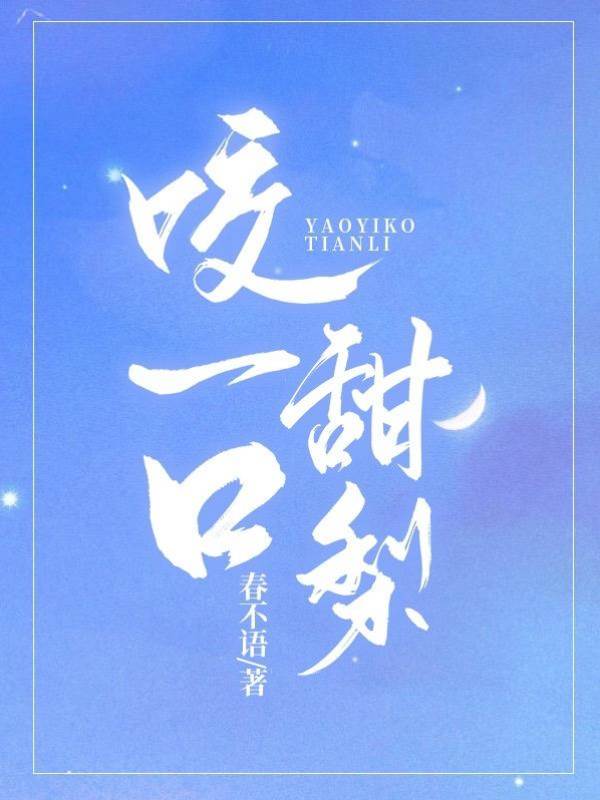《婚前破戒!我不做沈先生的心藥》 第228章 她不是自殺
這麽說來,沈斐真的是可惡的。
他總是說自己融不進人家沈家,如果真的是沈時倦說的那樣的話,什麽樣的家庭能讓他這樣融?融化的融吧。
我不想提沈斐了,不過沈時倦也功地把話題給拉跑偏了。
我以為他有意把話題給拉開,不會再繼續他和思儂分手的這件事,沒想到他自己又接著說。
“我跟思儂兩年,有很大一部分時間我都在國外,到後麵我們就經常吵架。“
“你該不會跟我說你早就不思儂了,你以前糾纏我隻是因為一種下意識,就像那些已婚的渣男在外麵騙小姑娘,都會說他跟他太太沒有了。”
“你放心,我不會洗白自己。”
“那就好,接下來的話我就能放心聽了,你繼續。”
我一邊大快朵頤一邊聽他說故事,豈不樂哉?
“聽說。”我接下來要放大招了,就不知道他能不能得了。
我抬起頭來看著他,順便看了看門口在找絕佳的逃跑路線,如果我接下來的話激怒了他,等會兒逃起來也比較便捷。
“據說思儂是自殺的?”
我等著他忽然崩潰翻臉,通常這種賣深人設的人,緒總是很不穩定。
出乎我意料他還平靜的,我探究地看著他,在想他是不是被我氣瘋了,平靜隻是暴雨前來臨的寧靜。
“我曾經這麽懷疑過,也查了當時出事故的整個過程,撞車的路段是有急剎車的痕跡的,也就是說當渣土車開過來的時候,嚐試急剎車和躲避,所以自殺的可能很低。”
“原來不是,所以你才這麽平靜?”
Advertisement
“當時喝了酒屬於醉駕。”
“所以你疚?”
“疚當然是疚的。”
“那就你跟提分手,你是真的不了還是...”
“我覺得我沒有那麽了,走了之後,我卻無法接,疚和自責控製了我,那段時間我發瘋地想讓活過來。因為我知道家隻有和媽媽兩個人,他去世了,對他媽來說是致命的打擊。”
“他媽媽一定很恨你,所以你不知道。他媽媽將他的心髒捐了出去。”
“是的。”
“我是不是殘忍的,專門在你的傷口上撒鹽?”我用手托著腮看著他。
“傷口痛了那麽久了,早就愈合結疤了,現在連疤痕都快消失得差不多了。”
“你別告訴我你快忘了思儂。”
“當然沒有忘,但是沒有以前那麽痛,我們異地的時候都維持不下去了,更何況一個人已經消失在這個世界上了,再深刻的都需要陪伴。”
我們今天的聊天話題居然有些深刻,沈時倦的好像也有那麽幾分道理。
“你是在為你上我這件事鋪墊?好,我就當做你真的上了我,但是思儂永遠在你心裏,不是有那麽一句話嗎?活人永遠打敗不了死人。”
“所以我沒有你,晚凝,如果你上了別人,我真的會放手的,但是前提是要真的有這麽一個人。”
“我就不喜歡你說話的這個調調,好像天底下除了你就沒有好男人了,再說你也不是好男人。”
“別隨便找個男人,比如沈斐那樣的。”
“沈斐這件事就你是打算說一輩子的嗎?我說過了,沒有你,我也會有一場轟轟烈烈的。”
Advertisement
“那我要不要祝福你呢?”
“隨便你。”
跟沈時倦說這句話的時候,我腦子裏麵跳出了A先生的模樣。
我總覺得我對他應該是和對旁人有些許不同的,不然此時此刻我為什麽會想起他?
我很期待當沈時倦知道我上其他人了,他會是怎樣的表?
別看他現在說得雲淡風輕,像他這樣自負的,從來都沒有失敗過的人,哪怕他沒那麽我,他都無法接失敗。
吃完午餐沈時倦送我去顧氏,他親自給我拉開車門,我正要邁步往顧氏大門裏走的時候,他忽然跟我說。
“晚凝我們可以做朋友嗎?就是那種偶爾可以一起吃吃飯,聊聊天的朋友,至別像現在這樣抗拒我。”
“我很抗拒嗎?抗拒還跟你一起吃午餐?但是做朋友這種事是順其自然的。”
我知道他想曲線救國,他不死心。
”那好,那就順其自然。”
他目送我走進顧氏大門,我推開我辦公室的門就看見顧辰北坐在我的辦公椅裏。
我知道他很喜歡我這個位置。爸生前的時候他就一直在爭取顧氏總經理的職位,可是我爸覺得他還未到火候。
他那麽深思慮,卻因為沈時倦的關係把這麽重要的職位給了我。
難怪顧辰北不服氣,這換做任何一個人都無法接。
我走過去把包隨意丟在桌上,響亮的聲音剛好可以表明出我此刻的態度。
“剛才進來嚇了一跳,我還以為我走錯房間了呢。我記得以前顧副總是很有分寸的,爸經常跟我們說,讓我們都學學你的穩重,怎麽爸走了沒人教你了?“
Advertisement
顧辰北忍耐的皺眉頭:“我不是顧淑怡他們,我不熱衷於打炮。”
“那我就直截了當地說,那麽喜歡坐這個位置,但是現在還不是你的。”
顧辰北站起來,他的臉沉得很難看。
爸走了,他的吃相比他的臉更難看,以前在人前他還裝一裝。
我走到我的椅子那邊坐下來:“顧副總找我有什麽事?”
“我兌現了我的承諾,接下來就你也要兌現你的承諾。”
“什麽承諾?”
“顧氏10%的份,那天我已經跟顧家人宣布過了。”
“哦,你是說顧焰騁豆腐宴那天?你那個補充協議好像沒有生效吧?顧家人也沒認可,那天吵那個樣子也沒有個確切的結論,你該不會覺得自己就這麽說了一下,就生效了吧。”
“囑不是簽合同,他們若是不接那就打司好了,我已經通知他們了,明天上午9點去方律師的律師樓簽份轉讓協議。”顧辰北在我麵前坐下來:”你現在把印章出來和明天出來其實都一樣,你可以完全信任我。如果你明天收到份再出來的話也是可以的。”
“顧副總不要之過急,等到一切都塵埃落定了再說,據我對他們的了解,儲珍一定不會同意的。”
“他們不同意也不行。”
“做生意也不帶強買強賣的,更何況是囑。顧副總難道不知道在囑有異議的時候,公司份是不能隨意分割的嗎?”顧辰北急著想掌握大權,他的心我能理解,但是他什麽功課都不做,難怪爸爸之前不肯把公司總經理的職位給他。
Advertisement
顧辰北的眉心擰得像個疙瘩。他兩隻手撐在桌麵上,覺下一秒他就要把我的桌子給掀翻了,不過我的辦公桌很重的,他沒那麽大力氣。
“你該不會是耍我吧?”他咬著牙問。
“顧副總,你若是能讓所有人都認了。明天他們都去律師樓簽協議,那我就簽,簽了之後回來我就把印章給你,包括總經理這個職位。”
顧辰北的眼睛亮了,但他高興的未免太早了,因為這個任務是不可能完的。
“好,那明天律師樓見。”
我們顧家人都有一個通病,能力不夠,野心卻不小。
顧辰北前腳剛走,顧曼貞就過來找麻煩了。
昨天我陪我媽去廟裏沒到公司來,我知道顧曼貞遲早要找我。
果然一進來就要撒潑,剛剛舉起我桌上的一隻水晶擺臺就要砸下去,我提醒他。
“這個擺臺13萬,你先把錢轉我,你怎麽砸我不管你。”
“那天顧焰騁的豆腐宴上,那兩個人是你把他們找過來的吧?”
“哪兩個人?”我裝傻充愣:”哦,我想起來了,你足的那一對夫妻啊。“
“顧晚凝!”氣急敗壞地大。
有些人就是這樣,明明做的事很不齒,但卻不讓別人說,一說就破防。
“我哪裏說錯了嗎?人家是合法夫妻,你可不就是個小三?姑姑,我發現你很喜歡介別人的家庭啊,你的每一任都是人夫吧?”
“顧婉婷!”惱怒,舉著水晶擺臺就向我衝過來。
“你小心一點,弄壞了東西要賠弄,但你如果弄壞了我的話,你想想你自己的下場。”
在我還有半米的地方停了下來,顧曼貞已經被我氣到炸,但卻不敢造次。
我聽說有一次顧焰騁要掐死我,被沈時倦整得很慘。
雖然氣憤,但還有腦子,沒敢輕舉妄。
我走過去將我的水晶擺臺奪過來,這是南星送給我的,其實沒有那麽貴,我剛才說的那個價格的1%都沒有。
如果真的砸碎了的話,那我就問要13萬,一分價都不講。
我小心翼翼地放回原位:“你是不是快更年期了?你搞錯了對象你知道嗎?那天那兩個人不是我找來的,還有讓你那個姘頭反水也跟我沒關係,顧辰北給了他500萬讓你那天難堪,冤有頭債有主,顧曼貞,你要找你先去找顧辰北,你又惹不起我,你跟我在這裏一頓囂有什麽用?”
顧曼楨站在原地,他的臉都被氣紫了。
“500萬?他那個公司我給他的幾次投資加起來都不止500萬。”
“一個男人但凡花你的錢,他對你還能是真心的嗎?而且你那麽喜歡喜歡搶,你去搶銀行了,搶男人你又搶不來。”
顧曼貞真快要被我氣瘋了,紅的眼睛瞪著我片刻,忽然森森地笑了。
“我搶跟你沒關係,但你這個替做得一輩子都出不了頭。沈時倦的前友死了,一個活人永遠都敵不過一個死人的。沈時倦會在心裏永遠記掛著,一生一世。“
“我管他幾生幾世,我現在已經失憶了。我對沈時倦無,而且我也和他離婚了,我大可以去找別的男人,也就是說我一邊可以著的甜,另一邊還有個人永遠在我後幫我托底所有的事,顧曼貞,爽不爽?”
我又功地把顧曼貞氣到了,看著吃癟的臉,我心裏此刻要多爽有多爽。
我都死過兩次的人了,耗沒意義。
我心裏清楚沈時倦心裏永遠會有思儂,那我就認清這個現實,並且接。
顧曼貞張口結舌,不知道該怎麽反駁我,我也不想在辦公室裏跟就這個話題繼續吵下去。
我拍了桌子:“現在是上班時間,你卻跑到總經理辦公室跟你的上司吵架,顧曼貞,你的工作態度太差了,你已經無法勝任現在的這個職位了,顧曼貞,你現在去市場部,給你一個副部長的職位,算是平調。”
“你憑什麽?”
“憑我是總經理啊,我讓你去當清潔工你都得去。”我撥了線電話:“人力資源部的吳部長來一下,帶顧小姐去新崗位。”
猜你喜歡
-
連載1965 章

左先生寵妻百分百
她是能精確到0.01毫米的神槍手。本是頂級豪門的女兒,卻被綠茶婊冒名頂替身世。他本是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專情總裁,卻因錯認救命恩人,與她閃婚閃離。他從冇想過,有一天,她會用冰冷的洞口指向他的心臟。“這一顆,送你去給我的孩子陪葬!”她扣下食指……
164.4萬字8 184411 -
連載2383 章

錯嫁纏婚:首富老公乖乖寵我
為了救父親與公司,她嫁給了權傾商界的首富,首富老公口嫌體正直,前面有多厭惡她,后來就有多離不開她——“老公寵我,我超甜。”“嗯......確實甜。”“老公你又失眠了?”“因為沒抱你。”“老公,有壞女人欺負我。”“帶上保鏢,打回去。”“說是你情人。”“我沒情人。”“老公,我看好國外的一座城......”“買下來,給你做生日禮物。”媒體采訪:“傅先生,你覺得你的妻子哪里好?”傅沉淵微笑,“勤快,忙著幫我花錢。”眾人腹誹:首富先生,鏡頭面前請收斂一下?
219.6萬字8 148190 -
完結10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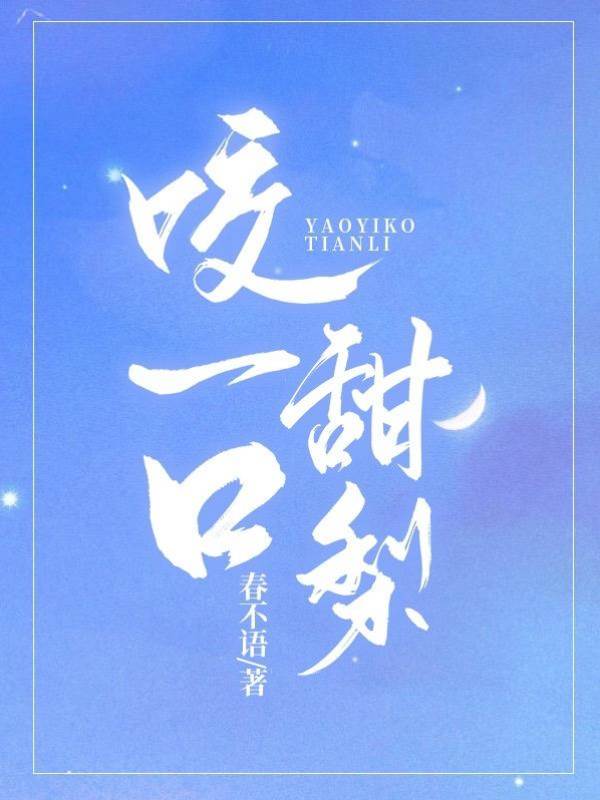
咬一口甜梨
白切黑清冷醫生vs小心機甜妹,很甜無虐。楚淵第一次見寄養在他家的阮梨是在醫院,弱柳扶風的病美人,豔若桃李,驚為天人。她眸裏水光盈盈,蔥蔥玉指拽著他的衣服,“楚醫生,我怕痛,你輕點。”第二次是在楚家桃園裏,桃花樹下,他被一隻貓抓傷了脖子。阮梨一身旗袍,黛眉朱唇,身段玲瓏,她手輕碰他的脖子,“哥哥,你疼不疼?”楚淵眉目深深沉,不見情緒,對她的接近毫無反應,近乎冷漠。-人人皆知,楚淵這位醫學界天才素有天仙之稱,他溫潤如玉,君子如蘭,多少女人愛慕,卻從不敢靠近,在他眼裏亦隻有病人,沒有女人。阮梨煞費苦心抱上大佬大腿,成為他的寶貝‘妹妹’。不料,男人溫潤如玉的皮囊下是一頭腹黑狡猾的狼。楚淵抱住她,薄唇碰到她的耳垂,似是撩撥:“想要談戀愛可以,但隻能跟我談。”-梨,多汁,清甜,嚐一口,食髓知味。既許一人以偏愛,願盡餘生之慷慨。
20.2萬字8 773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