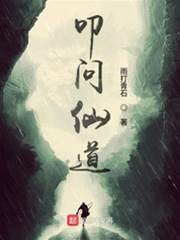《一往情深傅少的心尖愛妻》 第1186章:好事近(1)
合/歡樹已經比當初移栽進月牙灣別墅時,長得更為茁壯了。
夏天時,遮蔽日,完全在院落里籠罩下一片涼。
合/歡樹下的鐵制雕花鞦韆,上面很乾凈,看起來像是有人經常打理拭。
言歡坐在鞦韆上,紀深爵也坐了過來。
言歡瞥了他一眼,但沒說話。
紀深爵修長的手臂一手握著鞦韆靠椅,一條長輕輕點地,皮鞋蹬了幾下地面,鞦韆搖搖晃晃的漾起來。
紀深爵轉眸看著言歡的側臉,沒有避諱的問:「後院的小閣樓,你走以後,我又讓工人重新修繕好了,要不要去看看?」
提到後院的小閣樓,言歡的眼神明顯一頓。
紀深爵握住的手,笑著說:「修繕好肯定不是用來再囚/你一次的。我當初干出那麼混的事兒,連我自己都忍不住自己耳刮子,不過那個修繕好的閣樓,倒是也算『囚』了我兩年。」
言歡略微不解。
紀深爵起道:「走吧,帶你去看看。」
言歡沒拒絕,跟著紀深爵一起去了後院。
後院的小閣樓外牆上,已經煥然一新,抹了新的牆漆,已然不見當初被焚燒過的痕跡。
言歡走上那木質的樓梯,紀深爵跟在後說:「那時你剛走,我幾乎每晚都睡在這裡,企圖你能進我的夢裡,眷顧一下我也好。當時想,你真狠心,走了連夢都不讓我夢見。」
Advertisement
上了樓梯,紀深爵打開門,言歡進了小閣樓。
看見那雕花的窗欞,溫溫淡淡的笑著說:「其實有件事我還沒告訴你。三年前的那個除夕夜,你在日記本里寫,你在樓下給我放了一夜的煙火,其實我坐在這裡,也等了你一夜。」
紀深爵心臟震,目深邃容的看著。
言歡在小閣樓里轉了一圈,在小閣樓的書桌上,發現一張撕下的紙張。
還未看清紙張上寫什麼,紀深爵已經更快一步上前,眼明手快的將那張紙奪到了背後,大手將那紙張揪一團。
不想被言歡看見。
可他越是這樣遮掩,言歡便越是來了興趣。
言歡朝他手:「那是什麼?」
「沒什麼,就是一張廢紙而已。」紀深爵的表,擺明了此地無銀三百兩。
言歡執著的張著手跟他討要:「我看見上面寫了字,你的字跡。」
「真沒什麼……」
紀深爵有些無奈的嘆氣,這種日記,在那些寂寥失落的日子裡,他自個兒寫寫就好了,給看,還是當著他的面兒看,多尷尬呀。
他一向不是個矯的人,那顯得婆婆媽媽,娘了吧唧的。
「紀深爵,你不給我看,我可就走了。」
言歡作勢要走。
紀深爵一手攥住的胳膊,「別介啊。」
「那你給看不給看?」
「不……」
紀深爵拒絕的話還未落下,言歡已經歪朝他背後探去,搶他手裡的紙團。
Advertisement
紀深爵朝後退,一時沒有防備,兩人一退一進,同時跌到沙發上。
紀深爵跌倒在沙發上,言歡跌倒在他懷裡。
四目相對。
紀深爵眸含著戲謔笑意,一手著紙團,一手摟著的背,揶揄道:「早說啊,早說你的目的是這個,我一準讓你撲倒。」
言歡看他滿臉匪氣的樣子,作勢就手去搶他另一隻手裡的紙團,可紀深爵手臂長,舉起閃躲時,言歡本不是他的對手。
「紀深爵!」
紀深爵禍水的笑著,抿著笑意道:「算了,不逗夫人了。夫人既然想看,我這老臉怎麼也得豁出去。只是,看了可別哭。」
紀深爵將手裡的紙團遞到面前,「喏,你的。」
言歡睇了他一眼,從他掌心裡取過那紙團,拆開,平那揪一團的褶皺。
上面沒幾個字,卻字字深刻。
這是紀深爵日記本上,被撕掉的最後一頁。
也是最近的一篇日子。
以為要與陸琛結婚的那晚,寫下的。
「這是我們的第十年,我會一直、一直你,沒結果也。」
像是對言歡說的,可又像是,紀深爵對自己說的。
言歡看著那幾行字,神和眸頓住了,只怔怔的看著那紙上的字裡行間。
漸漸地,眼圈泛了酸。
心口,堵的厲害。
紀深爵抬手撓了撓眉骨,有些無措,「我就不該給你看。」
紀深爵將的臉,進了膛里,了的長發。
Advertisement
言歡在他口問:「既然以為我要嫁給陸琛了,為什麼還要繼續著,我記得離婚那天分手你跟我說,你要戒煙,也會像戒煙一樣把我戒了。所以都是騙我的?」
「戒煙可以,但戒你,還是算了,會死。」
言歡角緩緩莞爾:「沒結果也?」
紀深爵看著頭頂上方的吊燈,聲音很淡卻很堅定的說:「嗯,我你,你沒用也。」
言歡被他這話,弄的噗嗤一聲笑出聲來。
「好笑嗎?」某人臉無比認真的看向。
言歡咬了咬,忍住笑意,「不好笑。」
言歡看著他,看著看著,視線忽然落在了他薄上。
「紀深爵。」
忽然他一聲。
紀深爵微微坐起來,言歡已經小作的撲向他,雙手抱住了他的脖子,低頭,吻住了他的。
吻得、纏綿。
紀深爵微微一怔,沒想到會突然主。
吻完后,紀深爵不要臉的回味了一番,偶爾被的覺竟然這麼好。
紀深爵黑眸灼灼的看著:「夫人,這又是什麼意思?在下實在不懂。」
裝。
繼續裝。
言歡起,不搭理他,「不懂就算了,我也只想吃個豆腐,沒想幹什麼。男/當前,我心也是應該的,人而已。」
紀深爵哪能讓就這麼跑了,氣笑著手就把扯回來。
「我這人比較純,親了就要負責的。」
Advertisement
「……」
他整個人,哪點跟「純」沾邊?
不要臉。
紀深爵抱著說:「剛才那個就當章,反正現在我是你的人了,你不能不認。」
「你臉皮還可以再厚點。」
紀深爵眸一暗,將言歡猛地抵在牆壁上,聲低啞迷人的落在耳畔:「夫人既然讓我再無恥點,那我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何時讓他再無恥點了?
「紀唔……」
紀深爵一邊吻,一邊彎腰,將言歡打橫抱起,走到那張乾淨的小床上。
喜歡的不能自已。
紀深爵很霸道,並不算多溫。
卻,滿是深。
他將的手握住在淺床單上,用力的十指相扣,指尖,全是暖意肆意。
紀深爵滾燙的呼吸聲,落在耳畔,啞聲深沉的在耳邊說:「三年,歡哥,你終於……又是我的了。」
猜你喜歡
-
完結134 章

妖王的報恩
眾叛親離的妖王被帶至人類的巢穴,心中充滿屈辱和怨恨,“卑鄙的人類,我堂堂大妖,豈可于一人類為仆。”“不知羞恥的人類,竟摸我的尾巴,等我恢復妖力,必將你撕成碎片。”誰知那個女人收留了他數日,喂他吃香噴噴的食物,捋順他的毛發,包扎好他的傷口,又將他帶回山林。那人解開他的禁制,摸摸他的耳朵,對他說:“回去吧。給你自由。” 袁香兒學藝初成,入妖林,欲擒一小妖,契之以為使徒。 見一狼妖被眾妖所傷,委頓于地,奄奄一息,周身血跡斑斑。袁香兒心中不忍,將其帶回家中,哺食裹傷,悉心照料。狼妖野性難馴,每日對她齜牙咧嘴,兇惡異常。遂放之。至此之后,每天外出歸來的袁香兒欣喜的發現家門口總會多出一些奇怪的禮物。 偷偷躲在的妖王恨得牙癢癢:那個女人又和一只貓妖結契了,貓妖除了那張臉好看還有什麼作用?她竟然摸那只狐貍的尾巴,狐貍根本比不上我,我的尾巴才是最好的。
49.4萬字8 16611 -
連載224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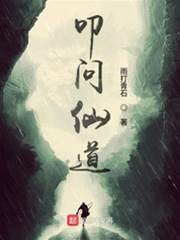
叩問仙道
一個凡人少年因為一次意外而誤入仙道,在求仙路上掙扎前行。 仙路難於登天,面對重重險阻,他的求道之心依然不減分毫。 再回首,青山依舊在,故舊皆白骨。 下面兩個企鵝群,大家想加群的,可以酌情加入。
321.2萬字8.18 48512 -
完結1134 章
諸天神皇
我有一刀,斬天裂地!諸天之上,斗戰十方!
225萬字8 1125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