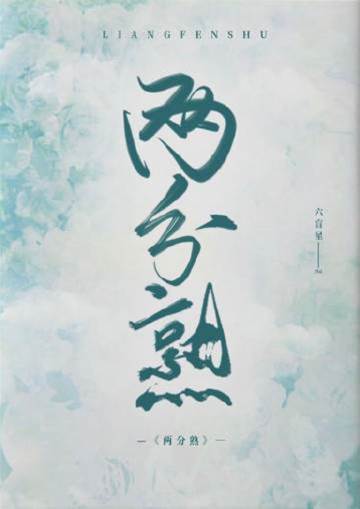《港島夜濃》 第163章 人要向前看
次日,早七點半。
蘇紋半夜未眠,起床沐浴後,便打算去廚房弄些簡餐墊肚子。
“咚咚——”
玄關傳來敲門聲。
蘇紋過貓眼向外看,發現是外賣員。
開啟門,對方遞來餐盒,“你好,你的早餐。”
蘇紋笑著說送錯了。
外賣員看著訂單,又看了眼門牌號,“沒送錯,就是這裡,梁先生點的。”
蘇紋道謝後,回到客廳,把餐盒放到桌上,撥了梁敬澤的電話。
不到三聲,對方便接起。
“早餐收到了,謝謝。”
“客氣什麼。”梁敬澤吁了口煙,“慢慢吃,九點去接你。”
蘇紋回眸睇著桌上的早餐盒,言又止。
北城老街包子鋪的早餐,由於食客太多,一直沒有開通外賣服務。
這話,蘇紋沒說。
兩人定好見面地點,便結束了通話。
蘇紋開啟外賣袋,小屜牛包、土豆餅、醬香鹹菜、甜味豆漿。
皆是每次去包子鋪必點的食。
另一邊。
梁家主宅。
梁敬澤在別墅門前的草坪完煙,折返回客廳。
梁母瞧見他的影,隨口問道:“假期還起這麼早,傭人你說六點就出門了?”
梁敬澤:“嗯,跑步。”
梁母看著他一休閒裝的打扮,並未懷疑。
Advertisement
又道:“昨晚我說的話,你放在心上,頭幾年看你忙,不催你,你自己也別不當回事。想當年,我像你這麼大,你都9歲了。”
面對母親大清早的嘮叨,梁敬澤展眉表態,“我心裡有數,您就別心了。”
梁母佯怒地剜他一眼,“你要真有數,我現在都當了。”
……
不到九點。
梁敬澤開車抵達水岸佳苑。
小區門口,蘇紋戴著墨鏡,著休閒闊和瘦T恤,肩頭斜挎著迷你包。
尋常的打扮,又著一模糊年齡的時尚。
梁敬澤踩下剎車,目綿長地欣賞了幾秒。
不可否認,褪去了青的蘇紋,大氣的韻味,更勝從前。
那邊。
蘇紋的手機似乎響了。
從兜裡拿出電話,送到耳邊接聽。
梁敬澤沒著急開過去,就將車停在路邊樹蔭下,靜靜地看著。
片刻後,蘇紋收起手機。
一輛計程車適時停在小區門口。
一個肩頭掛著雙肩包的短髮姑娘下車走到了蘇紋的面前。
兩人不知說了什麼。
蘇紋笑得開懷,並出卡片遞給了對方。
短短幾分鐘,流完畢。
那名短髮姑娘就輕車路地進了小區。
梁敬澤收回目,順勢按響了喇叭。
Advertisement
不多時。
蘇紋上車,邊系安全帶邊戲謔:“看了半天,看出什麼名堂了?”
顯然,早就注意到樹蔭下的賓利車。
梁敬澤對於看被抓包的事,毫不覺得尷尬。
坦然地道:“我見你們在談事,就沒過去。”
蘇紋繫好安全帶,繼續道:“我以前的助理。”
梁敬澤說見過一次,發引擎時,他平靜地道:“謝靳來過吧。”
標準的陳述句。
蘇紋笑容一淡:“何以見得?”
梁敬澤手指敲著方向盤,勾道:“除了他,誰還能讓你把散打冠軍返聘回來。”
蘇紋扯,想說些什麼,又忽然間有些意興闌珊。
車廂裡蔓延起無聲的沉寂。
梁敬澤沒再多言,掛了擋便朝著高爾夫球場駛去。
蘇紋眼神凌地著窗外掠過的街景。
莫名的陷煩躁。
昨天之前,已經很出現如此強烈的緒波了。
一路無話。
到了高爾夫球場。
梁敬澤停好車,一扭頭,就見蘇紋臉不佳,鼻尖還有細的汗珠。
車空調20度,絕對不至於熱到出汗。
梁敬澤凝神蹙眉,“怎麼了,是不是不舒服?”
蘇紋吸了口氣,牽強地扯角,“沒有,走……”
“蘇紋!”梁敬澤按住僵的肩膀。
Advertisement
良久,低嘆道:“在我面前,沒必要這樣,我不是你的客戶。”
言外之意,別用對待客戶的那套社標準在他面前偽裝。
蘇紋閉了閉眼,重新靠回椅背,“有紙巾嗎?”
梁敬澤開啟儲盒,聲線低沉又無奈,“突然這麼低落,是因為謝靳?”
“不是。”蘇紋著溼的掌心,“生理期。”
這種說辭梁敬澤自然不信。
他側目睇著蘇紋,一無力悄然爬上心頭。
梁敬澤降下車窗,向遠的綠蔭草坪,“既然放不下,何不再給彼此一個機會?”
蘇紋作一頓,突兀地笑出了聲。
梁敬澤不解地挑起眉頭。
蘇紋著手裡的紙團,輕描淡寫地道:“除非我有斯德哥爾。”
梁敬澤品著這句話,眸逐漸深沉,“什麼意思?”
蘇紋低頭手,“比喻而已,沒到那種地步。”
梁敬澤微微抿,不回憶起蘇紋離家的兩年。
那麼長一段時間。
不僅沒有和家裡保持聯絡,還一度中斷與所有親朋好友的聯絡。
即便是最疼的妹妹蘇緹,也時常找不到人。
原本他們都以為這是蘇紋“為走天涯”的決心。
現在看來,似乎另有……
蘇紋:“抱歉,今天可能沒法跟你切磋了。”
Advertisement
梁敬澤:“真以為我你出來是為了切磋球技?”
四目相對。
這一刻。
蘇紋讀出了梁敬澤眼底流淌的陌生愫。
很淡,很淺,稍縱即逝。
蘇紋平靜地轉開臉,“回去吧。”
這副心如止水的態度,讓梁敬澤有些挫敗地啞然失笑。
是他表現的不夠明顯,還是不到?
自打蘇紋回到平江。
他刻意制著對的欣賞之。
一來不想退婚事件重演。
二來不確定是不是真的放下過去。
沒有確切答案之前。
男的驕傲和自尊不允許他在同一人上連栽兩次。
尤其前幾日,謝靳現蘇緹和邵霆的婚禮。
那束由謝靳轉給的手捧花,並沒理掉。
那時候,梁敬澤便萌生退意。
君子有人之,他做不來橫刀奪的事。
但今日,蘇紋說出那句“斯德哥爾”。
梁敬澤就知道,他們所有人恐怕都想錯了。
“蘇紋,人要向前看,向前走。”
梁敬澤說完,推開車門,“我菸,等我幾分鐘。”
蘇紋本想說在車裡也沒關係。
話沒出口,男人已傾而出。
猜你喜歡
-
完結91 章

偏要你獨屬我
分手兩年後,秦煙在南尋大學校友會上見到靳南野。 包間內的氛圍燈光撒下,將他棱角分明的臉映照得晦暗不明。 曾經那個將她備注成“小可愛”的青澀少年,如今早已蛻成了商場上殺伐果斷的男人。 明明頂著壹張俊逸卓絕的臉,手段卻淩厲如刀。 秦煙躲在角落處,偷聽他們講話。 老同學問靳南野:“既然回來了,妳就不打算去找秦煙嗎?” 男人有壹雙桃花眼,看人時總是暧昧含情,可聽到這個名字時他卻眸光微斂,渾身的氣息清冷淡漠。 他慵懶地靠在沙發上,語調漫不經心:“找她做什麽?我又不是非她不可。” 秦煙不願再聽,轉身就走。 在她走後沒多久,靳南野的眼尾慢慢紅了。在嘈雜的歌聲中,他分明聽到了自己的聲音。 “明明是她不要我了。” - 幾年過去,在他們複合後的某個夜晚,靳南野俯身抱住秦煙。 濃郁的酒香包裹住兩人,就連空氣也變得燥熱稀薄。 男人貼著她的耳畔,嗓音低啞缱绻,“秦秦,我喝醉了。” 他輕啄了壹下她的唇。 “可以跟妳撒個嬌嗎?” *破鏡重圓,甜文,雙c雙初戀 *悶騷深情忠犬×又純又欲野貓 *年齡差:男比女大三歲
27.3萬字8 18404 -
完結7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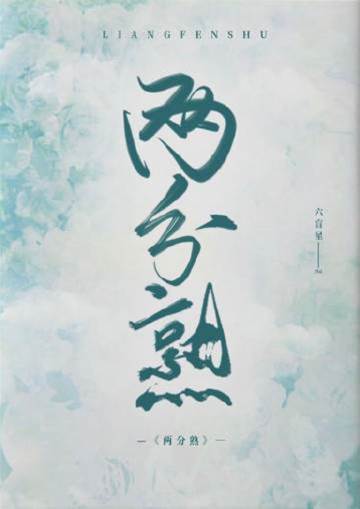
兩分熟
大學時,阮云喬一直覺得她和李硯只有兩分熟。學校里他是女粉萬千、拿獎無數的優秀學生,而她是風評奇差、天天跑劇組的浪蕩學渣。天差地別,毫無交集。那僅剩的兩分熟只在于——門一關、窗簾一拉,好學生像只惡犬要吞人的時候。…
25.3萬字8 6302 -
完結62 章

要和我交往嗎
徐其遇被稱爲晉大的高嶺之花,眉目疏朗,多少女生沉迷他的臉。 餘初檸不一樣,她看中的是他的身體。 爲了能讓徐其遇做一次自己的人體模特,餘初檸特地去找了這位傳說中的高嶺之花。 可在見到徐其遇第一眼時,餘初檸立即換了想法。 做什麼人體模特啊,男朋友不是更好! 三個月後,餘初檸碰壁無數,選擇放棄:) * 畫室中,餘初檸正在畫畫,徐其遇突然闖了進來。 餘初檸:“幹、幹什麼!” 徐其遇微眯着眸子,二話不說開始解襯衫鈕釦:“聽說你在找人體模特,我來應聘。” 餘初檸看着他的動作,臉色漲紅地說:“應聘就應聘,脫什麼衣服!” 徐其遇手上動作未停,輕笑了一聲:“不脫衣服怎麼驗身,如果你不滿意怎麼辦?” 餘初檸連連點頭:“滿意滿意!” 可這時,徐其遇停了下來,微微勾脣道:“不過我價格很貴,不知道你付不付得起。” 餘初檸:“什麼價位?” 徐其遇:“我要你。”
16.8萬字8 4332 -
完結435 章
一手遮腰
【清醒心機旗袍設計師vs偏執禁慾資本大佬】南婠為了籌謀算計,攀附上了清絕皮囊下殺伐果斷的賀淮宴,借的是他放在心尖兒上那位的光。後來她挽著別的男人高調粉墨登場。賀淮宴冷笑:「白眼狼」南婠:「賀先生,這場遊戲你該自負盈虧」平生驚鴻一遇,神明終迷了凡心,賀淮宴眼裡的南婠似誘似癮,他只想沾染入骨。
66.3萬字8 515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