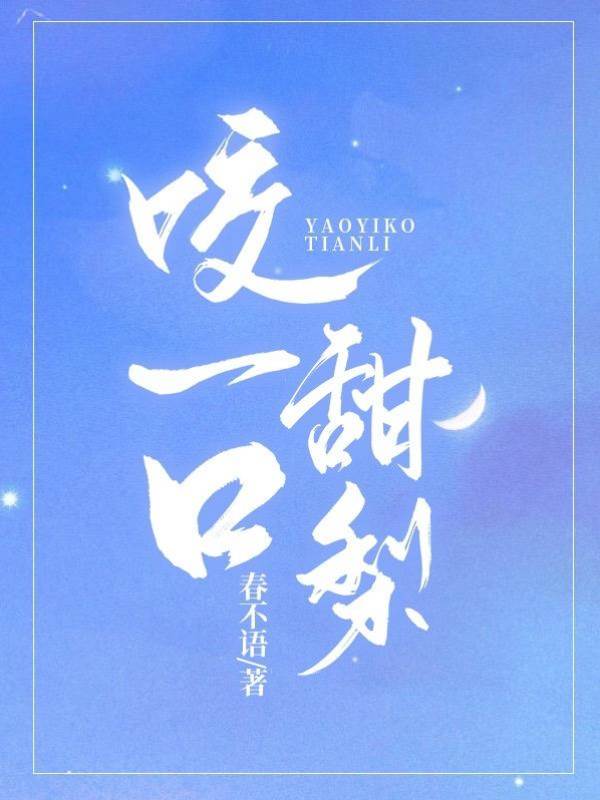《陸太太的甜婚日常》 第175章 陸生:你最重要!
回程路上,兩人討論了一會訂婚之事,場地,宴客名單這些瑣事都不用他們心,全都是家中長輩請了專人理,所以,他們要做的就是在當日出現就行了。
聊一會兒訂婚的事,車子已行至半山私人道路。
「剛才在會所到江家二了。」
葉臻頭靠在陸懷遠肩膀,他張開一邊手臂摟著,只一隻手與十指扣,握著放在他大上,訂婚戒指在昏暗中散發著耀眼的芒。
懷中的姑娘說了這句話后,就低著眼不出聲。
陸懷遠原本摟著手臂的手向上移,溫暖的手掌落在後頸,聲音溫淡地問:「聊了什麼?」
「說……」終於抬眼,卻頓住了沒有說完的話,鬆開與他握的手指,雙臂抬了起來,勾住他脖子,將臉深深地埋了進去,鼻端儘是他悉又好聞的氣息。
陸懷遠任摟著,結實的雙臂回抱著。
「對不起……」
兩人擁抱了許久,小小的,帶著哽咽的道歉聲從他溫熱的頸脖傳了出來,懷中孩輕呼而出的氣息輕拂著他頸側的。
「對不起,以後我做任何事一定會三思而行,一定會同你商量……」
不會再讓你因我而低頭。
不會再讓你因我而為難。
不會再讓陸家被人嘲笑。
「傻氣……」
不用問,他也知剛才在會所江家二同講何事了。
「以後不許再因這樣的事跟我講『對不起』。真要覺得抱歉,就給我好好把保健品核心品牌升級方案重做一份,兩天之我要看到結果。」
眸中微帶淚意的孩被他的手指抬起了下,他角帶笑,*住帶著水的眼眸。
什麼道歉的話都不必說。
對他而言,財富名利皆浮雲,千金散盡還復來。
Advertisement
,最重要。
-
安琪晚飯是在葉曦這邊跟薛嘉瑜們一起吃的,陸懷遠與葉臻拖手進屋后,也告辭回隔壁。
家裡除了天黑就自開啟的壁燈,屋一片安靜。
以為邵百川還未回來,也懶得管他幾時回,上了樓正在打開房門,對面臥室的門卻打開,不想見的人雙手環靠在門邊定定地看著:「回來了?」
這不是睜眼說瞎話,沒話找話嘛!
安小姐心裡哼一聲,不理會他,逕自開門屋,正在關上房門時,門被一雙有力的大手撐住。
「還在生我氣?」
他半個子橫了進來。
本來安琪的氣已經消得差不多了,但見他一副橫在門裡奈何不了他的模樣,氣又不打一來。
「你出去。」手想推他,奈何力氣太小,連推了好幾下,邵百川頎長結實的軀毫不,還過分地手攬住肩膀。
安琪氣極了,任地在他手臂又抓又咬,還抬腳踢他,踩他,可他就是不放開。
「安琪,別生我的氣了,好不好?」他仍舊地摟著,低頭在耳邊輕聲哄著,極有耐心,「早上的事是我不好,以後不會再這樣了,行不行?」
安琪從小到大都是,家中所有人都寵,哄,就連弟弟平時都會讓幾分。
只是自從嫁人之後,所有人好像將對的寵都收回了一大半,個個都讓多學著做個好妻子。
知道家裡人不是不了,只是想讓學著長大,可心裡還是會不平衡,卻又半點辦法也沒有。
都不知道多久沒有人像邵百川這樣耐心地哄了。
耳里聽著他左一句『對不起』右一句『對不起』,裡雖然不饒人,拍打他的作也沒有停下來,可心裡還是很用的。
Advertisement
被人放在手心疼寵的覺,不得不承認,很讓人心暖,還會讓人心跳加快,臉蛋發熱。
於是,罵人的聲音越來越低,打人的作也越來越慢。
最後,兩人都沉默下來。
的手在他手臂上撓了撓,像只小貓在抓。
「怎麼了?」邵百川低眸問。
「我要去洗澡。放開啦。」
那句,『有沒有被咬傷』終究還是沒說出口。
「那就是不生我氣了?」
邵百川鬆開一半的力道,讓活自由。
「除非你把那**剪了,我才不生氣。」
邵百川:「……」
這要求真的是太為難他了,就算想要哄不生氣,也不能答應。
安琪輕哼一聲,輕鬆地推開他的雙手。
-
翌日上午,葉臻與陸懷遠在家中等著禮服公司的人上門。
十月底,南方白日天氣依然在20度上下,氣溫宜人。
陸懷遠難得悠閑地坐在花園的太傘喝咖啡,坐在他側的葉臻卻沒有他的閑,筆電打開在面前,一手撐著下,一手移鼠翻閱著徐冰傳過來的資料。
一塊散香著濃郁香味的手工巧克力遞到邊時,很快被推開了。
「等會再吃。別吵我啦。」
遞巧克力的陸生只能又將巧克力放回碟子中,有些無奈的搖頭笑。
「娶個工作狂老婆是什麼覺?」
賀靜嘉拉開椅子會下來調侃他一句。
「我以後可以福了。」陸生半開玩笑回應。
「陸生的理想是做個功人背後的男人嗎?」
「這想法不錯。」
「呵……」賀靜嘉呵笑了聲,轉頭向正在埋頭看資料的葉臻問道:「陸太,日後你跟人家介紹的時候就可以說,這位是我丈夫陸先生。他做什麼?家庭煮夫……」
葉臻終於抬頭,卻哭笑不得。
他們這都扯到哪去了呢?
Advertisement
「你們慢聊,我回屋,等會禮服公司的人到了再我。」
起,抱著筆電往屋裡走。
剛才只有陸懷遠在側時,可以心無旁騖地專心做自己的事,因為他也很安靜地不出聲打擾。
但是賀小姐在就不同了,不想讓你做事就真的鬧到你什麼也做不了。
方案在兩天之要完,而這兩天之事很多,要試禮服,要回S城看老太太,還要隨時跟進NSA二次投標可能產生的變故,實在沒時間跟他們這些理公事遊刃有餘的人閑聊。
「嘖……」賀小姐看著葉臻匆忙進屋的背影嘆了幾聲,然後向始終平靜的陸懷遠:「阿遠哥,你真的不介意十年二十年後,你以葉臻丈夫的份為人所尊敬?」
十年,以葉臻的聰明,足以為一名讓人尊敬的商場強人。
「當然不介意。」陸生極有教養的莞爾一笑,「我應該到更加的開心與驕傲。」
那語氣,分明像是一個父親對材的兒才有的一種迷之自豪。
賀小姐又是一聲呵笑:「那是你老婆,又不是兒,你得瑟什麼呀?」
指不定外頭的人怎麼講他懼,被老婆爬在頭上做威做福呢!
「有區別?」
陸生留下三個字給賀小姐,起回屋。
沒區別?
呵呵……
男人果然都有惡趣味,就算表面再道傲貌然如陸懷遠,也不能免俗。
-
禮服公司的人如約而至,葉曦趴在二樓樓梯扶手上看著好幾個陌生人進來,抬著從一排排的訂製進來,好奇卻不敢下來。
最近變得大膽勇敢很多,便面對完完全全的陌生人,還是膽怯的。
姐夫在樓下讓去書房姐姐下來,點頭轉就跑。
可是,姐姐說再等二十分鐘,於是只能跑出來,趴在扶手上跟姐夫打著手勢傳達姐姐的意思。
Advertisement
管家奉上了茶水及點心便退下去了,賀靜嘉與剛到的安琪便開始對那一排排品頭論足,然後翻看禮服公司送過來的最新目錄,等們將目錄翻到最後一頁時,主角總算是姍姍來遲。
不試不知道,一試嚇一跳。
服尺碼好像小了些,穿是穿得進去,但是那效果就由優雅變了。
葉臻有些哭無淚。
十九歲之後,的CUP就一直沒變,怎麼忽然就……
最近天天加班,還沒有空去理會這件小事,結果一穿上禮服就全底了……
「沒關係,現在改還來得及。」禮服公司的人站在側微笑地安。
「還在發育期就是不一樣啊。」安琪雙手調侃了句。
「哦哦哦……」
賀小姐也在一邊鬧。
葉臻整張小臉都紅了,笑著拍向。
臨時搭起來的更室里傳來一片笑鬧聲。
坐在沙發上的陸懷遠手裡握著杯咖啡,臉如常,眼底笑意卻慢慢地溢了上來,鋪滿漆黑眼底。
-
試完訂婚禮服及日常,已是數個小時,然後又是珠寶公司的人將上次訂的首飾送過來,戒指,手鏈,耳環,針,髮夾……從頭到腳全都是訂製款。
葉臻看得兩眼都花,除了訂婚日需要用到的幾款試了一下之外,其餘全都收進儲藏櫃中。
下午四點,一行人一同搭直升機回S城,傍晚時分齊齊出現在醫院。
賀靜嘉等人進來招呼一聲后便不再打攪,最後只留葉臻與陸懷遠陪著。
陸方士已清醒,但仍需臥床休息,不過神狀態還不錯,還沒能說太多的話,卻想多聽聽孫子與準孫媳婦兒坐在一邊說話。
與此同時,賀靜嘉也去探太嫲。
與陸方士不同,霍家太嫲年紀太大,雖然生命征趨於正常,但至今尚未清醒。
賀靜嘉握住老人家枯瘦的手,心裡酸酸楚楚的。
太嫲會住院,與的任不無關係。
雖然裡不承認,但心底卻清楚得很。
如今坐在這裡看著將從小疼大的老人再也不能開口同說話,心裡更是疚又難過。
「太嫲,對不住。你一定要醒過來,我不會再惹你生氣了,好不好?」
-
薛嘉瑜輕拍了下姐姐的肩膀,正開口安時,包里的手機響了,是賀父。
轉走出病房門才接起電話。
回港開店,母親不放心昨日已從法國飛過來探,原本是計劃一家人在港聚聚,一起吃個飯的。
可八百年不聯繫的父母剛通了電話就一言不合,各自甩了電話,聚餐不了了之。
父親不屑去港,母親同樣也不屑回s城。
於是只能同嘉嘉回來探家人,已經許久未現他們見面,特別是一對小的雙胞胎,很是掛念。
父親來電,正在詢問幾時過去,君姨已備好飯菜等候們姐妹二人。
回復父親后,轉返回來時,卻在抬眼的不經意間看到了一個穿黑西裝的男人雙手在兜里,背對著站在百葉窗口前朝裡頭著。
就在猶豫著要不要走過去時,站著的男人似是聽到了腳步聲,轉頭朝的方向過來。
霍希安高一百八十五公分,雖然看著瘦,但形修長拔,頭髮黝黑茂,五清俊,一雙濃眉下的狹長眼眸總是不經意流出富家子弟的慵懶與傲。
薛嘉瑜怔怔地看著站在自己眼前的男人,等反應過來時才發現霍希安也在盯著看。
只能著頭髮招呼一聲:「姐夫。」
聞言,霍希安冷哼一聲,收回目,轉頭回去背對著。
薛嘉瑜與賀靜嘉是雙胞胎姐妹,但兩人的外表個卻天壤之別,而且們從六歲之後就分開,一個留在賀家,一個跟著母親去了法國生活,只有每年寒暑假時回國或另一個出國相聚。
他們之間開始並沒什麼集,而且格向,跟他們一伙人也玩不來。
直到有一年回國過暑假,賀父嫌棄的母語越來越差,寫的字更是難看得讓人想發火。
他們這幾個年紀相當的夥伴就他的字寫得特別漂亮,而且兩家住得近,賀家長輩便讓他教寫字。
霍希安縱有千百個不樂意,卻敵不過長輩的再三遊說,勉強答應。
就在那一年暑假,喜歡上他的。
當然,以霍公子的家世外貌,從小到大喜歡他的孩子數不勝不數,還沒上大學都不知換過幾任朋友。
所以就算薛嘉瑜這個孩沒表白,可從看他的眼神,霍公子一眼就明了的慕,第一時間就找了借口不再教寫字。
薛嘉瑜雖然比不上同胞姐姐的明艷人,但也是長相清秀,就是太單純,本不懂玩轉男遊戲,這樣的孩本不是他會喜歡的類型,更不能是他能玩玩的對像。
猜你喜歡
-
連載1965 章

左先生寵妻百分百
她是能精確到0.01毫米的神槍手。本是頂級豪門的女兒,卻被綠茶婊冒名頂替身世。他本是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專情總裁,卻因錯認救命恩人,與她閃婚閃離。他從冇想過,有一天,她會用冰冷的洞口指向他的心臟。“這一顆,送你去給我的孩子陪葬!”她扣下食指……
164.4萬字8 184422 -
連載2383 章

錯嫁纏婚:首富老公乖乖寵我
為了救父親與公司,她嫁給了權傾商界的首富,首富老公口嫌體正直,前面有多厭惡她,后來就有多離不開她——“老公寵我,我超甜。”“嗯......確實甜。”“老公你又失眠了?”“因為沒抱你。”“老公,有壞女人欺負我。”“帶上保鏢,打回去。”“說是你情人。”“我沒情人。”“老公,我看好國外的一座城......”“買下來,給你做生日禮物。”媒體采訪:“傅先生,你覺得你的妻子哪里好?”傅沉淵微笑,“勤快,忙著幫我花錢。”眾人腹誹:首富先生,鏡頭面前請收斂一下?
219.6萬字8 148207 -
完結10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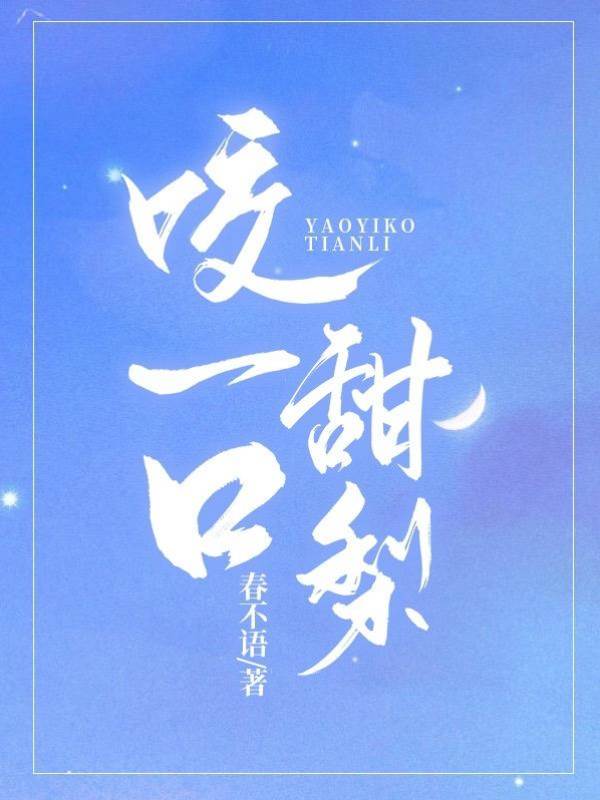
咬一口甜梨
白切黑清冷醫生vs小心機甜妹,很甜無虐。楚淵第一次見寄養在他家的阮梨是在醫院,弱柳扶風的病美人,豔若桃李,驚為天人。她眸裏水光盈盈,蔥蔥玉指拽著他的衣服,“楚醫生,我怕痛,你輕點。”第二次是在楚家桃園裏,桃花樹下,他被一隻貓抓傷了脖子。阮梨一身旗袍,黛眉朱唇,身段玲瓏,她手輕碰他的脖子,“哥哥,你疼不疼?”楚淵眉目深深沉,不見情緒,對她的接近毫無反應,近乎冷漠。-人人皆知,楚淵這位醫學界天才素有天仙之稱,他溫潤如玉,君子如蘭,多少女人愛慕,卻從不敢靠近,在他眼裏亦隻有病人,沒有女人。阮梨煞費苦心抱上大佬大腿,成為他的寶貝‘妹妹’。不料,男人溫潤如玉的皮囊下是一頭腹黑狡猾的狼。楚淵抱住她,薄唇碰到她的耳垂,似是撩撥:“想要談戀愛可以,但隻能跟我談。”-梨,多汁,清甜,嚐一口,食髓知味。既許一人以偏愛,願盡餘生之慷慨。
20.2萬字8 786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