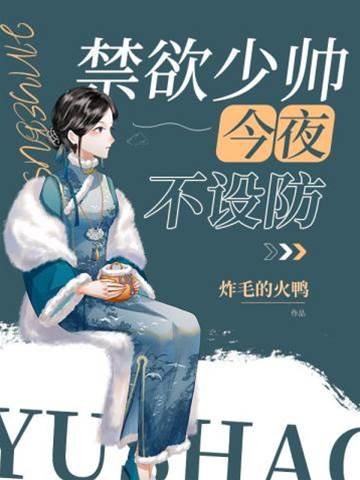《非典型性血族契約》 第79章 草原
秦小游不止一次過李先生的,早上他還用手指過。
當時的想法非常純潔。
除了羨慕還是羨慕,希自己將來也能練出像李先生一樣的好材,并且把這個當作長期的目標。
李先生似乎知道他的想法,每次他上手時,都任他個夠,眼神寵溺,仿佛他是一只頑皮的小貓咪。
然而今天,經過一系列事件的發酵,他對李先生的發生了變化,這會兒他的,就不那麼純潔了。
手……出奇的好。
放松狀態下,的還有彈,皮細膩,沒有多余的,久了會上癮。
不知道一下是什麼覺?
這麼一想,便不自地付諸行。
下一秒,他的后頸被男人修長的手指給住了。
秦小游保持作,腦袋后仰,睜著一雙無辜的紅眼睛,和男人深沉的藍眼對視。
兩人沉默,彼此之間流淌著詭異的氣氛,氈包里安安靜靜,外面的篝火晚會熱火朝天,不時地傳來鼓聲、馬頭琴音以及人們的歌聲和吆喝聲。
不知過了多久,男人手指微,按著秦小游的頸椎,一節節地往下,到了肩胛骨中間,像專業的按師,力道恰到好,秦小游到整條脊椎都麻了,不由自主地發出舒服的低。
里溢出奇怪的聲音,他霎時赧然,雙手一松,捂住自己的,圓溜溜的眼睛有些失措地瞪視男人。
李先生神淡定如常,手指慢條斯理地回到他的后頸,勾起一縷銀的發,問道:“需要我幫你把串珠解下嗎?”
秦小游沒有立即回答。他在審視,在判斷,想從男人的臉上瞧出點什麼。可惜,他功力不足,本探不出男人的心思。
皺了下秀氣的眉頭,他放下捂的手,忽略剛才的窘態,若無其事地說:“顧兆告訴我,這種紅瑪瑙串珠只有才會戴。”
Advertisement
說完,他眨著眼睛,等待男人的回答。
“是嗎?”李先生揚起劍眉,似乎也有些意外,“賣我串珠的老嬤嬤說可以送給親近的人。”
秦小游一怔。
竟是誤會了他的意思?
李先生送他串珠,純粹是因為他是他的初擁,沒有其他多余的想法?
所以,到頭來,只有自己在一頭熱?
可是……可是他被顧兆點醒,釋放出心真實的,已經收不回去了。
秦小游下意識地咬,眼睛發酸,有點喪氣,又有點哭無淚。
懷里的小家伙突然泫然哭,李先生關心地他的臉頰,聲問:“怎麼了?”
秦小游覺得難堪,翻了個,離開他的懷抱,面朝里蜷一只小蝦米,懊惱地揪被角。
一定是他不夠,才會被李先生當了小輩。
李先生單了五千多年,完全沒有找伴的打算,自己怎麼能奢他突然開竅呢?
他對他的照顧,不過是建立在長親和初擁的基礎上。
兩人年齡懸殊,他雖然活了四十八歲,可連李先生的零頭都不到呢!
所以,在李先生眼里,他和剛學會走路的嬰兒差不多稚吧?
秦小游鼓著腮幫子,暗暗下定決心。
他要努力長,變強變厲害,站到和李先生一樣的高度,再向他表白!
一旦定下目標,心里的沮喪煙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對未來強烈的憧憬和信心。
想通了就釋然了,剛才的小波折,變得微不足道。
李先生手支著頭側躺著,眼眸幽深地凝視年消瘦的后背。年肩膀微,散發著沮喪的氣息。李先生斂眉,想將他抱回懷里,然而,不到半分鐘,年的氣息陡然一變,好像想通了什麼事,整個人神采奕奕,連蜷著的都直了。
Advertisement
秦小游恢復緒,到背后有道灼熱的目。剛才忽然離開李先生的懷抱,會不會引起他的懷疑?
他暗自吐了口氣,舒展眉目,重新轉,滾回到男人的懷里,手臂一,長一,半掛在男人上,微微仰頭,打著呵欠,出一副困頓的模樣。
“酒喝多了……頭痛。”
醉酒是個好借口,屢試不爽。
果然,男人手指輕輕地按著他的太,幫他緩解頭痛。“你酒量淺,以后喝。”
秦小游乖乖地應道:“嗯,我知道了。不過……晚上那碗馬酒不能怪我,我以為是茶。”
他閉起眼睛,調整姿勢,讓自己躺得更舒適一些。腳丫子不自覺地蹭著男人的小,心里慨,李先生不愧是最古老的族,進化得完無瑕,連孔都比一般人細,加上偏低的溫,皮像綢般,令人不釋手……哦,釋腳。
可能是他蹭得太明顯了,李先生的倏地換了位置,反過來制他。
秦小游本能地掙扎,結果纏到一起,都不了,接著,一只大掌拍打他的屁。
“好好睡覺。”男人低沉的聲音在頭頂響起。
秦小游一下子安靜了。
雖然還不明確李先生的心思,但至他不排斥自己的。
暫時維持親的關系,他已經心滿意足了。
等將來自己為事業有,頂天立地的男子漢后,一定要向李先生求婚,陪伴他,護他,讓他再也不會產生厭世的緒。
懷著這樣好的愿,秦小游枕著李先生的手臂,沉夢鄉。
等年的呼吸均勻了,李先生輕地挪開,讓年躺得更舒服一些。
睡夢中的秦小游似乎到他的作,“啪”的一聲,手掌按住他的左,用力一,呢喃:“我的……不許搶……”
Advertisement
李先生的眉抖了數下,深邃的眼神晦暗莫測,視線移向床邊掛著的裝飾繡布上。繡布手藝湛,圖案漂亮,是一幅張力十足的狩獵圖。
年輕的牧民半蹲在草叢間,手執弓箭,對準月下的雪狼。
李先生把玩著年發辮里的串珠,神溫和。
曾經,他是一名優秀的獵人,盯上麗的獵時,常常潛伏暗,仔細觀察獵的一舉一,在沒有等到最佳時機前,絕不輕舉妄。
年黏黏糊糊地往他懷里靠,他低頭親吻他的發,空出手按掉床邊的開關,霎時,氈包陷了黑暗。
篝火晚會持續到晚上十一點,吃飽喝足的牧民和游客們陸續回氈包休息。
顧兆打著呵欠,搖搖晃晃地走著,暗忖秦小游福氣不淺,被李先生抱進氈包后,就沒有出來了。
以李先生的材和力,明天早上小游能不能下床還是問題呢!
有些人啊,真是羨慕不來!
步自己借宿的氈包,掀開簾子,鉆了進去,乍見床邊坐著一名儒雅青年。
“嗨~”顧兆朝青年打了個招呼。
牧民的氈包數量有限,游客兩人住一個,他和青年分配到了一起。
早上直播時,不小心拍到青年,被他冷眼一瞟,嚇得不敢拍,盡量保持距離。
萬萬沒想到,分配氈包時,兩人湊到了一塊兒。
祁云冷淡地點了點頭,算是回應,繼續整理床鋪。
床很大,中間擺了一張矮幾,了分隔線,兩條被子,兩個枕頭,各睡一邊,互不干擾,不錯。
顧兆尷尬地搔頭,看著青年收拾好自己的床位,躺了上去,蓋被睡覺,毫不拖泥帶水,搞得他都不好意思弄出靜了。
輕手輕腳地洗漱完畢,他躺到床的另一邊,關了燈,出手機,心地想看一會再睡,可想到另一邊休息的青年,嘆了口氣,收起手機,認命地睡覺。
Advertisement
今天累得夠嗆,躺下沒多久,他便迷迷糊糊了。
夜更深了,月西移,遠約傳來狼嚎聲。
顧兆撓了撓手臂,不安地翻。
“叮鈴鈴……叮鈴鈴……”
突然,清脆的銅鈴聲在草原上回,由遠而近,仿佛就在耳邊。顧兆到蠱,雙眼閉,翻坐起,作緩慢地掀開被子,連外都沒有穿,抬起雙臂,像僵尸一樣蹦蹦跳跳地往門口蹦去。
祁云迅速下床,閃到顧兆邊,指尖竄出一電流,點擊他的背部,顧兆電般地抖了抖,瞬間清醒了。
當他發現自己穿短和t恤,赤腳站在氈包門口時,驚呆了。
“我……我夢游了?”
否則,他怎麼會半夜下床往外跑?
“不是夢游。”祁云收回手指,冷靜地道,“是中邪了。”
顧兆聽到青年清冷的聲音,嚇了一跳,張大:“中……中邪?”
開什麼玩笑!
科學時代,不要封建迷信好不好!
祁云見顧兆不信,沒有任何解釋,只是提醒道:“不管發生什麼事,都不要出去。”
他提起背包,掀開簾子,悄無聲息地離開。
顧兆愣愣地待在原地,半晌,他才驚覺。青年睡覺時,本沒有服!他早就知道夜里會出幺蛾子!
現在怎麼辦?
要不要出去看看況?
抱著好奇的心態,他將簾子掀開一條細,地往外瞧。
月下,一群衫不整的人,抬高雙臂,像僵尸般排一隊,蹦蹦跳跳地離開牧場。
他倒吸一口氣,放下簾子,驚慌失措地逃回床上,躲進被窩里瑟瑟發抖。
不管是不是中邪,外面那些和他同行的游客都中招了,毫無意識地被銅鈴聲引著往草原蹦去。
如果不是青年喚醒他,他恐怕也了其中一員。
不過,那個青年是什麼人?不僅沒有中招,還敢出去,莫非……他是警察?
只有警察才敢孤涉險,離開前還好心地救了他,提醒他。
顧兆啃著拳頭,堅定自己的想法。
惶恐不安的心逐漸穩定,腦子便開始高速運轉。
為什麼他們這些游客聽到銅鈴聲,會在睡夢中被引出去?剛才雖然只瞄了一眼,但他可以肯定,僵尸隊伍里沒有一個牧民。
當然,也不見李先生和秦小游。
而和他同住的警察同志一直保持清醒,仿佛預料半夜會發生匪夷所思的事。
想破腦袋,努力回憶,突然靈一閃,他瞪大眼睛。
導游!
出發前,導游熱地送他們每人一瓶礦泉水。
國人向來喜歡免費的東西,去牧場的途中,大部分游客先喝了導游送的水。
好像只有警察同志沒有喝,一直塞在背包的側面。
顧兆握了握拳頭,覺得自己不能獨善其,必須做些有意義的事。
他從被窩里出來,穿上服,背上背包,拿出手機,打開直播。
半夜直播間里沒有多人,只有幾個熬夜的老觀眾跳出來。
【喲,小顧,你終于舍得上線了?】
【就是,就是,知道我們等得多辛苦嗎?突然下線,連招呼都不打,太過分了!】
【話說小顧,你在什麼地方?怎麼黑乎乎的?】
顧兆嚴肅地開口:“三位老鐵你們好,沒時間解釋了,你們幫我錄屏保留證據,一會兒我將進行一場可怕的冒險,萬一出事,請務必幫忙報警!”
【啥啥……啥況?】
【不知道啊!哥們兒,你悠著點。】
【什麼冒險?好不好玩?我去我室友起來一起看。】
顧兆躡手躡腳地來到門邊,再次掀起簾子,銅鈴聲遠去,如僵尸蹦跳的游客不見了蹤影。
他深吸一口氣,貓著腰鉆出氈包。
草原的夜晚,冷風颼颼,氣溫下降了十幾度,凍得顧兆直打哆嗦,他急忙從背包里取出厚服穿上,低聲音說:“哎喲媽呀,好冷,好冷!”
【小顧,你說說你,好好的覺不睡,跑出來干嘛?】
【外面沒啥吧?月倒不錯。】
顧兆一邊直播一邊急步行走,離開牧場圍欄,約看到蹦跳的“僵尸”,他把鏡頭對準那邊,哈了口氣道:“老鐵們,能不能看清那邊的人?據說他們中邪了,聽到銅鈴聲后,一個個像僵尸一樣地跳出去。我跟你們說,我差點也中招,要不是和我同住的警察室友拍醒我,就像他們一樣被走了。”
【啥?小顧,你在夢游吧?】
【什麼中不中邪的,你別嚇人啊!我一個人住,晚上不敢睡了。】
猜你喜歡
-
完結558 章

隱婚老公太神秘
傳聞榮家二少天生殘疾,奇醜無比,無人願嫁,所以花重金娶她進門。而結婚兩年她都未成見過自己的丈夫,還遭人陷害與商界奇才宋臨南有了糾葛。她陷入自責中,宋臨南卻對她窮追不捨,還以此威脅她離婚。她逃,他追;她誠惶誠恐,他樂在其中。直到她發現,自己的殘疾丈夫和宋臨南竟是同一人……輿論、欺騙、陰謀讓這段婚姻走到了儘頭。四年後,一個酷似他的小男孩找他談判:“這位大叔,追我媽的人排到國外了,但你要是資金到位的話,我可以幫你插個隊。”他這才知道,什麼叫做“坑爹”。
98.8萬字8 106536 -
完結105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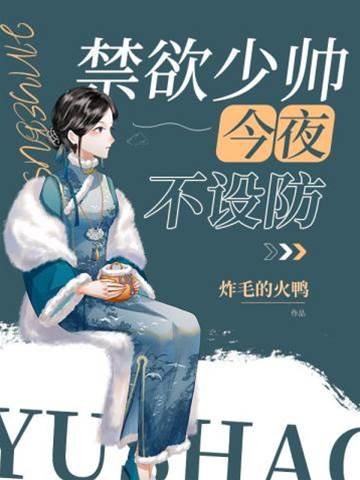
禁欲少帥今夜不設防
一朝身死,她被家人斷開屍骨,抽幹鮮血,還被用符紙鎮壓,無法投胎轉世。她原以為自己會一直作為魂魄遊蕩下去,沒想到她曾經最害怕的男人會將她屍骨挖出,小心珍藏。他散盡家財保她屍身不腐;他與她拜堂成親日日相對;直到有一天,他誤信讒言,剔骨削肉,為她而死。……所幸老天待她不薄,她重活一世,卷土而來,與鬼崽崽結下血契,得到了斬天滅地的力量。她奪家產、鬥惡母、賺大錢,還要保護那個對她至死不渝的愛人。而那個上輩子手段狠戾,殺伐果決的少帥,現在卻夜夜將她摟在懷中,低聲呢喃:“太太救了我,我無以為報,隻能以身相許了。”
193.2萬字8 20524 -
完結141 章

錯嫁瘋批老公後,我直接帶球死遁
夏鳶穿進一本瘋批文,成爲了下場悽慘的惡毒女配,只有抱緊瘋批男主的大腿才能苟活。 系統:“攻略瘋批男主,你就能回家!”夏鳶笑容乖巧:“我會讓瘋批男主成爲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瘋批男主手焊金絲籠。 夏鳶:“金閃閃的好漂亮,你昨天給我買的小鈴鐺可以掛上去嗎?”她鑽進去一秒入睡,愛得不行。 瘋批男主默默拆掉金絲籠,佔有慾十足抱着她哄睡。瘋批男主送給她安裝了追蹤器的手錶。 夏鳶:“你怎麼知道我缺手錶?”她二十四小時戴在手上,瘋批男主偷偷扔掉了手錶,罵它不要碧蓮。 當夏鳶拿下瘋批男主後,系統發出尖銳的爆鳴聲:“宿主,你攻略錯人了!”夏鳶摸了摸鼓起的孕肚:要不……帶球死遁?
26萬字8.18 283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