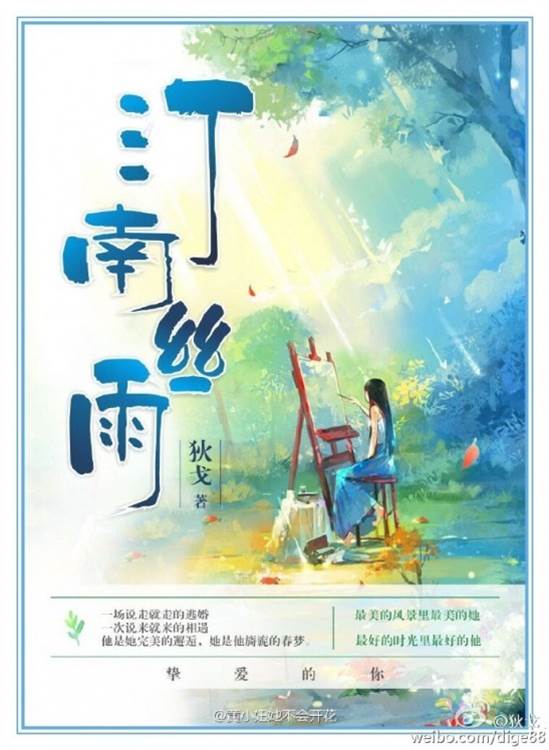《池中尤物:京圈締婚》 第 24章 他們的過去
懷孕的人坐下,看向寧笙手裏的棉花糖。
撇了撇,咽了咽唾沫。
回國這麽久,好久沒吃了。
“請問,可以給我吃一口嗎?”
“啊?”
寧笙不著頭腦,但還是分了一半給。
“謝謝。你不僅很漂亮,人還這麽好,我們做朋友吧。”
人自顧自地說著,隨即將自己手上的金鐲子取了下來。
“這上麵有我的名字寫,是定製的,送給你啦,當見麵禮。”
“不行,我不能要。”
寧笙更加不著頭腦了,“你怎麽一個人出來了,需不需要我們人送你回家?”
“我不回去!”
人仿佛很抗拒,隻顧吃著手裏的棉花糖。
“我秦芙,你什麽名字呀?你旁的男人好帥,是你老公嗎?”
秦芙看見帥哥兩眼放,忙不迭道。
“我是寧笙,他是我的丈夫,祁司煜。”
“你們好,你們好。”
秦芙雙眼發看向兩人,“祁司煜...”
呢喃著這個名字。
“我總覺見過你,但是我記不起來了。”
“嗯?是這樣嗎?祁司煜?”
寧笙瞇了瞇眼,看向一旁無辜躺槍的男人。
“老婆,我一直潔自好。”
祁司煜看起來極其清心寡,生淡薄,要不是寧笙見識過他在床上的樣子,還真的會信。
“最好是,誰知道你在遇見我之前有什麽風流債。”
寧笙直直看向他,忍不住吐槽。
Advertisement
“秦芙!”
一聲怒喝傳來,坐在椅子上的人“啊哦”一聲,表示糟糕。
寧笙朝遠去,一個簡裝的男人,後還跟著許多高大的人。
他們作很快,急速朝這邊走來。
看起來文質彬彬,卻又帶著幾分肅殺的氣息。
儒雅清俊的臉龐是掩飾不住的焦急。
他走到秦芙麵前,忍不住將360°檢查了一番,確定沒事才放下心來。
“誰允許你離家出走的?一走還直接國”
男人忍不住怒道,死死將抱在懷裏。
寧笙和祁司煜對視一眼,有什麽瓜是可以吃的嗎?
而祁司煜的氣卻降到了冰點。
他好好的一次約會。
誰允許別人擅自毀掉的?
“首長,夫人沒事就好,您切勿過分苛責。”
隨行而來的醫生連忙開始檢查,勸解道。
季源洲站在一旁,莫名覺到了一低氣。
在這樣的份,還能被威脅,讓他不滿地抬頭去。
淩厲的五映眼簾,腦海塵封的記憶迅速席卷而來。
他從一開始的思索,到震驚,再到一慌張,都被祁司煜看在眼裏。
“是你,好久不見啊。”
季源洲直直看向他,雙抿了一條直線。
是故人。
“你怎麽還是這樣飛狗跳?”
祁司煜的態度反而輕鬆很多,笑著接過話茬。
那一瞬間,季源洲以為他轉了。
但下一秒,他就知道自己想多了。
Advertisement
“這麽多年,看來你還是不長教訓。”
被點到名字的季源洲軀一僵,他帶來的手下有十幾個,此刻都豎起了耳朵聽起來。
“阿芙,我們走,回家。”
季源洲拉過自己妻子的手,就要離開。
“這麽久沒見,不吃個飯嗎?”
一句話將眾人釘在原地。
“你認識他們呀?你的朋友?”
寧笙好奇地朝他看去,問道。
“算是,我給你介紹。”
祁司煜攬過自己妻子的腰,一手搭上了季源洲的肩頭。
“這是我之前的同事,季源洲,這是他太太,秦芙。”
“之前秦芙在這裏的時候,你為什麽裝不認識?”
寧笙敏銳地問道。
“我有必要記住嗎?”
祁司煜笑著了的發。
“季源洲,這是我的太太,寧笙。”
季源洲轉過來,訥訥地問了一聲好。
“多年不見,你也已經結婚了。”
“沒有多久,不過在六年前罷了。”
祁司煜依舊如沐春風地笑著,十分紳士而得。
“走吧,遠道而來的客人。”
祁司煜拉著自己的妻子走在前方,而季源洲這才遣散了跟隨來的眾人,護著秦芙跟隨在後。
京都----醉花社。
水棠包間。
“季先生,你之前也是研究化工的嗎?”
寧笙試著打開四人間沉默的話題,季源洲夾菜的手一頓,抬眸去,祁太太眼裏是他從未見過的純真。
Advertisement
他看向邊的祁司煜,對方笑著盯著他,略微點了點頭。
那意思是他放心說。
“不是,我經營著一個雇傭兵集團。”
“那為什麽和祁司煜是同事啊?”
“之前他在我們那工作過一段時間。”
寧笙皺著眉,沒理解到他的意思。
見狀季源洲又補上了一句。
“洲武裝聯。”
“那我知道了,你們是北洲能力數一數二的。”
“沒了嗎?”
祁司煜低沉的話傳來,“詳細給我太太講講吧,在你的工作單位,我的能力怎麽樣。”
敢這是讓他側麵誇讚啊?
玩的真花,六年來子一點都沒變。
“祁先生,其實...非常的優秀,在我們集團的時候,出任務的經常是他,從無敗績。我們的集團之所以能壯大,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為祁先生的化工炸藥。”
“後來,他...”
“後來就是我回國,為國家做貢獻了,笙笙。”
祁司煜及時打斷他的話,溫看向邊的妻子。
季源洲覺得,現在的祁司煜,就像毒蛇一般,隻是沒吐蛇信子。
看起來他的妻子不知道後麵發生的事。
曾經的他們本來是親無間的戰友,他還沒當上首長,當初的老首長,已經屬意於23歲的祁司煜。
他表麵上被祁家從六歲起就送到洲留學,從小學到大學,再到博士的最高學位,但實際上,祁家對他不管不顧,隻是扔在了這樣一個殘酷的地方任人踐踏。
Advertisement
就連祁老爺子定期打來的金,也被祁家暗自扣下。
那時他還隻是一個六歲的孩子。
貧民窟極其黑暗,暴力犯罪層出不窮,他被要求從別人的下跪著鑽過,被剝了服打的滿烏紫,甚至還要被迫嗑藥。
一個個難熬的夜晚,讓他沒有年。
季源洲還記得見到他的第一麵。那一年他們都12歲。
幾個犯罪分子手上拿著發黴的熱狗,要求他從下鑽過,就給他食。
“A wild dog that no one wants!”(沒人要的野狗!)
嘲諷聲和哄笑鑽在場人所有的耳,祁司煜照做了。
但拿到食的那一刻,那群外國人的手掌也被炸開了花。
老首長目睹了全程,認為他是個可造之才。
解救了他,被收進洲武裝聯,他眼裏沒有純真,隻有不屬於這個年紀的。
一次次的沾滿鮮,他那段時間隻知道麻木地殺戮,不知道自己是誰。
心靈至此被扭曲,直到一片空白。
他們就這麽並肩作戰了十年,但他在第十年,遇到了自己的人,秦芙。
人是有有的,他無法做到不心。
而秦芙是北赫赫有名的華商千金,對方的父母不願意自己的兒嫁給一個雇傭兵,他屢次吃了閉門羹。
祁司煜自然也知道。
他主退出了洲武裝聯,去發展了自己的事業。
這有了後來名全球的埃斯蒙德。
那時候的他卻隻拍了拍自己的肩頭,道:“君子有人之。”
而他了新一代的首長,肩負起了許多責任和義務。
這也讓他犯下了終生難以彌補的大錯。
為首長後,由於他的疏忽,難以顧及自己的家庭,秦芙在某一天夜晚,被敵對勢力侵犯。
從那之後,的大腦造了創傷,選擇忘記了那段糟糕的時間,但有時候很孩子氣,更加依賴人,能做出離家出走到華國這件事,也不奇怪。
醫生也無法給定時間,什麽時候能好。
但這些,他沒拿出來說,他也明白,祁司煜知道的一清二楚。
六年間,他們唯一的聯係,就是一筆筆軍火訂單。
季源洲看向他,對方的視線卻在手中的蝦殼上,正往寧笙的碗裏放,蝦已經堆了一座小山。
他好像一直都這樣,如魚得水,從來不會顧此失彼。
猜你喜歡
-
完結638 章
買一送一:首席萌寶俏媽咪
盛安然被同父異母的姐姐陷害,和陌生男人過夜,還懷了孕! 她去醫院,卻告知有人下命,不準她流掉。 十月懷胎,盛安然生孩子九死一生,最後卻眼睜睜看著孩子被抱走。 數年後她回國,手裡牽著漂亮的小男孩,冇想到卻遇到了正版。 男人拽著她的手臂,怒道:“你竟然敢偷走我的孩子?” 小男孩一把將男人推開,冷冷道:“不準你碰我媽咪,她是我的!”
116.1萬字8.18 310839 -
完結75 章

一見到你呀
1. 向歌當年追周行衍時,曾絞盡腦汁。 快追到手的時候,她拍屁股走人了。 時隔多年,兩個人久別重逢。 蒼天饒過誰,周行衍把她忘了。 2. 向歌愛吃垃圾食品,周行衍作為一個養生派自然向來是不讓她吃的。 終于某天晚上,兩人因為炸雞外賣發生了一次爭吵。 周行衍長睫斂著,語氣微沉:“你要是想氣死我,你就點。” 向歌聞言面上一喜,毫不猶豫直接就掏出手機來,打開APP迅速下單。 “叮鈴”一聲輕脆聲響回蕩在客廳里,支付完畢。 周行衍:“……” * 囂張骨妖艷賤貨x假正經高嶺之花 本文tag—— #十八線小模特逆襲之路##醫生大大你如此欺騙我感情為哪般##不是不報時候未到##那些年你造過的孽將來都是要還的##我就承認了我爭寵爭不過炸雞好吧# “一見到你呀。” ——我就想托馬斯全旋側身旋轉三周半接720度轉體后空翻劈著叉跟你接個吻。
21萬字8 9512 -
完結43 章

我的愛生生不息
雲知新想這輩子就算沒有白耀楠的愛,有一個酷似他的孩子也好。也不枉自己愛了他二十年。來
4.3萬字8 13074 -
完結6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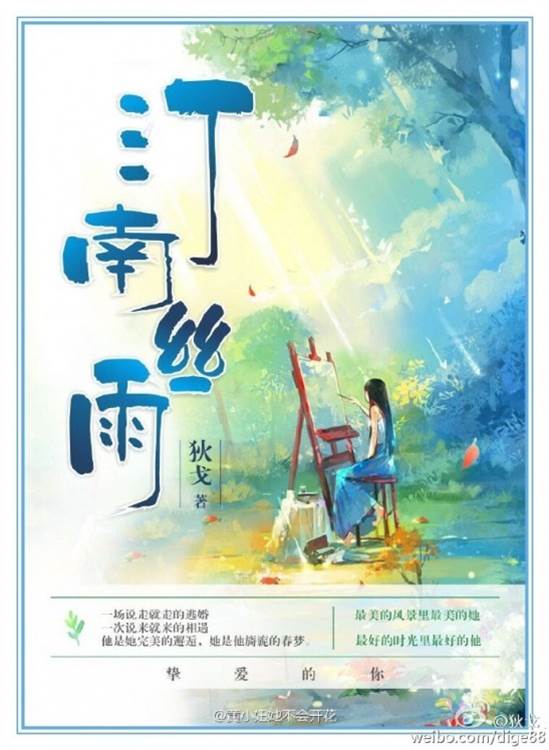
汀南絲雨
通俗文案: 故事從印象派油畫大師安潯偶遇醫學系高才生沈司羽開始。 他們互相成就了彼此的一夜成名。 初識,安潯說,可否請你當我的模特?不過我有個特殊要求…… 婚後,沈醫生拿了套護士服回家,他說,我也有個特殊要求…… 文藝文案: 最美的風景裡最美的她; 最好的時光裡最好的他。 摯愛的你。 閱讀指南: 1.無虐。 2.SC。
16.9萬字8 9132 -
完結222 章

退婚后被殘疾大佬嬌養了
真千金回來之後,楚知意這位假千金就像是蚊子血,處處招人煩。 爲了自己打算,楚知意盯上了某位暴戾大佬。 “請和我結婚。” 楚知意捧上自己所有積蓄到宴驚庭面前,“就算只結婚一年也行。” 原本做好了被拒絕的準備,哪知,宴驚庭竟然同意了。 結婚一年,各取所需。 一個假千金竟然嫁給了宴驚庭! 所有人都等着看楚知意被拋棄的好戲。 哪知…… 三個月過去了,網曝宴驚庭將卡給楚知意,她一天花了幾千萬! 六個月過去了,有人看到楚知意生氣指責宴驚庭。 宴驚庭非但沒有生氣,反而在楚知意麪前伏低做小! 一年過去了,宴驚庭摸着楚知意的肚子,問道,“還離婚嗎?” 楚知意咬緊牙,“離!” 宴驚庭淡笑,“想得美。” *她是我觸不可及高掛的明月。 可我偏要將月亮摘下來。 哪怕不擇手段。 —宴驚庭
60.5萬字8 3342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