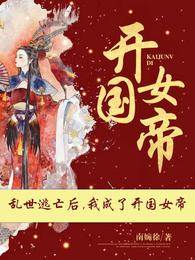《東宮避火圖》 第81章 不要再看我了
阮清從始至終看著他的眼睛,不知不覺間,心莫名跳得厲害。
咬著下,雙手落在石榴紅的擺上,將三重煙雨一般輕盈的煙羅,一點一點,掀了起來……
之後,又輕輕地全都落在了謝遲的頭上,蓋住他的白玉冠。
抬著頭,直了修長的脖頸,仰著屋梁上心描繪的避火圖,眸漸漸迷離。
子如此不爭氣。
抓著子的雙手,攥得越來越,兩條已經快要站不住了。
忍不住,一隻手垂下,隔著子著謝遲的頭,之後,另一隻無安放的手送到邊。
張口橫咬住食指,留下一排小巧的牙印。
嚨裏發出藏不住的輕……
-
這一宿,到香果兒跟來在門外伺候。
困得要命,還要掰著手指數著了幾次水。
一次,兩次,三次,四次……,後來就數了。
房裏鬧騰得要命,聽著姑娘被欺負地真是……慘啊……
哭也哭了,求了求了,斷斷續續,嗚嗚咽咽,殿下怎麽就不知道心疼呢?
他好像就見不得姑娘歇著,更容不得姑娘睡會兒。
一直到天都了魚肚白了,房裏才漸漸消停下來。
Advertisement
香果兒終於放心了,好不容易坐在門外草草打了個盹兒。
可沒一會兒,又聽謝遲在房中道:“水。”
又趕打起神來,張羅著命人送水過來。
進屋裏去時,一片狼藉早就見怪不怪了。
隻聽著姑娘在裏麵還在低低地哭。
香果兒一陣心疼。
阮清這回,是被禍害狠了。
謝遲幫清洗,在哭。
謝遲幫用藥膏,也在哭。
他是真的不得半點,到了就忍不住,就沒完。
最後天都徹底亮了,阮清換了套幹爽的寢將子裹上,不給他著,不理他,才總算消停。
然而,終於睡了,謝遲卻沒歇。
他隨便穿了件寢,披落著長發,疏懶敞著領子,半遮著膛,又坐在窗邊理昨晚帶過來的公文。
大熙朝的東宮,效仿皇帝的朝堂,不但配置了全套的衙門堂屬,還有東宮十率的軍由太子直接統領。
謝遲冊封時日未久,許多人事配備本就不齊全,又突然離開了一個多月,眼下手頭要理的事已經堆積如山。
他又要加籌備東海水師,同時監視沈氏的一舉一,將所有事齊頭並進,忙得不可開。
Advertisement
想要讓皇帝爹看到他是個合格的儲君,最基本的一點就是要有足夠的力和能力,將所有事全部理得清清楚楚,將一切都掌控在手中。
阮清到了晌午時,醒來了一會兒,掀開帳子,尋了一眼,就見謝遲坐在窗邊的榻上,一手拿著本沒看完的折子,擱在膝頭,另一手用指尖抵著額角,正在閉目養神。
雕花窗前,白瓷細口瓶中,著一支頗有風骨的石榴枝,枝頭一朵朵火紅的石榴花,開得正豔。
他黑的錦緞寢敞著,著潔的膛,一不。
謝遲到底是好看,不好看,當年也不會一眼心。
他是在酒樓上見了,起了心,才拿做賭。
又何嚐不是在兔子燈下,隻看了一眼他的側,就惦記著要帶他回家去倒門?
阮清趴在一團狼藉的床褥裏,下搭在疊著手臂上,懶洋洋地看了他一會兒,覺得又困又乏又,便不想看了,倒回床上去繼續睡。
“醒了?他們送吃的進來?”
他在窗下,將手指從額角拿開,睜眼時,已經清明了許多。
阮清懶散窩在床上,“殿下沒去上朝?”
Advertisement
一開口,嗓子都是啞的。
就後悔跟他說話了。
“今日休沐,哪兒都不去,就與你在這宅子裏待著。”
謝遲笑笑,放下手裏的折子,下榻出去外間,對門外低聲吩咐了一番。
過了一會兒,香果兒就帶人送了午膳進來。
與飯菜一同送來的,還有照例一碗避子湯。
是阮清每次從謝遲那兒回來都要喝的。
這次,起得晚,香果兒怕再晚喝了就沒用了,便與午膳一道送了進來,想服侍著姑娘空腹喝下。
謝遲一直垂眸看著那碗藥,見阮清手去拿時,便用手指摁住了碗沿兒。
“不要喝了。”他溫聲道。
“不能不喝。”阮清語調堅決,不容反駁。
是個寡婦,如今著整個侯府,跑出來伺候他,已是天下之大不韙,萬一敗,必定會死的很難看。
若是再不小心有了孕,實在是不堪設想。
更何況,也不想有他的孩子。
奪位遙遙無期,中宮更是未知之數,無論哪一步事敗,這弄出來的孩子,都會是個最大的累贅。
萬一謝遲死了,一個造反太子的孤,必是眾矢之的。
Advertisement
就算舍得付出大好的年華,含辛茹苦將孩子拉扯大,將來又如何與他說他的世?
告訴他,他的父親是個篡位失敗的反賊?
所以,不如一碗藥湯,一了百了。
謝遲著碗沿兒的手指,到底還是拿開了。
阮清皺著眉,將藥一口氣喝完,又漱了口。
如此,胃裏頓時已經滿了,再看著午膳,一口都吃不下。
“下去。”謝遲將香果兒屏退,坐到床邊,盯著阮清看了好一會兒,不知道在想些什麽。
阮清也不想理他,飯也不吃了,翻過去接著睡。
他自己不是人,也不把別人當人,真的是得夠夠的。
可是上隻隨便裹了件寢,沒穿子,那寢還是昨晚拿的,又寬又大,八是謝遲的。
此時翻,白膩的搭在被子上,又不小心了出來。
謝遲原本盯著想事,目就又被吸引了過去。
他手掌放在腳上,擺弄腳趾頭。
阮清無將腳丫走,“殿下,你就不能節製點 ?”
他不語,抓回細細的腳踝,手掌順著往上。
阮清累死了,還想躲,卻被他摁開,“別,看看昨晚的傷好點沒。”
阮清沒勁兒地手想用襟兒蓋住自己,都不知道是該哭好,是求饒好,還是罵他好。
“殿下不要再看我了。”
腫得要死。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