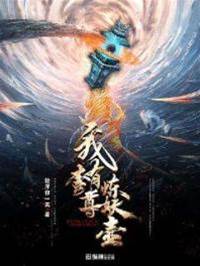《大明春色》 第31章 犬馬之勞
朱高煦打斷世子的話,得到燕王準予,便一臉嚴肅地抱拳道:“父王,北平都指揮使張信,投靠咱們……”
姚廣孝的聲音立刻道:“王爺,謹防有詐。”
朱高煦頭也不回,馬上搶著說道:“張信得了朝廷旨,要他來捉拿父王,人已在門樓。父王見他一面,明辨旨便知真假!”
這時世子竟然又抱拳道:“父王,兒臣還有要的地方沒說……”
看得出來,世子這回真的是用事、了真格,非常之執著。
燕王轉過頭來,眉頭皺,面有怒,但很快他的怒便收斂起來,口中說出來的話語重心長的:“高煦若真要害你,你為何至今還站在此地?”
世子的臉上一會兒紅、一會兒慘白,張著言又止的模樣。
燕王抬起手,將手裡的茶杯重重按到桌面上“哐”地一聲,斥道,“鬧夠了嗎?”
剛才朱高煦和世子各自爭辯的時候,燕王的話很,是沒有明確表態的。但現在他直接拋出兩句短促的話,就馬上把世子噎住、不敢吭聲了!
燕王的意思很明白,他隻想以大事為重,世子那點傷害本不值一提。當此之時,挑起一一毫部衝突都是不合時宜的,正該抱團一致對外的時候,還容世子繼續說下去?凡事一定要分出是非黑白、激化矛盾麼?
世子的都烏了,朱高煦見他袖子裡的手像篩糠一樣抖著,生怕他當場暈倒!
此時此刻,朱高煦其實是最理解世子的人。記得當初在回北平的路上缺馬,世子喪氣疲憊,決定自己留下,說了一番“很多人都不在乎他死活”的話……而現在,因為父王有更大的力和需要,確實又不在乎他的,世子心的沮喪悲涼,可想而知。
Advertisement
燕王轉頭看向朱高煦:“張信帶了旨?”
朱高煦道:“回父王的話,帶了的。”
燕王便道:“你去,把他帶進來。”
姚廣孝的聲音道:“王爺先勿急,等張信進來了,老衲出面甄別旨。”
朱高煦忍不住說道:“早就沒用了!府上有細作,已識破父王的計謀,不然朝廷如此著急下旨行,為何?”
燕王道:“你先去帶人!”
朱高煦抱拳退出來,告訴了太監馬和一聲,便去門樓。
沒多久,用大帽遮掩了半張臉的張信便跟著朱高煦,一塊兒來到燕王房中。朱高煦先進門行禮:“父王,張都指揮使到。”
只見燕王已坐到床上,拿厚厚的棉被包著,發髻凌,正在簌簌發抖,他看了朱高煦一眼,仍是一臉茫然。朱高煦一時間非常佩服父王的演技。燕王還沒稱帝,但演藝已足以稱帝、為影帝。
“末將參見燕王!”張信上前抱拳執軍禮。
燕王還是沒有反應。
朱高煦轉過頭來,與張信面面相覷。二人都心知肚明,張信也是清楚燕王在裝瘋,不然他投降個屁!
朱高煦道:“父王就在面前,張將軍把東西拿出來吧。”
張信不聲微微回顧,目在和尚姚廣孝臉上停留了片刻,他終於手進懷裡,把那竹筒掏出來,從裡面倒出一卷黃綢緞。
朱高煦先接了,當著燕王的面,到姚廣孝手裡。姚廣孝拿到眼睛面前,仔細看了一番,轉頭向燕王輕輕點頭……
姚廣孝收起旨時,乾燥的閉,牙齒也咬著,好像剛剛吃了一坨黃燦燦的長條,
正咬牙強吞下咽。 突然之間,燕王猛地把被子一掀,拿袖子在臉上了一把汗,便生龍活虎地從床上跳了下來。此時張信還雙手抱拳、彎著腰站在屋子當中,燕王大步走到張信面前,將他扶起:“張將軍,快快免禮!”
Advertisement
張信沒有免禮,反而“撲通”跪倒在跟前,斬釘截鐵地說道:“末將敬大王英雄氣概、大王栽培提攜之恩!若大王不棄,末將願效犬馬之勞!”
“好!好!”燕王把住張信的胳膊,將其提了起來,“張將軍雪中送炭及時警示,真乃俺的恩人!恩張!俺沒齒不忘今日之事。”
燕王和張信二人正互道惺惺相惜之時,朱高煦觀察到,姚廣孝正對世子用幅度非常小的作搖頭,並且輕輕歎了一氣。
以前朱高煦隻覺得姚廣孝與世子走得近一點而已,現在更加確定:姚廣孝的早就坐到那邊了的,只不過平素沒表現出來而已。
這時姚廣孝察覺到朱高煦的目,轉頭過來,二人四目相對,目錯剎那之間,姚廣孝的臉比哭還難看。他的三角眼一閃,但片刻後又一臉從容無神了,眼睛也變得仿佛有點渾濁。
朱高煦想起姚和尚說過:如果張信能被拉攏,他就鑽到慶壽寺的放生池裡化作一隻鱉!姚廣孝此時目有點閃爍示弱,估計也想到了那句話……
但畢竟歲月不饒人,和尚的臉皮如同枯樹皮、已變得又厚又皺。他很快把目投向了燕王和張信,好像什麼都沒想起、關注之事也不是什麼水生。
朱高煦自然也不提。不管怎樣,就目前而言這一屋子人都是一條繩子上的螞蚱,姚廣孝也是燕王府裡重要的人,現在和他撕破臉扯那些事,沒有任何好。
其實朱高煦並不想與姚廣孝過不去,也不想在父王面前表現什麼自我。他去拉攏張信時,僅僅因為命運相關,擔憂歷史在此時發生什麼偶然錯,想盡力幫忙、也是為自己出力。
畢竟,朱高煦能擁有這一切,只因他是燕王的兒子。
Advertisement
這時張信的聲音道:“大王府上的長史葛誠,已經背叛大王!大王佯裝神智有恙,便是葛誠告了布政使張昺!”
“這個吃裡外的東西!”燕王恨恨的聲音道,右手化掌,在腹前往下一劈。
姚廣孝道:“王爺,老衲以為,將葛誠拿下、先不殺,王府上可能還有別的細作。”
“嗯……”燕王微微點頭,將手背到後,在原地來回走了兩步,猛然又停下來,“大致還是照原來的謀劃行事。下令,傳張玉、朱能,袁珙、金忠,馬上府議事!”
姚廣孝道:“老衲這便馬和去辦。”
燕王又道:“隨後俺們到中殿的偏殿見面。”
屋子裡的人紛紛執禮告退。
就在這時,燕王走了過來,一把攜住朱高煦的小臂,如炬的目照到朱高煦的臉上,“俺兒勇智,當初為父不知也!”
那大手掌上悉有力的力道傳來,加上燕王讚賞的真誠目,朱高煦差點就開心了……要不是剛剛才見識了燕王的演技,朱高煦真的會放松緒,因為那慈父般的眼神太真誠了,簡直如沐春風。
朱高煦也急忙帶著哽咽地說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父王,您給兒臣的恩惠太多,兒臣便是豁出命,也報答不完。兒臣若非父王的兒子,便會如窮巷中的草芥一樣,吃多苦頭也無濟於事,哪能十幾年養尊優,用父王給予的榮華富貴?”
這句話倒是出於真心,於是朱高煦都不需要刻意表演,就能聲並茂。
燕王點頭道:“很好!俺兒定能助俺一臂之力!”
剛走到門外的世子悄悄回了一下頭,眼神如死灰,緒已不如剛才激。
“去罷。”燕王道。
朱高煦抱拳道:“兒臣告退。”
Advertisement
朱高煦走出房門,便聽到遠方傳來“隆隆隆……”的悶響,他抬頭看天,見烏雲布,仿佛要掉下來了一般。
從封閉沉悶的房間裡走出來,朱高煦長籲一口氣,但那黑的烏雲造了心理影響, 他仿佛還是有點不過氣來。
在此時此刻,朱高煦才忽然真真切切地意識到:戰爭已經來臨。
裡,弓馬騎嫻,一武藝力氣,勇武的仿佛為戰爭而生;但現在朱高煦的心還是前世的觀念,他並不是好戰之人。
前世那時,作為一個現代普通人,從各種資訊了解過戰爭的苦難。好好的和平日子不要,有網上有吃、舒服的生活不過了,為啥喜歡戰爭年代?
戰爭就會死很多人流很多,破壞很多經濟,富人財富水、窮人更窮。特別是這種戰,若是參照義務教育學到的知識、站到全社會的高度看,本就毫無意義……無論結果如何,打完也不會改變任何現狀,養尊優的那些人依舊是朱家子孫,各種武將勳貴和士大夫;目不識丁的苦哈哈大眾,以為打一場仗就能搖一變有什麼改變?
但是,朱高煦一面可以照著歷史教科書背誦的“歷史意義”歎一番,一面又要非常積極地加爭奪遊戲。因為爭奪的巨大利益裡,有他的一份!
這個鍋不能他來背,也不是燕王的錯。若非建文那邊的人苦苦相,不僅要割藩王的,還要五髒六腑,誰他媽願意上已經落袋的巨大好?
朱高煦等僅僅依靠“太祖兒孫”的份,就可以高高在上吃香喝辣……但是,想到湘王忽然變了“偽造貨幣”的罪犯,忽然那穩穩當當的鐵飯碗、藩王份、被人宣布屁都不是?作為鐵飯碗的益者、朱高煦也接不能。
部決定一切,他越想越生氣了。
猜你喜歡
-
完結119 章
農家醜媳
二十一世紀私房菜老闆葉青青,一覺醒來成爲一名"沉魚落雁"農家媳. 村裡人皆嘲笑她:"李家買來那醜婦,擡頭能把大雁嚇摔,低頭能把小魚嚇瘋,跟李家那病秧子倒也是絕配!" 醜婦咬牙發奮,不但將自己改造成貌美如花,病秧子相公也被調理得日漸健康,好日子來咯! 可是,不想突然蹦躂出一個女人稱是她娘,指鼻子罵窮書生不配她,勒令她嫁給土財主. 她淡定地撫著小腹問,"多給彩禮不?肚裡還一個呢." 相公驚訝不說話,當夜就長篇大論起來,"古人有云:車無轅而不行,人無信則不立,業無信而不興." "怎麼?" "爲了家業興隆,娘子,我們還是把肚裡那個做實吧——"病秧子化身餓狼,夜夜耕耘不知休. 良田大宅、連鎖店鋪、聰明包子、健壯夫君、美貌身材統統拿下.只是,相公,你的身份…有點可疑!
38.5萬字7.91 34579 -
完結185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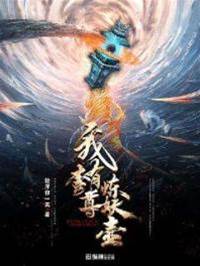
我有一尊煉妖壺
天地為爐,陰陽為碳。 一個破夜壺,誰能想到,竟是傳說中的上古神器「煉妖壺! 剛剛穿越異世,還沒吃上一口香噴噴的軟飯,宅男韓風就不得不手掌煉妖壺,醉臥美人膝,開啟自己寂寞如雪的新人生……
401萬字8 55054 -
完結319 章

帶億萬物資做惡毒后娘
【反套路+亂世求生】 教官九月帶著億萬物資穿成克死了兩任丈夫的黑寡婦。 第三次,她被國家分配給養了三個小崽子的光棍。 尚未洞房,夫君又被抓去做了壯丁。 在這個啥都不如食物值錢的亂世,九月不甘不愿的做了三個崽子的后娘。 于是,她的惡毒之名不脛而走! 多年后,三個崽子名揚天下。 成為戰神的夫君說:媳婦,仨娃都是我撿來的,各個漏風,不如我們自己生一個吧! 九月挑眉:“滾開,別耽誤老娘賺取功德給我的平頭哥特戰隊兌換裝備!”
56.5萬字8 3007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