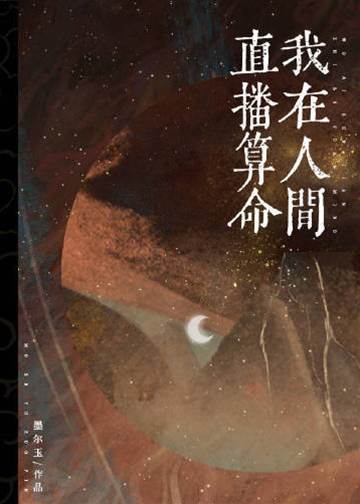《離婚后,霍總夜夜跪地哄》 第1卷 第35章 憑什麼這麼對我
王媽確實真的想過把鍋鏟扔臉上,但到底是一個保姆,沒那麼大的本事。
拉拽著蘇棠棠,“你給我滾出去,這里是我們太太的家,不歡迎你!拱出去!”
蘇棠棠死死著霍昀洲,年輕的看上去還沒有王媽有勁,王媽拉了幾下,立馬落下來幾滴眼淚。
“我不是小三,昀洲哥哥,我到底做錯了什麼?”
王媽見拽不,雙手掐腰。
“你還好意思說你做錯了什麼?你看看你現在,你一個單的姑娘,我們先生可是有家室的人,你覺得你這樣抱著他合適嗎?”
蘇棠棠抹了抹眼淚,“可是我把昀洲哥哥當我的親人,我爸和我大哥去世以后,昀洲哥哥說過要照顧我一輩子的!”
王媽直接無語了,翻了無數個白眼。
霍昀洲攬著哭泣的蘇棠棠,“好了,別哭了。我說過要照顧你一輩子就一定會做到。”
“王媽。”他俊臉一沉,“棠棠要在這里住一段時間,這段時間你不許欺負棠棠,更不能給老宅那邊通風報信,不然,你明天就辭職。”
Advertisement
“可是——”王媽指著沈念安,想問你自己的老婆都不管了嗎。
“沒有可是。”霍昀洲也是沒有辦法,把蘇棠棠安排在別的地方都會被老宅那邊的人發現,放在這里,相當于燈下黑,最危險的地方也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只是他沒想到沈念安會突然回來。
這并不在他的計劃之。
沈念安有那麼一瞬間,差點被霍昀洲氣得暈過去。
這個世界上,其實沒有那麼多暴躁又撒潑的人。
只有不費吹灰之力把人瘋的男人。
制住右手的瘋狂抖,一言不發地拿起了自己的包。
“霍昀洲,我祝你們百年好合,早生貴子。”
王媽趕攔住,張開雙臂,“太太,你可不能走啊!你走了才真的輸了!”
“王媽,你覺得現在我不走行麼?人都領到家里了還有什麼可說的?”看向霍昀洲,“霍昀洲,我們明天直接民政局見吧。”
霍昀洲一不,“除了離婚你就不會說點別的了?要我說多次?棠棠威脅不到你霍太太的地位,你就這麼容不下?”
Advertisement
“對,我他媽就是容不下!”沈念安了句。
說完心中陣陣悲涼,曾經的教養不允許說這些不得的話,可此時此刻,真的要被霍昀洲瘋了。
這可是他們的婚房,沈念安這三年的委屈和難堪都埋葬在這里。一千多個獨守空房的日夜,那些被迫的屈辱和等待,沈念安以為這里起碼是屬于自己的。
可霍昀洲就這麼輕而易舉地帶著一個別的人回來了。
算什麼?
狗屁不算!
推開王媽的手,踩著高跟鞋決然離去。
走到院子里的時候,手腕被抓住,沈念安想都沒想地甩開。
空氣中傳來清脆的響聲。
沈念安后知后覺自己的手心都是麻的,扇了霍昀洲一掌。
扇就扇吧。
這個狗男人應得的。
“解氣了麼?”霍昀洲舌尖抵了抵臉頰。
沈念安窩著憋屈的火,以前不敢跟霍昀洲剛,但現在讓殺人都不帶眨眼的。
“王,八,蛋。”
沈念安拿起手里的包,朝著霍昀洲砸了一下又一下,包上的劃破了他的襯衫,在他實飽滿的膛上留下一道道紅印。
Advertisement
沈念安愣了只一秒,繼續砸。
“你憑什麼這麼對我?”
“憑什麼!”
一直砸到聲嘶力竭,站都站不穩,霍昀洲將抱住。
“你就這麼在乎我?”
男人挨了打,語氣卻很愉悅。
沈念安剛發泄的緒再次被點燃,這次直接推開他,揚手就是一掌。
眼里的淚模糊了的視線,連霍昀洲的反應都沒看到,轉就走。
那一刻,眼淚掉下來,沒走一步,熱淚就不控制地涌出來。
回了出租屋沒多久,王媽給打電話。
“太太,你開下門吧。”
沈念安一時沒反應過來,打開門,王媽竟然背著大包小包站在家門口。
“您這是......”
王媽一臉開朗,“我實在不想看見那個蘇棠棠,先生說不想干就辭職,所以我就過來找您啦!”
沈念安一時難以分辨是不是霍昀洲派來的眼線,可這些年,王媽一直向著,在無數個夜晚陪聊心,和講悄悄話。
已經失去母親很多年了,王媽卻填補了這些空白。
“王媽,我這三年,是不是就是一場笑話?”
王媽滿是心疼地看著。
“太太,我說句實在的,您真的不應該就這麼走掉!反而應該留下來,讓蘇棠棠知道誰才是這個家的主人!”
猜你喜歡
-
完結797 章

厲少,你老婆又想離婚了!
蘇可曼曾經以為,她要嫁的男人,一定是溫潤如玉這款。可婚後,他惡狠狠地將她抵在牆角,咬牙切齒地說:「我對你沒興趣!」更過分的是他提出霸王條款:不準碰他、不準抱他、更不準親他。蘇可曼見識了他的冷漠無情,發現他就是一塊怎麼也捂不熱的石頭。她將離婚協議拍在桌子上,底氣十足:「老孃不幹了,我要和你離婚!」他一本正經道:「離婚?門都沒有窗更沒有!」後來小包子出生,她揚起小臉緊張地問:「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喜歡我的?」男人瀲灧眸光一閃:「寶貝兒別鬧,咱們該生二胎了!」
180.6萬字8 31774 -
完結914 章
重生八零辣妻當家
許卿直到死才發現,她感恩的後媽其實才是最蛇蠍心腸的那一個!毀她人生,斷她幸福,讓她從此在地獄中痛苦活著。一朝重生歸來: 許卿手握先機先虐渣,腳踩仇人吊打白蓮。還要找前世葬她的男人報恩。只是前世那個冷漠的男人好像有些不一樣了, 第二次見面,就把紅通通的存摺遞了過來……
161.9萬字8 137690 -
完結23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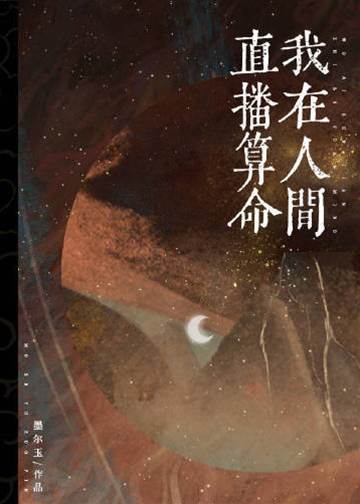
我在人間直播算命[玄學]
安如故畢業回村,繼承了一個道觀。道觀古樸又肅穆,卻游客寥寥,一點香火錢也沒有。聽說網上做直播賺錢,她于是也開始做直播。但她的直播不是唱歌跳舞,而是在直播間給人算命。…
134.6萬字8 964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