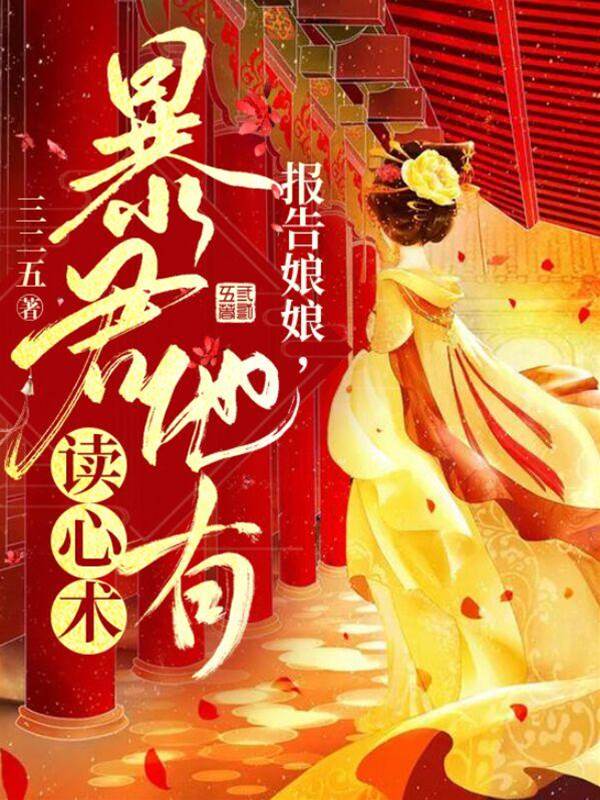《咬春靨》 第279章 送他菊花酒
謝妙云見到表妹胳膊上那道疤痕,瞳孔都了一下。
原因無他,只因兒家家都是的。
而阮凝玉胳膊上的傷疤不大不小,在下尤其明顯。那道疤猙獰又丑陋,出現在那雪白細膩的上,與纖細麗的胳膊形鮮明對比,讓看見的人心里都會嘆一聲:可惜了。
可惜了這麼好的皮,原來人也是有瑕疵的。
但阮凝玉此話一出,周圍的人都愣住了。
們都沒想到這道疤痕竟是這樣得來的。
謝妙云一時不知道該說什麼了,一人是所仰慕敬重的堂兄,一人又是喜的表妹。
總不能去罵堂兄吧?
謝妙云心十分復雜,很矛盾。
仰慕著堂兄,從來都覺得男人做過的決定便是對的,可今兒看見阮凝玉的傷疤卻搖了。
走過來的謝宜溫蹙眉,“當時沒涂藥膏麼?”
應該是能祛疤的才是。
春綠在旁邊替小姐委屈道:“回大姑娘,當時什麼藥膏都用了,什麼上好的丹參羊脂膏,或是旁的偏方,通通都用了,也真是奇了怪了,就小姐胳膊這一傷疤無論如何都好不了。”
沒忍住,低聲啜泣。
謝宜溫抿。
沒有哪個人能容忍這樣的疤痕陪伴自己一輩子,打心底地心疼阮凝玉。
謝妙云也在心里怨起謝凌起來。
堂兄未免也太鐵石心腸了些,當時竟然將阮妹妹打得那麼嚴重。剛剛那道疤痕真的嚇到了了,說不好聽的,就像只蟲子。
阮凝玉見兩位表姐這時看向的目里都帶了抹憐,一時覺得好笑,“不就是落下傷疤了,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有這樣的印記在倒能時刻讓表妹警醒些,切莫再做出私奔那等蠢事了。”
見二房這兩姐妹仍垮著張臉。
Advertisement
“真的,沒事,尋常人又見不到我裳底下的皮,不是麼?”
見阮凝玉跟沒事人一樣,還反過來安們,這對親姐妹的心更沉了下去。
別人是看不到,那阮凝玉今后嫁了人呢?
謝易墨就坐在們的邊上,是聽到了這番對話。
于是撥弄著手上茶盞的蓋子,事不關己地笑了笑,“難得聽阮表妹說了句極對的話。”
“表妹就是應該落下點難看的傷疤,這樣才能好好長長記呢。”
這會剛好是臺上的戲子停下來搬椅子重新布景的空當,于是這群姑娘家的話便清清楚楚地傳到了對面。
離得不遠,所以謝凌過去時,便看見了堂妹輕輕掀起了表姑娘的袖,他一眼就見到了烙在阮凝玉胳膊上的疤痕。
他那被日照淺棕的瞳孔了一。
表姑娘的在下白得過曝驚艷,如同上好的羊脂玉。可是這樣的卻被上面那道蟲子爬行似的疤痕給毀得一干二凈。
在謝老太太看過來之前,謝凌收回了目。
他接過嬤嬤遞過來的紫銅壽紋手爐,便將其塞在了老太太的手里,“祖母子不好,更要注意保暖才是。今兒便縱容祖母一回在外頭看半天的戲,待祖母的病好了,便將戲班子請到謝家個把月,隨祖母什麼時候聽膩。”
謝老太太卻留意到了姑娘們那邊說的話,方才也到謝凌看向了那邊。
謝老太太問:“怎麼,心疼了?”
見祖母心思探尋,謝凌低著頸,端的是君子的溫雅恭順,以及世家繼承人的淡薄。
“表姑娘了家規理應懲戒,何來心疼這一說?”
謝老太太看了他一會,這才相信了他說的是真心話。
謝凌不會因這點小事容,從而影響了緒,這才是所看重的長孫。
Advertisement
謝老太太手捧著手爐,繼續聽曲,慈目微闔,“不會便好,你是謝家大公子,行事一切都應以世家利益為重,這是你祖父告誡你的,你要永遠都記得。”
阮表姑娘為人輕佻,仗著自己的貌便肆意妄為。若不讓吃點苦頭和教訓,這樣的子今后嫁到別人府上遲早會害了。
謝凌為整理了蓋在上避寒的毯子,不見容,“祖母訓誡的是。”
謝老太太這才沒說什麼。
那笨手笨腳燙傷阮凝玉的小婢自然是被罰了。
阮凝玉被帶去隔間換了件裳回來,便無事發生,繼續聽戲曲。
那道丑陋的疤痕被重新掩在了裳底下,無人可窺見。
阮凝玉想,陪著老太太的男人應當沒聽見才對。
適才的聲音很小,而且也不愿意被他給知道。
若是被謝凌知道了,對而言無異于是再度回到那辱的祠堂,又被他重新鞭撻了一回,再度皮開綻,對是第二次的神侮辱。
謝妙云現在倒能理解阮凝玉為什麼那麼的怕堂兄了。
自己總覺得堂兄溫雅,可沒想到他竟會對表姑娘做出這種事來。
回去之后二房姐妹極心疼,于是謝宜溫給的海棠院送來了喜的檀香木手串,而謝妙云把最舍不得的那套玉石棋子也送給了。
阮凝玉覺得無奈,又好笑。
夜晚丫鬟侍候沐浴時,春綠捧著的胳膊,看著上面的疤痕,“看,連大姑娘三姑娘都心疼小姐。”
“要不讓奴婢再去問問偏方,看看能不能祛疤……”
阮凝玉卻道:“不用了。”
既然淡不了,就沒必要祛掉。
這樣留在的上,還能讓時時刻刻記得對謝凌的恨。
春綠想想就來氣,“今兒小姐去聽曲子的時候,奴婢總覺得大公子應該是聽到了。可他卻一點反應都沒有,當真冷。”
Advertisement
沐浴完后,婢又給阮凝玉子涂抹化玉膏。
從前當上皇后致慣了,如今雖然待遇差了很多,但還是會讓丫鬟去買名貴的膏用來保養,尤其是秋后天氣漸干,阮凝玉更是會每晚都涂。
為小姐涂上冰涼的化玉膏,春綠和抱玉對視了一眼,嘆:“小姐細皮,勝雪,尤其是常年帶著香,真不知道小姐以后會便宜了哪家府上的郎君。”
阮凝玉正在對著鏡子梳著半干的青,聞言卻心里微了一下。
明明努力克制著不再去回想跟沈景鈺在侯府的那夜。
可經兩個小丫頭一提,便又回想了那夜的瘋狂,上全是他留下的紅痕。
阮凝玉瞇起眼來。
雖然只有模糊的印象,可依稀記得那晚男人的材很是不錯,力也很好,看的眼神深沉又滾燙。
再想起年給寫的那些不含蓄又熱忱表達意的書信,阮凝玉的手就抖了抖。
也不知道沈景鈺在驍騎營怎麼樣了。
想到上次見面他上便帶了傷,阮凝玉有些擔心。
臨睡前,阮凝玉在床榻上翻,睜開眼睛,問著在塌邊守夜的春綠。
“我讓你調查的事怎麼樣了。”
春綠知道在說許清瑤,于是乖巧回答:“許姑娘自從出事了之后,便被那許大人勒令著不準出府一步。”
“現今風波已平,但還是沒有見到許姑娘出來過。”
阮凝玉合上了眼睛。
許伯威乃史臺的柱石,史大夫最重名譽,故此許伯威這段時間不會再讓許清瑤出來以免再引起流言蠻語。
可是難保許清瑤不會溜出府。
重登高,便是個再度見到謝凌的好時機。
在初九的前一日,阮凝玉總算在文廣堂見到了七皇子。
再次見到慕容深,是年讀完書剛剛從謝凌齋房出來的時候。
Advertisement
學了一天的慕容深怎麼也沒想到在門口竟見到,天微暗下來,他還險些以為是自己看錯了眼。
阮凝玉著鮮紅的石榴,比天邊的晚霞還要的艷。
那張臉在夕下,神圣不可直視,著他的眼眸中依然帶了難以言說的。
慕容深張得攥了手,可仔細一看的時候,卻發現阮凝玉旁還跟了位旁的姑娘,正是的大表姐。
他記得……這位姑娘做謝宜溫。
慕容深不可抑制地皺了眉心。
待確定這不是他的幻覺后,他忙上前,沉的眼亮了起來,“阮姐姐。”
又對著人的表姐作揖。
“謝大姑娘。”
謝宜溫對著七皇子萬福,盡管面冷淡,但眸卻要顯得溫和得多。
見他比之前眼底烏青更重了,阮凝玉更是心疼。
了下他的手,一片冰涼。
嘆著氣,柳眉蹙著,“天冷了,我再人給你做兩件披風。”
“你只管用心讀書,早日進文廣堂,有我跟謝先生在,其余的便不用想。”
謝宜溫見到自家表妹的作,心里微驚。
男授不親,表妹行為未免也太大膽了些。
可是阮凝玉給的覺卻很明坦然,而且看起來對七皇子也不是那種心思。反而更像是對待一個親人,弟弟之類的。
偏生七皇子也神淡淡的,早已習以為常。
兩人都這樣,向來被世家規矩管束的謝宜溫突然也覺得阮凝玉的行為極正常了。
被阮凝玉的手著,這些時日呆在謝凌邊的抑被一掃而空。
年上抑制的暴戾氣也得到了安,一顆心也漸漸平復。
連傍晚間的秋風也不再寒冷。
慕容深乖順地低著頭,“好。”
這樣看來,兩人的關系很像對待謝氏其他族弟的關心照顧。
于是謝宜溫也沒覺得什麼了,靜靜地看著。
過來,主要就是想見見這位七皇子……
明明是謝家嫡長,心高于天也慕強,可眼前這位沒沒無聞的七皇子卻莫名地吸引著的注意,也讓生了想幫助他的心思。
就是不知道……他對有沒有好,愿不愿意跟朋友。
阮凝玉在海棠院閑來無事便釀了花酒,這次過來為的就是把花酒帶給慕容深。
“明兒便是重了,這花酒你帶回去。”
重有飲花酒的風俗,其實就是花和糯米一起釀造的米酒。
酒能祛百病,解制頹齡。《西京記》中有記載重這日飲花酒,可令人壽長。
明日便是初九,文廣堂會放假。于是阮凝玉趕在重之前給七皇子送來了酒壇,為的就是討個好意頭。
民間忙著拜神祭祖,宮里的娘娘都在吃花糕,皇宮也會舉行大型宴飲活。
可是明天過節,那麼為七皇子的慕容深……便會孤獨了。
宮宴自然不會邀請他這個皇帝不喜的皇子,而他的生母早就不在了,加之文廣堂放了假,阮凝玉知道每逢佳節便是這個敏自卑的年最孤獨的時候,和在謝府的時候很像。
所以才會特地來給他送這花酒。
慕容深手里捧著酒翁,微笑,“謝謝阮姐姐。”
這時蒼山正好從齋房里走了出來,他本是要將男人的茶拿出去洗的,這時見到們,尤其是見到大小姐,于是過來行禮。
然后便要走。
阮凝玉卻住了他:“站住。”
蒼山回頭,“表姑娘,有什麼事麼?”
阮凝玉想了想,便讓春綠將手上的那只酒壇遞過去。
“這是我釀的花酒,特意送來給表哥,還請你替我將它拿給表哥。”
阮凝玉是這樣想的,畢竟慕容深了謝凌的學生。故此每到過節,最好送些禮給男人為慕容深攢點好,這也是人世故。
蒼山愣了愣,看著的目一時復雜。
他是畫舫那夜的目睹者,雖然他不知道當時二樓發生了什麼事,可是他卻能嗅出來不對勁。
那時謝凌抱阮凝玉下樓時,人上還多了件裳,蓋得嚴嚴實實的,所以他這個侍衛才會覺得后怕。
表姑娘這會兒反而過來“親近”長孫,他險些站不穩子。
“怎麼了?”阮凝玉警覺,總覺得他有點不對勁。
蒼山忙回神,“屬下現在就替表姑娘將東西給公子送過去。”
他捧著酒壇,轉便進去了。
須臾,便從里頭出來。
蒼山道:“公子讓屬下過來傳話,說是謝過表姑娘釀的酒,姑娘的心意他收到了。”
阮凝玉這才放心。
也知道謝凌在別人面前會給留下幾分面。
雖然不知道他會不會喝,但是既然他收下了,便是承了的。
慕容深卻抿了抿。
時候也不早了,謝妙云還在馬車上等著們。
于是阮凝玉與謝宜溫便和他道別。
走之前,阮凝玉在日暮下回過了頭,明眸笑了笑,里頭碎點點,“七皇子,明兒過節你便跟馮公公在宮里吃糕喝花酒吧,再去登高臺。”
“祝你祛病消災,歲歲重,安康常伴。”
的笑帶了夕的輝,眸彎彎的,紅紅的。
慕容深著阮姐姐,深了眼。
而后便轉了,跟表姐牽著手離開了。
只留慕容深站在原地捧著酒壇,靜默不語。
兩位姑娘已經不見影,慕容深看了看天邊的霞。
若他得了權勢……便能隨意地出府,也能和阮姐姐一起過重了。
有些念頭一旦萌芽,就再也抑制不了,只會瘋狂地生長。
到了翌日,便是重了。
猜你喜歡
-
完結1961 章

重生後,我嬌養了反派鎮北王
亡國前,慕容妤是宰相嫡女,錦衣玉食奴仆成群,戴著金湯匙出生,名副其實的天之驕女。亡國後,她成了鎮北王的通房。這位鎮北王恨她,厭她,不喜她,但她也得承受著,因為全家人的安危都掌握在他手上。然而在跟了他的第五年,慕容妤重生了。回到她明媚的十五歲,這時候,威懾四方的鎮北王還隻是她宰相府的犬戎奴。未來的鎮北王掰著手指頭細數:大小姐教他練武,教他讀書,還親手做藥丸給他補足身體的虧損,噓寒問暖,無微不至,把他養得威風凜凜氣宇軒昂,他無以為報,隻能以身相許!隻想借這棵大樹靠一靠的慕容妤:“……”她是不是用力過猛了,現在
208.9萬字8.18 52894 -
完結474 章

小皇叔腹黑又難纏
那一夜,他奄奄一息壓著她,“救我,許你一切。”翌日,她甩出契約,“簽了它,從今以后你是我小弟。”面對家人強行逼婚,她應下了當朝小皇叔的提親,卻在大婚前帶著新收的小弟逃去了外地逍遙快活。后來,謠言飛起,街頭巷尾都在傳,“柳家嫡女不知廉恥,拋下未婚夫與野男人私奔!”再后來,某‘小弟’摟著她,當著所有人宣告,“你們口中的野男人,正是本王!”
137.3萬字8 102572 -
完結46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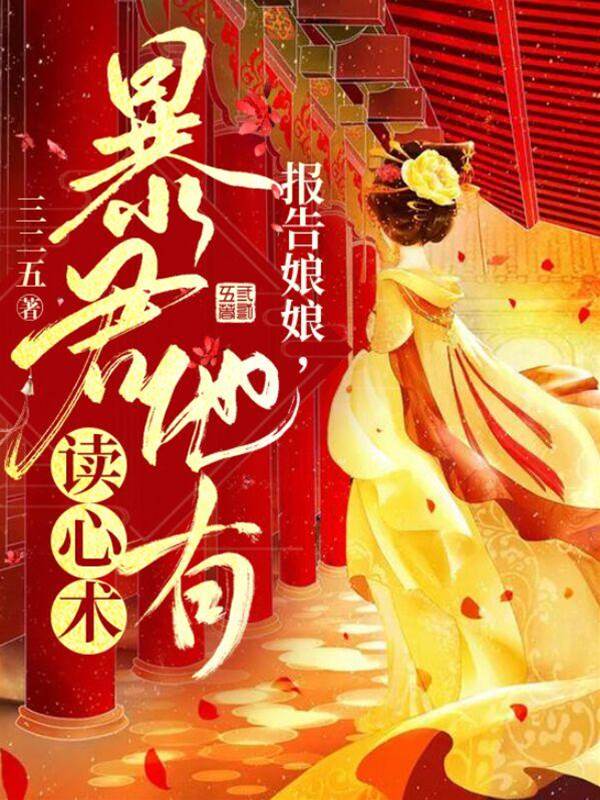
報告娘娘,暴君他有讀心術祝無歡鳳長夜
(雙潔 沙雕 救贖 爆笑互懟)穿越成史上死得最慘的皇後,她天天都想幹掉暴君做女皇,卻不知暴君有讀心術。暴君病重她哭求上蒼,暴君正感動,卻聽她心聲,【求上蒼賜狗暴君速死,本宮要登基!】暴君為她廢除六宮,…
87.7萬字8 21825 -
完結321 章

別人御獸,我召喚老公
許靈昀穿越初就面死局,為了活命,她為自己爭取到參加覺醒大典的機會。別人召喚出來的都是毛茸茸,而她在眾目昭彰中,召喚了只凄艷詭譎,口器森然的蟲族之王。 世人皆知,皇女許靈昀自絕靈之地走出,憑一己之力將燕金鐵騎逼退千里,又將海異人族的殿宇攪得天翻地覆,其兇殘鐵血展露無遺。 但他們不知道的是,當月色拂過樹梢,猙獰可怖的蟲族將少女納入柔軟的腹腔。 再之后,殘暴血腥的蟲族,乖張缺愛的人魚,狂暴兇殘的魔龍,無序的古神混沌之主,都只為她一人——俯首稱臣。
63.6萬字8 89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