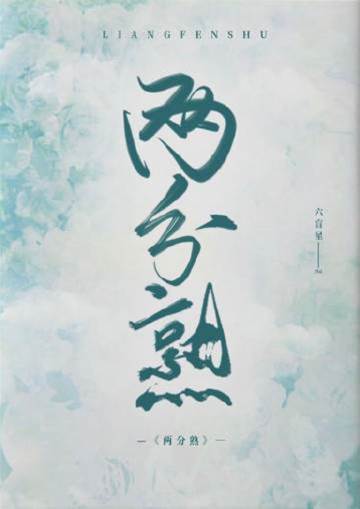《蓄意染指》 第1卷 第45章 “他怎麼敢!”
海恬四歲之前,爸爸葉顯榮和的媽媽還是十分恩的。
也是有滿墻芭比娃娃、有父母疼的小公主。
可四歲生日那天,葉顯榮和媽媽大吵一架,接著就離開了。
一年后,在商業雜志上看見葉顯榮和別的人在一起,邊還有一對和差不多大的龍胎。
年懵懂的也從媽媽崩潰大哭的話語里知道了。
原來所謂的爸爸,一直都有別的家。
而也不是他唯一的孩子。
更不是他所的孩子。
十七歲那年,消失很久的葉顯榮突然出現,喪偶的他娶了媽媽。
能明顯覺到媽媽的排斥,可不知道為什麼,他們還是領證了。
原本以為能有一個完整的家,終于不會被做沒有爸爸的野孩子了,可沒想到是更深的地獄。
哥哥葉昊天和姐姐葉輔歌對表現的極其不友好。
潑水,弄壞所有的東西,關在漆黑的屋子里……惡劣的行為越發的過分。
而那對兄妹對的媽媽也沒有毫敬畏,發現葉顯榮只是想要一個合適面的妻子,本不管家里如何之后,更是從欺負到開始欺負們母……
十八歲那年在高盧國出事后,在霉國呆了一年。
葉輔歌找到了,向展了自己的野心。
葉顯榮非常的重男輕,所以在他眼里真正的孩子只有葉昊天,這兩個兒只不過是將來可以“易”的籌碼。
Advertisement
葉輔歌夠了這種被支配的生活,所以背地里和海恬達了合作。
明面上還是哥哥的走狗,如惡一般的做盡壞事,明目張膽的欺負海恬。
但背地里,葉輔歌會如現在這般和通氣。
聽到葉輔歌提到媽媽,海恬著手機的手驟然用力,但沒有表心的真正緒。
畢竟與葉輔歌合作也只是與虎謀皮罷了。
著緒反問道:“既然你知道我和我媽的很單薄,又和我說這些有什麼意義?”
葉輔歌好似猜到了海恬會這麼說,輕笑一聲,是毫不掩飾的嘲諷,“海恬,好歹我們是合作關系,一點信任都沒有,豈不是要繞很多彎路?
你也不用對我這麼警惕,如果葉顯榮和葉昊天知道我和你暗度陳倉,是不會饒了我的,所以你手上也有我的致命籌碼,我們現在是一條繩上的螞蚱,你說,是吧?”
“你想說什麼?”海恬并不相信的話。
很清楚,葉輔歌也只是利用罷了,們之間的誼連塑料姐妹花都稱不上。
“我是想提醒你,和一個民宿小老板談是沒有前途的。”葉輔歌說到這兒突然停了下來,仔細的捕捉著海恬的緒。
“你怎麼知道。”海恬雖然極力的制自己的緒,可關心則,沒注意到說話語速比平時稍微快了一點。
Advertisement
葉輔歌無聲的笑了。
只是一點,就夠了。
因為知道海恬慌了。
看來海恬真的不知道蔣百川在城代表著什麼。
“親的妹妹,我都知道了,你說老頭子還能用幾天知道?他可是打算把你賣個好價錢的, 如果傳出來你和一個民宿小老板搞到一起了,貶值了,你說他會怎麼對付他呢?打斷他的另一條?嗤……”
葉輔歌三言兩語就把海恬一直埋藏在心底的擔憂和恐懼全都給掀出來了,讓最后一幻想都破滅了。
海恬的聲音控制不住的有點抖:“他怎麼敢!”
“啊,怎麼敢,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對了,既然你心里還殘留著一點僥幸,那我就好人做到底?今天早上的照片、發給你!”
葉輔歌說完,海恬的手機震了一下,點開V信頁面。
照片映眼簾的瞬間,覺渾上下的力氣仿佛都被了一般。
照片上,的媽媽出的皮都是淤青,無力的跪在地上,那單薄的影搖搖墜。
海恬用手的捂住自己的才沒有發出嗚咽聲。
“你也知道葉昊天是個神經病,總覺得我媽的死和你媽有關系,所以最近瘋的更厲害了。也不知道海阿姨還能多久?你說他們都敢對一個知名舞蹈家下黑手,你那個無權無勢的民宿小老板靠什麼?靠拳頭?靠一腔熱?只怕到時候沒的不是另一條了吧?”
Advertisement
葉輔歌聽著電話那頭的呼吸越來越急促,知道差不多了。
輕嘆一口氣:“我知道你的無力,我又比你好到哪兒去呢?看看我的名字,輔歌,輔佐那個傻哥哥的意思,從我出生的那一刻我也被拋棄了,注定要為葉昊天腳下的一條狗。
海恬,你和我都逃不了。要是往常我還能幫你多瞞兩天,讓你和你心的小人來個溫告別,可錢程在亞島的事兒鬧得沸沸揚揚的,葉昊天今天問了我你的事兒,對于你要推遲回來的計劃產生了疑慮,所以你最好今天晚上就回來,明天就帶著蘇予懷去葉家把訂婚的事兒敲定了。
否則要是被葉昊天提前知道了,呵,只怕惱怒的他會立馬把你塞給哪個年紀能當你爸爸的男人玩兒。
你知道的,葉昊天對你和你媽有多恨!”
海恬無力的癱坐在床上。
手指用力的被單,還在做最后的掙扎。
“不會的,他也就是在城有些勢力,手腳再長也不到亞島,我,我把媽媽接來……”
葉輔歌靜靜的聽著海恬說,直到的聲音越說越小,才著無奈回道:“瞧,你自己都沒辦法說服自己,是,你現在天高皇帝遠,只要不回來,和那個小老板領證結婚,生米煮飯,可以過你的小日子,可海阿姨走得了?走不了,葉家不垮,葉顯榮會放過?”
Advertisement
海恬沒出聲,手越發用力的竄,指骨青白,圓潤的指甲著手心,鈍鈍的疼。
“我不是想你,我只是把你不想不敢面對的現實告訴你,你留在亞島,只怕葉家那倆畜生會把氣全都撒在海阿姨上。
海恬,你應該沒有那麼恨吧?恨到想要死?”
猜你喜歡
-
完結1070 章

奉子成婚:古少,求離婚(又名:離婚時愛你)
新婚夜,他給她一紙協議,“孩子出生後,便離婚。” 可為什麼孩子出生後,彆說離婚,連離床都不能……
171萬字8 363580 -
完結46 章

你如星辰不可及
蘇清下意識的拿手摸了一下微隆的小腹,她還沒來得及站穩就被人甩在了衣櫃上。後腦勺的疼痛,讓她悶哼了—聲。
4.2萬字8 18278 -
完結7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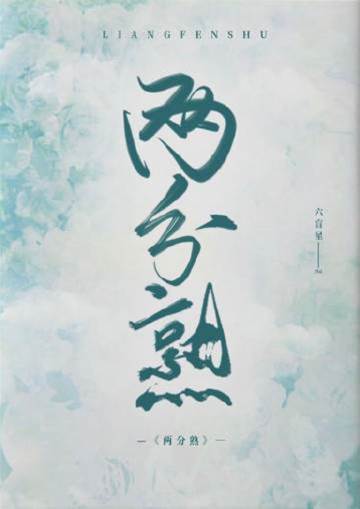
兩分熟
大學時,阮云喬一直覺得她和李硯只有兩分熟。學校里他是女粉萬千、拿獎無數的優秀學生,而她是風評奇差、天天跑劇組的浪蕩學渣。天差地別,毫無交集。那僅剩的兩分熟只在于——門一關、窗簾一拉,好學生像只惡犬要吞人的時候。…
25.3萬字8 6298 -
完結493 章
惡魔的寵愛
“以你的身材和技術,我認為隻值五毛錢,不過我沒零錢,不用找。”將一枚一塊的硬幣拍在床頭櫃上,喬錦挑釁地看著夜千塵。“好,很好!女人,很好!”夜千塵冷著臉,他夜千塵的第一次,竟然隻值五毛錢!再次見麵,他是高高在上的王,她是低到塵埃的花。一份價值兩億的契約,將她困在他身旁……
84.9萬字8 1488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