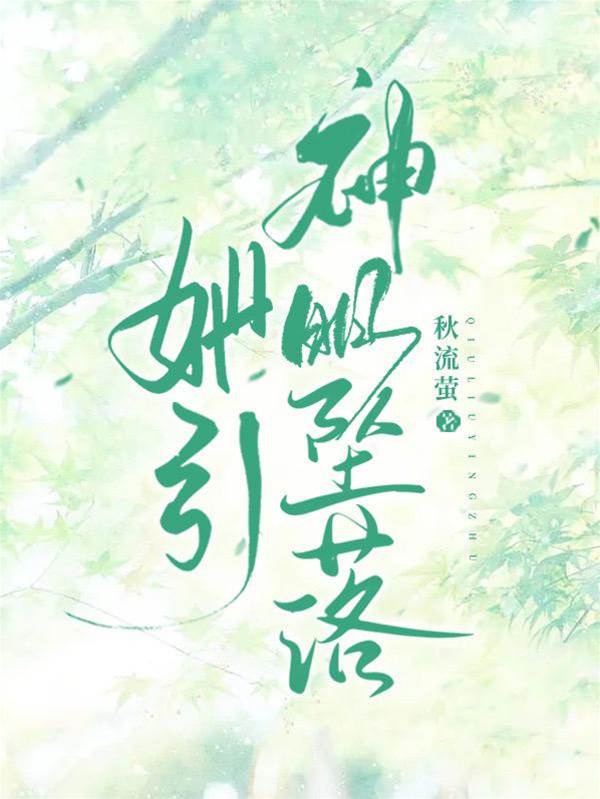《嬌嬈》 第1卷 第215章 終章
酣暢淋漓的結束了兩次,周驚寒咬著的耳垂饜足的輕。
唱晚咬著,無力地抱著男人的脖子輕聲哼哼,的腳腕被他生生握出一圈紅痕,指印清晰。
宛如綠寶石般的眸子逐漸聚焦,回想起剛才激烈刺激的一幕幕,紅著臉小聲他:“周驚寒...你剛剛...”
剩下幾個字沒好意思說出口。
周驚寒沒有做措施。
兩次都沒做。
男人嗯了聲,順著的肩頸線條吻上致的鎖骨,“怕不怕?”
唱晚搖頭:“...不怕。”
周驚寒俯去吻的脖子,細細咬,直至吻出點點曖昧紅痕,他叼住的耳垂,頭緩慢吞咽,聲音沙啞極了:
“那再來一次?”
他氣息滾燙的嚇人,唱晚不控制的抖了一下,半邊都麻了。
還沒等回過神,男人已經翻了上來,炙烈的吻侵襲而來。
“......”
等一切結束,周驚寒抱著人去了浴室,沖洗過后,兩人躺在床上,男人一手把洗得香噴噴的人兒摟進懷里肆意。
唱晚真的一力氣也沒有了,強撐著打起神,不讓自己倒頭睡下,仰頭問他:“周驚寒,...你今天心不好嗎?”
周驚寒低頭親了下的額頭,“怎麼看出來的?”
“....覺。”
“沒事。”頭頂傳來一道低低的笑聲,“現在已經好了。”
“......”
唱晚轉過,微仰起頭,一時間兩人四目相對。
臥室里只開了床頭的壁燈,暖黃燈影影綽綽,灑在那張俊無鑄的臉上,襯得臉部線條愈發深邃立,男人額前發還帶著一水汽,一頭黑發蓬松凌,眸幽深如寒潭。
“是不是出什麼不好的事了?”唱晚思索片刻,小聲問,“你要不要和我說說看?”
Advertisement
如果是因為工作的事惹得他心不好,那麼周驚寒吃完飯后肯定會進書房打電話或者開視頻會議,直到把手底下一堆人罵個狗淋頭才會罷休。
發完火后會非常分的從書房出來親親的臉,溫聲細語地問晚上想吃什麼夜宵...
而剛才幾次纏綿歡里,很明顯的察覺到,周驚寒帶了一發泄的味道在里面。
“跟周遠山有關。”
唱晚聽見這個名字,長睫撲閃,反應了幾秒才輕聲問:“是你父親?”
“他...怎麼了?”
唱晚有點張,不會是因為他們兩人結婚的事吧?
難道他父親又找周驚寒麻煩了嗎?
“他快不行了。”周驚寒語氣平靜,仿佛談論的只是一個陌生人的生死。
唱晚吃驚極了,“什麼?”
“肝癌晚期,也就這幾天的事了。”
“......”
“周驚寒...”
周驚寒著的手指,“他想見你。”
“......”
“我可以去見他的。”唱晚安他,“沒關系的。”
周驚寒上的臉,“我不會讓你見他。”
“都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但我了解他,他不是那種臨死之際就會突然開悟的人,我這個所謂的父親,固執了一輩子,沒有任何東西能改變他,也沒有任何東西值得他退讓。他這一輩子為了公司,為了董事長的位置,或直接或間接的害了不人。他眼里只有自己,其他人對于他而言,只分為兩種。”
“有用或者沒用。”
比如,周遠山需要宋氏穩定局面的時候,溫素對他而言就了棄子,周遠山可以毫不顧及肚子里的孩子,一腳將踹開,等到人老了,宋氏對他不構威脅的時候,再找個長得和相似的明星作為消遣,還給自己安了一個深的好人設。
Advertisement
再比如,周驚寒對周遠山沒什麼大用的時候,他的存在便是留給宋林染一家出氣的,等到他的價值顯出來,周驚寒就是一個絕好的聯姻工,陸氏加上他手里ST的份,一定可以讓周氏更上一層樓。
......
說到這里,他眼神越發漠然,“我對他...實在沒什麼父子之可言。”
“......”
唱晚盯著他的眉眼,心里發酸。
周驚寒低下頭,微涼鼻尖在臉頰上蹭了蹭,低聲重復:“我不會讓你見他。”
***
自那天去過一次醫院后,周驚寒再沒去看過周遠山。
周遠山是一周后離世的。
他的葬禮低調而隆重。
葬禮當天,周黎和周驚寒并肩而立,兩人俱是一襲黑,面肅穆冷凝,周驚寒手里牽著唱晚,底下一群人見此況神態各異,卻無一人敢開口置喙。
一旁的宋林染目在唱晚手指上的寶石戒指上一凝,隨即若無其事的移開了視線。
周驚寒花近億天價拍下一枚綠寶石戒指的事,最近在網上鬧得沸沸揚揚,連宋林染這種久居國外的人都聽見了風聲。
他今天牽著的人,莫非就是他的妻子?
藏得跟寶貝似的,這種場合才舍得讓個面。
底下的人心思各異,幾方勢力暗流涌,不約而同將視線聚集到唱晚上,其中暗含的打量與計算,令周驚寒眉峰緩緩攏起,眼神更是毫無溫度。
偏偏邊的姑娘一臉茫然,對黑暗深的危險無知無覺。
“怎麼了?”
唱晚仰頭,懵懵地問。
周驚寒無奈地搖頭,著的長發,“沒事。”
周遠山頭七過后的第二天晚上,周驚寒把唱晚進了書房。
端了一杯水放到他桌上,“找我有事嗎?”
周驚寒拉著到自己邊坐下,指著桌上的文件,“你過來簽個字。”
Advertisement
“簽字?”
唱晚疑地拿起那份文件,第一頁赫然寫著一行大字:份轉讓協議書。
指尖一頓,往下隨意翻看幾眼,接著便是滿臉愕然。
周驚寒居然準備送周氏百分之二十的份。
男人掐掐的臉蛋,“怎麼這個表?”
唱晚把手里的文件遞給他,一時訥訥無言。
“這是你在周氏安立命的本錢。”周驚寒把簽字筆塞到手里,“有了它,才沒人敢輕視你,欺負你,知道了嗎?”
“簽字。”
他敲敲桌子,提高音量重復道。
唱晚和他對視良久,猶豫又猶豫,最終還是在他越來越不爽的表里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周驚寒拿起文件,順手的腦袋,“沒事了,去玩吧。”
“......”
自周遠山過世,這座城市竟綿綿下了一個多月的雨。
等到上弦月重現天際,已經是除夕夜了。
雨后天溫潤,水汽尚存,傍晚時分,輕煙薄霧籠罩全城。
除夕這晚,周驚寒特地帶唱晚去外面吃的飯,兩人還喝了點酒。
那果酒的后勁有些出乎周驚寒的意料,唱晚貪甜多喝了兩杯,沒多久就醉得迷迷糊糊,在包廂里的時候就黏上去抱著他的腰綿綿的撒。
周驚寒放下手里的杯子,濃眉微挑,指腹在額頭點了點,“以后我不在,不許在外頭喝酒,瞧瞧你這傻呼呼的模樣,被人賣了都不知道。”
“...新年快樂。”
唱晚醉醺醺的,完全沒聽懂他的揶揄,自顧自的說完話,仰頭蹭蹭他的下,吧唧在他上親了口。
綿果酒香混雜著孩子清甜的氣息撲面而來,周驚寒回味著剛才一即離的吻,眸漸深,“回家再親。”
周驚寒把人帶回家,伺候洗完澡,又在浴室里收夠了利息,再出來時已是深夜。
Advertisement
唱晚捧著蜂水靠在周驚寒懷里慢悠悠喝著,兩人一道窩在沙發上,電視機里正在放春晚,兩只小貓的呼嚕聲此起彼伏,歲月如此靜好。
快十二點的時候,周驚寒抱著回了臥室,兩人相擁著躺下。
“周驚寒。”
“嗯?”
大約是酒勁還沒散,那些憋了很久的話在這個寂靜的除夕夜里慢慢吐出來。
“...我爸爸去世十多年了,我記得你以前見過他的。”
周驚寒睜開眼睛,嗯了聲,“我記得。”
黑夜里的眼睛亮晶晶的,“他是法國人,小時候哄我睡覺,他常常為我講《圣經》的故事,可是自從他去世后,我就再也沒讀過《圣經》了。”
周驚寒靜靜聽著。
“但是有一卷我記得非常清楚,是《新約》里的一卷書,名《馬太福音》,里面有一段話是這麼說的:如果你的右手你跌倒,那就把它砍下來丟掉。”
“寧可缺失百中的一,不全陷在地獄里。”
“這些話我從來沒和別人說過,連曼曼也不知道,但我想告訴你。”
周驚寒抬眸,“你說。”
“你父親曾來找過我,和我說過一些話,那些話雖然不好聽,但它是事實,所以我并沒有怨恨過他,也從來沒介意過這件事...包括鄭柯宇和我姨媽找來的那個男人。他們是那只拉我進地獄的右手。我明白,那不是我的錯,也不該由我承擔那些不好的緒。”
周驚寒吻的眼睛,“你這麼想是對的。”
“所以我想告訴你。”唱晚彎起角,輕輕地說,“你也是時候把那只右手丟掉了。”
“....好。”
話音剛落,恰在此時,零點升空的煙花響徹天際,繽紛流破開冰冷死寂的長夜,周驚寒忽然扣住唱晚的后頸,與十指扣,溫地吻了上去。
“寶貝新年快樂。”
角落的霾剎那間一掃而空。
差一點,只差一點。
他終將被恨意浸,勘不破的真諦。
轉眼凜冬呼嘯而過,枝椏再度生出綠芽,蟻蟲破繭蝶,冰雪消融,綠意接天。
東風起,花滿園,梨花飛過秋千去。
暖香熏人醉,共赴春天里。
——全文完
***
***
***
***
下面的話是我寫這篇文的一些想,不興趣的同學可以忽略。
這是我寫的第二篇文,陸陸續續寫了五個月,和第一篇文差不多,我從頭到尾都是更。
在無大綱,無存稿且番茄不給量的況下,寫完一本書真的需要莫大的勇氣與耐心。
人的力是有限的,魚和熊掌不可兼得。
十月和十一月我因為學業問題難以維持穩定更新,而斷更的那段時間里,我收到了許多讀者的鼓勵,也正是這些鼓勵,讓我在考試、論文和專業課程的多重力下,堅持將這個故事寫完。
謝所有追讀至此的讀者。
到了這里,我還想再提一下寫這篇文的初衷。
這個故事的核可以用兩個字來概括——釋懷。
在我看來,人的緒是一把無形的利劍。
如果是人控制緒,那他將所向披靡,倘若是緒控制了人,那他將陷無止境的耗。
在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里,難免遇見各種事,而這些事,無時無刻都牽引著我們的緒,例如原生家庭,學習績,男等等。
希大家心底生出不好的緒時,能及時將那只妄圖拖你地獄的右手砍下來扔掉。
祝你也祝我,往后大步向前,前路只有明。
謝謝。
下一本,傅行深X楚歸梵。
這本會輕松搞笑很多。
書名暫定,封面暫定,文名暫定,開文時間暫定...
至于本書番外,寒假的時候我會開個腦,假如周驚寒帶著記憶回到墓園再遇那一天,會發生什麼事呢?
敬請期待~
再次謝看到這里的讀者,你們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力!!!
你們!!!
猜你喜歡
-
完結3328 章

先婚後愛:BOSS輕點寵
她以為離婚成功,收拾包袱瀟灑拜拜,誰知轉眼他就來敲門。第一次,他一臉淡定:“老婆,寶寶餓了!”第二次,他死皮賴臉:“老婆,我也餓了!”第三次,他直接撲倒:“老婆,好冷,來動一動!”前夫的奪情索愛,她無力反抗,步步驚情。“我們已經離婚了!”她終於忍無可忍。他決然的把小包子塞過來:“喏,一個不夠,再添兩個拖油瓶!”
591.3萬字8.46 320926 -
完結3045 章

天價萌妻:厲少的33日戀人
他是歐洲金融市場龍頭厲家三少爺厲爵風,而她隻是一個落魄千金,跑跑新聞的小狗仔顧小艾。他們本不該有交集,所以她包袱款款走得瀟灑。惡魔總裁大怒,“女人,想逃?先把我的心留下!”這是一場征服與反征服的遊戲,誰先動情誰輸,她輸不起,唯一能守住的隻有自己的心。
236.6萬字8 23019 -
連載1815 章

枕上歡:老公請輕點
唐慕橙在結婚前夜迎來了破產、劈腿的大“驚喜”。正走投無路時,男人從天而降,她成了他的契約妻。唐慕橙以為這不過是一場無聊遊戲,卻冇想到,婚後男人每天變著花樣的攻占著她的心,讓她沉淪在他的溫柔中無法自拔……
318.3萬字8 35129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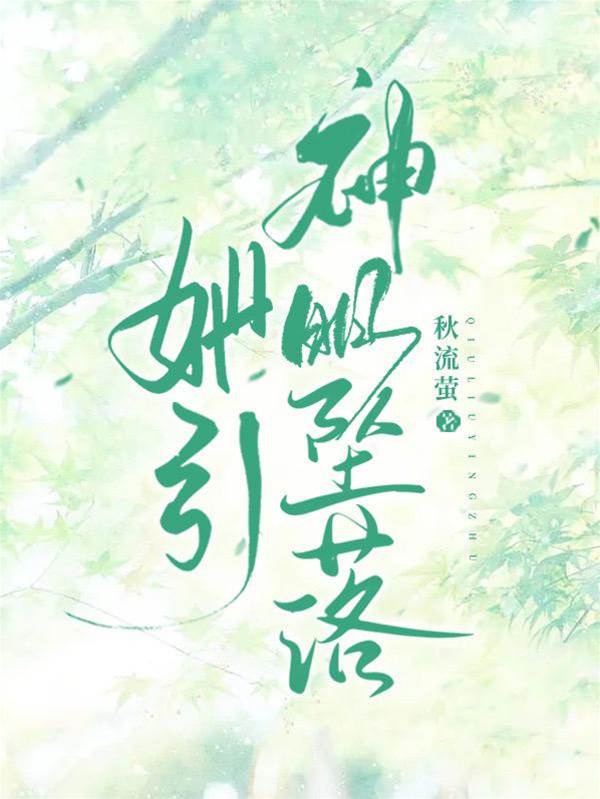
她引神明墜落
沈黛怡出身京北醫學世家,這年,低調的母親生日突然舉辦宴席,各大名門紛紛前來祝福,她喜提相親。相親那天,下著紛飛小雪。年少時曾喜歡過的人就坐在她相親對象隔壁宛若高山白雪,天上神子的男人,一如當年,矜貴脫俗,高不可攀,叫人不敢染指。沈黛怡想起當年纏著他的英勇事蹟,恨不得扭頭就走。“你這些年性情變化挺大的。”“有沒有可能是我們現在不熟。”宋清衍想起沈黛怡當年追在自己身邊,聲音嬌嗲慣會撒嬌,宛若妖女,勾他纏他。小妖女不告而別,時隔多年再相遇,對他疏離避而不及。不管如何,神子要收妖,豈是她能跑得掉。某天,宋清衍手上多出一枚婚戒,他結婚了。眾人驚呼,詫異不已。他們都以為,宋清衍結婚,不過只是為了家族傳宗接代,那位宋太太,名副其實工具人。直到有人看見,高貴在上的男人摟著一個女人親的難以自控。視頻一發出去,薄情寡欲的神子人設崩了!眾人皆說宋清衍高不可攀,無人能染指,可沈黛怡一笑,便潦倒萬物眾生,引他墜落。誰說神明不入凡塵,在沈黛怡面前,他不過一介凡夫俗 子。
20.2萬字8 45509 -
完結191 章

你有男閨蜜,就不要纏著我了
結婚前夕。女友:“我閨蜜結婚時住的酒店多高檔,吃的婚宴多貴,你再看看你,因為七八萬跟我討價還價,你還是個男人嗎?!”“雖然是你出的錢,但婚房是我們倆的,我爸媽可
33.3萬字8.18 289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