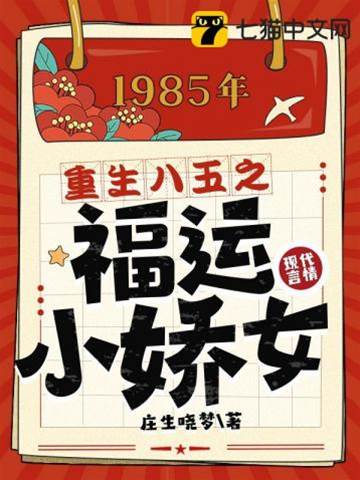《溺養嬌臠》 第1卷 第207章 越過山丘,總會有你的豁然開朗
“啪嗒”一聲,安全帶松開,帶了些力度,扣敲到車門。
男人坐回駕駛座,眼睛微挑,看著副駕駛的絕,啞聲:“好。”
虞晚晚從駕駛座爬了過來。
謝廳南輕拍了一下:“小東西,坐好了。”
他單手控制方向盤,另一手,扣好安全帶。
一路聽著淮揚小調,他卻把車子開的四平八穩,偶爾會輕斥晚晚:
“累了就睡會,大半夜還這麼鬧?”
“大半夜,正當時。”氣的捂他的。
車子在一幽靜的小山里停了下來,周圍有連片的木屋別墅。
一寬闊平坦的空地上,帶了白晝的。
男男圍坐在餐墊旁,品著酒,聊著天,吹著半夜的微涼夏風,舒適而愜意。
謝廳南慢條斯理的認真給虞晚晚清理著:“這片老邢開發的地兒,帶你來玩玩。”
“可真會選時間,大半夜的。”
虞晚晚看著那認真給自己凈手的男人,一一手指,仔細的清理,細致到指的紋路。
“瞧不上?熬到半夜專程給你接風。”
Advertisement
“你奚落你自己媳婦兒。”
謝廳南很這樣的撒,眉眼帶了星點笑意,取過披肩把包好,直接抱著下車。
雙雙對對的朋友,相的都在,也有關系稍次一些的,全都是一個圈子里的。
是給和謝廳南專組的“單趴。”
虞晚晚一眼看到了林茵,偎著譚定松,被男人手臂攬著腰。
“了。”謝廳南的聲音在耳畔。
從那晚譚定松把人帶走,虞晚晚就到了進度條拉滿的節奏。
如今,出了趟國的時間,水到渠。
意料之中。
男人們玩牌的時候,林茵走過來,遞給了虞晚晚一杯雪利酒。
“速度夠快,或者說,證也領了?”虞晚晚彎。
“敢擋你的道嗎?我不得先完你的伴娘任務,狠鬧一波你和謝二爺的房啊。”
林茵笑著和虞晚晚杯。
“不用專門鬧,天天房。”虞晚晚輕挑眉,淺啜了一口杯中酒。
“蛙趣,”林茵搖著頭。
沒什麼可矯的。
握住謝廳南和譚定松這樣的男人,要的是段位,最沒用的就是矯。
Advertisement
“見過家人了?”虞晚晚一針見。
“見了譚夫人,算說得過去。當然,還有個人,你也,”林茵調皮笑了笑:
“定松他妹妹。能不能把當一個完整的人看,需要觀察。看理不看親。何況,”林茵飲下杯中酒,瞥了眼男人堆里笑容漸多的譚定松:
“定松工作很忙,我也很忙。他父親在京的時候,會見一面,再回趟我家。父母沒意見,基本就定下來了。”
“好。”
“個料,譚曉松相親了。”
虞晚晚想到了那晚茶店的遇見,淡聲:“那驕傲的格,能接家里安排的相親,倒是個重要的改變。”
“所以,相親失敗。還卡著你家二爺那條件找呢,都孩子他爸了,圖什麼?”
虞晚晚沒有說話。
有的人,不會輕易降低自己的標準,固守自己的驕傲。
因為驕傲本就是一種習慣,為自己活早就了一種態度,所以,不可能會遷就任何人。
心靈相通有時候很巧妙。
Advertisement
同樣的夜晚,譚家大宅的一簡約致的歐式臥室里,譚曉松睡不著,穿了睡起,來到窗前,點燃一士香煙,著窗外夜,眼睛卻沒什麼聚焦。
因為和謝廳南的那次失敗訂婚,幾乎了京圈核心的邊緣人。
除了在名媛圈里看一些明爭暗斗比男人的無趣臉,已經進不了真正核心子弟的局。
突然了邊緣人,這比讓訂婚失敗更煩躁。
尤其經了白男E的惡心一遭,又在遇到相親男人時候直覺的不適,短時間里,都不想再。
狗屁不是。
陳叔給安排的那男人,門當戶對,學業和工作履歷十分鮮,三十五歲的年紀,比譚定松職位還高一級。
可惜,個頭比高不了多,還有輕微的禿頂。
譚曉松勾笑了笑,想起了謝廳南的樣子。
如今,不是還對那個男人存著什麼居心,一高門子,屬實做不出惦記別人老公這種齷齪事。
只是,那男人的標準,已經在心里深固,不會為任何人降低標準,否則,不如獨。
Advertisement
想通也看了這些,忽然覺得窗外那譚家大宅,如牢籠一般,一時讓自己有些不過氣。
謝廳南和虞晚晚要結婚了,自己哥哥譚定松,也即將把林茵領進門。
京市八月的天,推開窗,帶了暑熱的窒息。
沒有猶豫,取出手機,手指翻間,定好了白天的機票。
從京城,到曼哈頓。
想回到自己悉的世界里自由呼吸。
或許,再次回來,的皮囊仍然是譚曉松,心已經重生……
猜你喜歡
-
完結1161 章
他養的小可愛太甜了
他是商界數一數二的大人物,眾人皆怕他,隻有少數人知道,沈大佬他……怕老婆! 沈大佬二十八歲以前,對女人嗤之以鼻,認為她們不過是無能,麻煩又虛偽的低等生物。 哪想一朝失策,他被低等生物鑽了空子,心被拐走了。 後來的一次晚宴上,助理遞來不小心摁下擴音的電話,裡麵傳來小女人奶兇的聲音,「壞蛋,你再不早點回家陪我,我就不要你了!」 沈大佬變了臉色,立即起身往外走,並且憤怒的威脅:「林南薰,再敢說不要我試試,真以為我捨不得收拾你?」 一個小時之後,家中臥室,小女人嘟囔著將另外一隻腳也塞進他的懷裡。 「這隻腳也酸。」 沈大佬麵不改色的接過她的腳丫子,一邊伸手揉著,一邊冷哼的問她。 「還敢說不要我?」 她笑了笑,然後乖乖的應了一聲:「敢。」 沈大佬:「……」 多年後,終於有人大著膽子問沈大佬,沈太太如此嬌軟,到底怕她什麼? 「怕她流淚,怕她受傷,更……怕她真不要我了。」正在給孩子換尿布的沈大佬語重心長的
105.2萬字8 125199 -
完結3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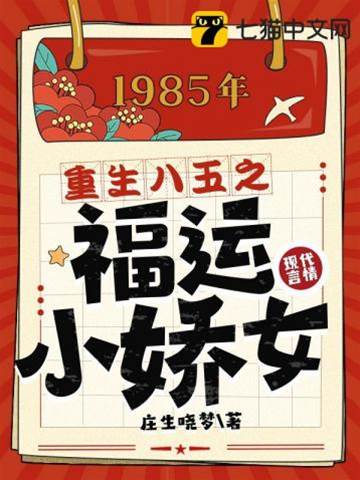
重生八五之福運小嬌女
前世,喬金靈臨死前才知道爸爸死在閨蜜王曉嬌之手! 玉石俱焚,她一朝重生在85年,那年她6歲,還來得及救爸爸...... 這一次,她不再輕信,該打的打,該懟的懟。 福星錦鯉體質,接觸她的人都幸運起來。 而且一個不留神,她就幫著全家走向人生巔峰,當富二代不香嘛? 只是小時候認識的小男孩,長大后老是纏著她。 清泠儒雅的外交官宋益善,指著額頭的疤,輕聲對她說道:“你小時候打的,毀容了,你得負責。 ”
70.5萬字8 20503 -
連載552 章

妻女死祭,渣總在陪白月光孩子慶生
【重生+雙潔+偽禁忌+追妻火葬場】和名義上的小叔宮沉一夜荒唐后,林知意承受了八年的折磨。當她抱著女兒的骨灰自殺時,宮沉卻在為白月光的兒子舉辦盛大的生日宴會。再次睜眼,重活一世的她,決心讓宮沉付出代價!前世,她鄭重解釋,宮沉說她下藥爬床居心叵測,這一世,她就當眾和他劃清界限!前世,白月光剽竊她作品,宮沉說她嫉妒成性,這一世,她就腳踩白月光站上領獎臺!前世,她被誣陷針對,宮沉偏心袒護白月光,這一世,她就狂扇白月光的臉!宮沉總以為林知意會一如既往的深愛他。可當林知意頭也不回離開時,他卻徹底慌了。不可一世的宮沉紅著眼拉住她:“知意,別不要我,帶我一起走好嗎?”
101萬字8.33 177888 -
完結179 章

灼灼浪漫
大雨滂沱的夜晚,奚漫無助地蹲在奚家門口。 一把雨傘遮在她頭頂,沈溫清雋斯文,極盡溫柔地衝她伸出手:“漫漫不哭,三哥來接你回家。” 從此她被沈溫養在身邊,寵若珍寶。所有人都覺得,他們倆感情穩定,遲早結婚。 有次奚漫陪沈溫參加好友的婚禮,宴席上,朋友調侃:“沈溫,你和奚漫打算什麼時候結婚?” 沈溫喝着酒,漫不經心:“別胡說,我把漫漫當妹妹。” 奚漫扯出一抹得體的笑:“大家別誤會,我和三哥是兄妹情。” 她知道,沈溫的前女友要從國外回來了,他們很快會結婚。 宴席沒結束,奚漫中途離開。她默默收拾行李,搬離沈家。 晚上沈溫回家,看着空空蕩蕩的屋子裏再無半點奚漫的痕跡,他的心突然跟着空了。 —— 奚漫搬進了沈溫的死對頭簡灼白家。 簡家門口,她看向眼前桀驁冷痞的男人:“你說過,只要我搬進來,你就幫他做成那筆生意。” 簡灼白舌尖抵了下後槽牙,臉上情緒不明:“就這麼在意他,什麼都願意爲他做?” 奚漫不說話。 沈溫養她七年,這是她爲他做的最後一件事,從此恩怨兩清,互不相欠。 那時的奚漫根本想不到,她會因爲和簡灼白的這場約定,把自己的心完完全全丟在這裏。 —— 兄弟們連着好幾天沒見過簡灼白了,一起去他家裏找他。 客廳沙發上,簡灼白罕見地抵着位美人,他被嫉妒染紅了眼:“沈溫這樣抱過你沒有?” 奚漫輕輕搖頭。 “親過你沒有?” “沒有。”奚漫黏人地勾住他的脖子,“怎麼親,你教教我?” 衆兄弟:“!!!” 這不是沈溫家裏丟了的那隻小白兔嗎?外面沈溫找她都找瘋了,怎麼被灼哥藏在這兒??? ——後來奚漫才知道,她被沈溫從奚家門口接走的那個晚上,簡灼白也去了。 說起那晚,男人自嘲地笑,漆黑瞳底浸滿失意。 他凝神看着窗外的雨,聲音輕得幾乎要聽不見:“可惜,晚了一步。”
30.6萬字8.18 1853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