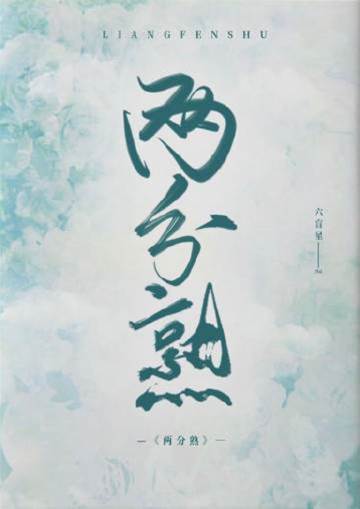《夏夜有染》 第1卷 第167章 番外:“愿不愿意嫁給我?”
日子一天天過得很快。
許恩棠還沒畢業,邊開始陸續有人結婚了。
第一次收到婚禮的邀請是高二高三時坐前面的薛昂。他和還有林佳羽一直有聯系。
今天結婚的是談霽禮的師兄邢彥。
談霽禮去當伴郎。
通常伴郎是要幫新郎擋擋酒的,防止新郎被灌得太厲害。
談霽禮屬于空有一張臉,但沒什麼用的伴郎。
好在還有另外三個,不然他和邢彥誰幫誰擋酒還不一定。
許恩棠臨近畢業,最近很忙。
白天有事,就晚上去參加了婚宴。
談霽禮的座位就在旁邊,不過他當伴郎忙的,大部分時間不在。
邢彥的婚禮很圓滿。
結束后,許恩棠留下來等談霽禮,正好和夏凝打了個電話。
夏凝本科畢業后去了麻省理工,繼續學的計算機科學,才回國沒多久。
現在留在A大做科研。
聊了幾句后,許恩棠問起的生活。
上次打電話的時候,夏凝說有個麻省理工的校友在追。
夏凝在電話里說:“已經被我拒絕啦。”
許恩棠問:“怎麼了?我看照片長得還好的。”
夏凝說:“他沒什麼問題,主要是我自己不想談。”
之前許恩棠和聊過,可能是父母影響,對婚姻和沒什麼期待。
許恩棠尊重的想法,覺得現在這樣也很好。
只要開心,別的什麼都不重要。
打完電話沒多久,談霽禮來了。
他今天穿了伴郎統一的西服,口別著朵花。
“結束了?”許恩棠站起來問。
談霽禮:“嗯。”
許恩棠看了看他,覺得他好像有哪里不對,眼睛水瀲滟的,讓他的眼神有些看不清。
這時候,送完親戚的邢彥走過來,“你小子沒事吧?”
談霽禮懶懶散散地抬了下手,“沒事。”
Advertisement
許恩棠問:“怎麼了?”
邢彥抱歉地說:“他喝了點酒。”
許恩棠看向談霽禮,問:“你喝酒了?”
邢彥:“是我一個表哥喝多了,非要跟他喝,我本來攔著的,正好跟人說話,一轉頭他已經喝了。應該……沒多,就一小杯……或者兩小杯白的。”
他說得有些心虛。
這時,談霽禮自己說:“沒多。”
邢彥說:“看起來還行。”
許恩棠:“……”
可是發現他的語調明顯比平時慢了點。
垂在側的手被牽住。
談霽禮對上的眼睛,說:“回家,棠棠同學。”
許恩棠:“……”
怎麼起“棠棠同學”了。
他很在別人面前這麼的。
談霽禮又拽拽地抬起空著的那只手,了指尖,對邢彥說:“不用送。”
“……”
什麼時候要送你了。
邢彥對許恩棠說:“喝多了吧?”
談霽禮幽幽地說:“沒有。”
許恩棠:“應該沒事,師兄,我們走了。新婚快樂。”
某人拽里拽氣:“新婚快樂。”
許恩棠和談霽禮一起離開。
進到電梯,打量著談霽禮。
他面朝電梯門,眼瞼微微耷拉著,表看起來很正常,走路也穩的,就是臉有些紅。
“二漂亮?”試探地喊他。
“嗯……”
好乖。
他平時可不會這麼乖地答應。
但鑒于他也不是沒裝醉過,許恩棠又試探。
“談霽禮小朋友?”
隔了一兩秒,談霽禮轉過頭看向的眼睛,認真又無辜地問:“我有什麼事嗎?”
“……”
許恩棠沒忍住,角上揚。
真的喝醉了,語調都帶小尾了。
電梯門打開,談霽禮收回目,拉著走出去。
來到他們車前,他自覺地上了副駕。
許恩棠繞到主駕那邊上車,看見他正低著頭在扣安全帶。
Advertisement
發頂沖著這邊,黑的短發很,看起來茸茸的,讓很想一把。
剛想手,這人扣好安全帶,抬起了頭。
許恩棠只好作罷。
把車開出地庫后,問:“你怎麼喝那麼多啊?”
他平時都不喝酒的,誰都灌不他。
這麼多年也就大一那次喝醉過。
談霽禮喝醉了是有問必答的那種。
他慢吞吞地回答:“邢彥結婚了。”
許恩棠:“……他結婚你為什麼要喝多啊?舍不得他?”
談霽禮轉過頭看向,直直地看了幾秒,不理解地問:“我又不喜歡他,為什麼要不舍得他?”
之后他沒再說話,低著頭,一副要睡著的樣子。
許恩棠等紅燈的時候看了他幾眼,以為他睡著了。
結果車一到北壹號停下來,他就解開安全帶下車。
進門后,他徑直往書房走。
這人不會喝醉了還想著工作吧?
許恩棠不放心地跟過去,看見他坐在電腦前的椅子上,在屜里慢慢地翻找著什麼。
第一個屜找完,找第二個。
許恩棠好奇地問:“你找什麼?”
話音落下,看見他從屜里拿出一個小盒子,絨面的。
談霽禮打開盒子,里面是枚鉆戒。
看到盒子,許恩棠大概猜到是什麼了,但真的看見還是愣住一下。
問:“你什麼時候買的?”
終于找到戒指的談爺抬起頭,乖乖回答說:“畢業的時候。”
還沒畢業,那就是他畢業的時候。
都好幾年前了。
許恩棠很驚訝,問:“那你為什麼沒給我?”
“因為那時候你還太小了,還要讀書。”談霽禮的聲音黏糊糊的。
許恩棠的視線落在那枚鉆戒上,心里很。
“棠棠同學。”談霽禮喊。
許恩棠視線上移,對上他的眼睛。
他是坐著的,而倚在桌邊,他仰著頭。
Advertisement
他的眼睛很亮,因為喝醉了,像有水波,映著的樣子。
他表很認真,眼神不太清晰,每一個字都拖著尾調:“你可以跟我結婚嗎?”
語氣像玩過家家的小朋友問結不結婚一樣。
許恩棠:“……”
他這算求婚嗎?
哪有人這樣求婚的。
見沒有說話,談霽禮幽幽地問:“你不想跟我結婚嗎?”
語速緩慢。
他又更加幽怨:“那你想嫁給誰。”
“……”
許恩棠拿他一點辦法都沒有,好笑地說:“嫁給你。”
嫁給你嫁給你。
談霽禮隔了一兩秒才沖一笑。
“哦。”
某人喝多了也沒忘記要把戒指戴到許恩棠的手上。
他握住許恩棠的手,要把戒指戴上去。
但是試了兩次,都沒戴準,戒指蹭著許恩棠手指的邊緣過去。
談霽禮抬起頭,無辜的語調里帶著點委屈:“不是都答應了嗎?為什麼不讓我戴。”
許恩棠:“……”
“撲哧”一聲笑了出來,“談霽禮,你這樣好可啊。”
談爺一點笑不出來,很哀怨。
許恩棠沒忍住用另一只手了他的短發。
某人頂著張很拽很不開心的臉,還配合地把腦袋湊了過來。
許恩棠多了兩下,收回手,然后主把指尖送進戒圈。
“戴吧。”
談霽禮終于順利地幫把戒指戴上。
之后,一直到睡覺,許恩棠不知道聽了多聲“老婆”了,每一聲都拖著小尾。
睡覺前,某人又湊上來。
許恩棠說:“睡覺了,談霽禮。”
談霽禮“哦”了一聲,靠近的耳邊,“晚安,老婆。”
……
翌日,許恩棠早早起來寫論文。
到快中午的時候,談霽禮起來了。
許恩棠聽到靜就沒什麼心思寫下去了,上下劃著文檔。
洗了個澡后,談霽禮帶著一水汽來找。
Advertisement
許恩棠擋住手上的戒指,試探問:“你醒了?”
談霽禮“嗯”了一聲,走過來手按上的后腦,了垂順的頭發,低頭在臉上親了下,問:“幾點起來的?”
許恩棠抬起頭看他,回答說:“八點多。”
注意到的視線,談霽禮問:“看我做什麼?”
看來這人真不記得了。
怎麼能連求婚都不記得。
許恩棠:“你昨晚喝了多酒啊?”
涉及酒量問題,談爺的眉梢輕輕抬了抬,有些回避。
正好這時候手機響了。
他拿著手機說:“沒多。我接個電話。”
說完他就走了。
談霽禮的電話打了半個多小時,打完就到吃飯的點了。
今天中午他們在家吃,是周姨安排的阿姨來做飯。
許恩棠放下電腦,走過來坐下。
談霽禮宿醉過后沒什麼胃口,整個人懶洋洋的,一只手支著腦袋。
看見來,他漫不經心地瞥一眼。
隨后他頓了頓,又朝看過去,目落在的手指上,懶散的樣子也收了起來,整個人像是被定住。
“……”
“……”
一陣寂靜過后,他找回自己的聲音。
“……你這是……哪來的?”
許恩棠本想照實說的,話到邊又想抓住這個難得的機會逗逗他,“前幾天買的。”
“……”
談霽禮放下筷子起去書房。
應該是去確認了。
但他一去就去了十來分鐘。
在許恩棠以為他不準備吃飯的時候,他回來了。
許恩棠從他的表里看不出什麼,還是平時那副樣子。
談霽禮坐下后坦然地迎上的視線,問:“我有沒有說這戒指是什麼時候買的?”
許恩棠有些招架不住他的坦然,想移開視線。
但想想斷片的又不是。
于是更坦然地看回去,點點頭說:“你說了,你畢業的時候。”
兩人就這麼對視了幾秒。
談霽禮的角勾起一個弧度,“哦”了一聲,說:“棠棠同學,所以你昨晚答應嫁給我了?”
“……”
這人怎麼不按常理出牌。
許恩棠否認:“沒有。”
談霽禮覆上搭在桌子上的手,撥弄了一下戒指。
這是證。
“戒指都戴了,你不能反悔了。”
**
經歷許多磕磕絆絆,許恩棠這一屆終于要畢業了。
大家恨不得抱頭痛哭。
畢業典禮這天,陸老爺子和談老爺子都來了。
陸老太太這兩年腳不如以前,出復園的次數減很多。
談霽禮當然也來了,一直在被談老爺子指揮著給他們拍照。
談霽禮和老爺子的兩年之約早已到期。
閾境智能做得有模有樣,這兩年一舉一都著業界關注,不就上科技板塊的頭條。
老爺子雖然不甘心,但也只能愿賭服輸,隨便他了。
能在這個行業布局也很好。
不過,再厲害的老板這會兒也得當拍照工,老爺子指揮。
談老爺子:“沒好呢,你再走近些給我們拍幾張。”
“別把眨眼拍進去,多拍點。”
“表不好要告訴我們。”
“記得把醫學院那幾個字拍進去。”
……
談霽禮一邊任勞任怨,一邊說:“我畢業的時候也不見您來。”
談老爺子很嫌棄他:“你跟棠棠能一樣嗎?你這混賬畢不了業都跟我們沒關系。”
談霽禮:“我畢不了業您可能最高興。”
老爺子輕哼。
許恩棠聽得想笑。
又拍了幾張,談霽禮把手機還回去,“這都拍了一百多張了,該到我了吧?”
談老爺子接過手機,說:“行吧,我們先看看,這一百多張要是拍得不好,你還得給我們重拍。”
談霽禮走到許恩棠邊。
許恩棠今天穿了紅黑的博士畢業服,垂布是白,帽子上垂下的紅流蘇隨著看向談霽禮,輕輕晃。
談老爺子把手機給陸老爺子,說:“你們陸爺爺拍照比我好,讓他給你們拍。”
陸老爺子一點也不謙虛,還讓他往旁邊讓讓。
陸老爺子舉起手機,看著鏡頭里的兩人,心中有一慨。
“準備了。”
許恩棠看向鏡頭。
陸老爺子拍了一張后,又說:“我跟你們多拍兩張。”
許恩棠點點頭。
陸老爺子拍了幾張后,看向邊,說:“棠棠,你往旁邊看看。”
許恩棠疑地轉過頭,看見談霽禮手中拿著戒指。
今天的太很好,戒指在自然的下反著極其耀眼的,但不如他眼睛里的那一片。
微風拂,吹過草木,和許恩棠的發。
談霽禮認真地說:“上次的太隨意,我再重新求一次。”
“棠棠,愿不愿意嫁給我?”
在兩位老爺子的見證下、在校園里,他再次認真地向求了婚。
許恩棠的心跳得很快,生出一種涌的滿脹。
朝談霽禮笑了笑,告訴他:“我愿意。”
“談霽禮,我愿意嫁給你。”
猜你喜歡
-
完結1070 章

奉子成婚:古少,求離婚(又名:離婚時愛你)
新婚夜,他給她一紙協議,“孩子出生後,便離婚。” 可為什麼孩子出生後,彆說離婚,連離床都不能……
171萬字8 365384 -
完結46 章

你如星辰不可及
蘇清下意識的拿手摸了一下微隆的小腹,她還沒來得及站穩就被人甩在了衣櫃上。後腦勺的疼痛,讓她悶哼了—聲。
4.2萬字8 18622 -
完結7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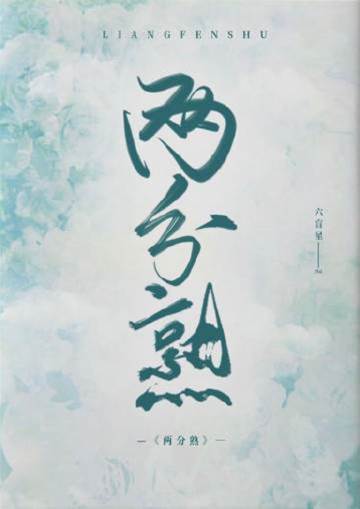
兩分熟
大學時,阮云喬一直覺得她和李硯只有兩分熟。學校里他是女粉萬千、拿獎無數的優秀學生,而她是風評奇差、天天跑劇組的浪蕩學渣。天差地別,毫無交集。那僅剩的兩分熟只在于——門一關、窗簾一拉,好學生像只惡犬要吞人的時候。…
25.3萬字8 6408 -
完結493 章
惡魔的寵愛
“以你的身材和技術,我認為隻值五毛錢,不過我沒零錢,不用找。”將一枚一塊的硬幣拍在床頭櫃上,喬錦挑釁地看著夜千塵。“好,很好!女人,很好!”夜千塵冷著臉,他夜千塵的第一次,竟然隻值五毛錢!再次見麵,他是高高在上的王,她是低到塵埃的花。一份價值兩億的契約,將她困在他身旁……
84.9萬字8 1497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