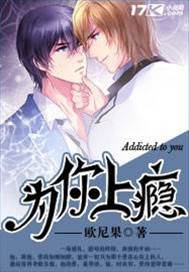《魔道祖師》 第93章 寤寐第二十 4
那家客棧一樓大堂裡之前還有一個客人,現在一個都沒有了。魏無羨和藍忘機邁了進去,揀了張桌子坐下,半天都沒人來招呼。魏無羨不得不用指節輕輕叩了叩桌面,喚道:“勞煩!”
夥計這才慢騰騰地過來。興許是長期倦怠慣了,有生意做也打不起神。魏無羨對著牆上的菜牌點了幾個菜,他仍是一副理不理的模樣。藍忘機拿起茶杯看了一眼,杯底還不如那家小客棧洗的乾淨,又默默放下,不再去桌上的任何東西。
點完了菜,魏無羨道:“請問你們這二樓是做什麼用的?”
夥計耷拉著眼皮道:“門外寫著了。一樓酒食,二樓住宿。你不識字?”
魏無羨隨口道:“你說對了,我真的不識字。那怎麼鎖住了?”
夥計不耐煩地道:“住住不住不住,問那麼多幹啥。”
藍忘機道:“住。”
他一開口,那夥計像是吞了塊冰,登時一個哆嗦。
藍忘機又了一錠銀子在桌上,冷聲道:“要一間房。”
魏無羨忙道:“別呀,咱們不住。收起來收起來!”
他說著去那銀子,卻不小心到了藍忘機的手,兩人同時一。藍忘機垂下手,袖子掩住了手指,見狀魏無羨一顆心往下一,那銀子掉到地上,夥計立刻撿起來,道:“房間不退!”
他收了錢,上樓開鎖,清掃走廊和房間去了。魏無羨調整了下表,狀似無事地道:“何必?”
藍忘機道:“待會兒總是要上去的。”
魏無羨道:“是要上去的。不過我們可以從窗戶走,從屋檐走,又不一定非要從這扇門走。<>省著點花吧,不是我的錢我都替你心疼。”
Advertisement
這時,點的菜也上來了。因爲客人只有他們兩個,上的才快。魏無羨夾起盤中一條青菜,聞了聞,竟然真的聞到了一令人作嘔的焦糊味。他對藍忘機笑道:“我算是知道了。本來就在鬧兇,房不能住,菜不能聞,夥計還跟吃了炮仗似的。這樣生意也能好纔是天理難容。你怎麼看?”
一談正事,兩人立刻自然起來。藍忘機道:“大火。”
魏無羨道:“還有?”
藍忘機道:“煙花之地。”
據那老闆娘所說,行老闆一家經歷的異象是房子裡到都能看到赤|著抱作一團的人,什麼地方會是這樣的?煙花之地。後來住進客棧的人晚上會做房子著火、焦翻滾的噩夢,說明這個地方曾起過一場大火,燒死了不人。
活活燒死,是極爲痛苦的一種死法,因此,時隔多年仍留著一部分死者的殘魂在影響此地。那老闆娘是八年前搬來這座城的,來時首飾鋪子老闆棄店離去,然而並沒提到這場大火。這火起的要更早,恐怕還遠在首飾鋪子開張之前,至有十幾年了。
這都是顯而易見的事。魏無羨道:“所見略同。還有,不是煙花之地,還是個風雅的煙花之地,一樓大廳裡總是有人彈琴,彈得還相當好。二樓用來,嗯,辦事,所以行老闆一家看到的摟抱人影都在上層。”
藍忘機道:“猜測。仍需驗證。”
魏無羨道:“那是。不過找誰驗證?那老闆娘八年前就來了,尚且不知道大火的事,否則肯定一腦全說了。問這夥計也肯定是不行的。”
正在這時,一個彎腰的人影邁進客棧來。隨眼一看,又是白天那名布衫老者,魏無羨心道:“這人還真捧這客棧的場。”
Advertisement
誰知,那名夥計並不領,一見他進來,翻了個白眼。<>
藍忘機道:“他。”
魏無羨也隨即想到了,這名老者年紀夠大,若是本地人,必然知之甚多,多半能問出點什麼來。
那布衫老頭在附近一張桌子上坐了,道:“要一壺茶。”
因爲魏無羨和藍忘機要了二樓的房間,夥計剛纔開了鎖,臨時匆匆打掃了一番,剛做完事,滿心不快,假裝沒聽到。那老者又道:“要一壺茶。”
夥計道:“沒有茶。”
那老者慍道:“怎麼沒有?”
夥計譏笑道:“沒有就是沒有。每次都要一壺茶坐著喝一整天,我們這兒的花生米不要錢很好吃是吧!”
那布衫老者正是因爲貪這個便宜纔來的,臉一陣紅一陣白,又怒又窘。魏無羨忙道:“這裡有這裡有,老人家您到這邊來,我們請你喝茶。”
那夥計瞅他們一眼,不敢再說什麼。布衫老者得了個臺階,立刻順著下了,坐到這邊桌上,嘆氣不止,謝他們。魏無羨搭訕套話的本事嫺,往來幾句,很快打得熱絡,問到重點。那布衫老頭也拿起了筷子,全然不嫌棄菜裡的焦氣味,邊吃邊道:“我?我在這條街上都住了三十多年了,誰比我更悉這裡的事?”
魏無羨和藍忘機對視一眼,神都來了。他立刻道:“三十多年?那可真是夠久的。這間客棧都沒三十多年吧。聽說這裡開過首飾鋪子,開過行,這麼說您都見過了。”
布衫老頭道:“它最風的樣子我也見過哩。”他低聲音,道:“你們是不是要在這裡住?我告訴你們,別。之前二樓上了一把鎖你們看到了嗎?”
Advertisement
魏無羨也低聲音:“看到了。<>那到底怎麼回事?”
老頭道:“十幾年前,這個地方起過一場大火,燒死了不人。只怕是都還留在這兒呢。”
和他們的推測完全一致。
魏無羨道:“起火的是什麼地方?”
老頭道:“思詩軒。”
這名字乍一聽,還以爲是詩作對、詠雲賦月的風雅之地,怎料想是勾欄之所。魏無羨故意道:“思詩軒?書畫閣嗎?”
老頭道:“不是!是坊。原先不這個名字的,不過後來出了兩個大紅的姑娘,就用們的名字湊在一起,改了個新的名字。一個思思,一個孟詩,合起來就是‘思詩’。”
聽到這裡,藍魏二人都是目一凝。
魏無羨道:“孟詩?這名字像是有點耳。”
布衫老者道:“那是當然。孟詩當年在雲夢也是紅過幾年的,彈琴寫字畫畫,還會作點詩,衝名聲來的人多得很,有些管做‘煙花才’。”
果然!
金瑤是雲夢人,他是在自己母親死後才北上投奔金善去的,之前隨母姓,姓孟。雖然經過金瑤刻意的磨滅痕跡,大多數人都不清楚那位煙花才的全名,但一聽到姓孟,就有所懷疑了。沒想到竟然真是!
布衫老頭說完,看了看魏無羨,又搖頭道:“不對,也不像。孟詩紅都是二十幾年前的事了,也沒紅得出雲夢去,現在也沒什麼人記得了。你年紀不大,應該不知道。”
魏無羨信口胡謅道:“我知道。我有個伯父,當年仰慕過孟詩姑娘,如癡如醉,天天跟我們講的事。後來嫁了人,那伯父喝得大醉,那一個傷心。”
Advertisement
布衫老者果然上鉤,道:“誰說嫁了人?”
魏無羨道:“沒有嗎?那我怎麼聽我伯父說連兒子都生了?”
布衫老者道:“倒是想嫁,遇到那個男的的時候都二十多歲了,年紀不小了,再過幾年肯定就不紅了,所以才拼著被責罵也非要生個兒子,不就是想。可那也得男的肯要。”
魏無羨道:“怎麼,那男的連兒子都不要?”
布衫老者把一盤菜都吃完了,道:“我聽說那男的是個修仙世家的大人,家裡肯定有不兒子。什麼東西多了都不稀罕的,怎麼會留心外頭的這個?孟詩盼來盼去盼不到人來接他,只好自己養了。”
和莫玄羽的母親莫二娘子如出一轍的想法、如出一轍的命運。天底下有多子都把希寄託在兒子上,指母憑子貴。與其嘔心瀝花那諸般心思,還不如多關注自己。然而魏無羨想不明白,縱使金善不願意把孟詩帶回金麟臺,但給一個煙花子贖,給一筆錢養兒,對他而言是很容易的事。爲什麼連這舉手之勞都不肯做?
他道:“嗯,那倒也是。這孩子聰明麼?”
布衫老頭道:“這麼說吧。我活了這五十幾年,還沒見過比小孟更聰明伶俐的孩子。孟詩也是有心教好他,把兒子當富貴人家的公子養,教他讀書寫字,什麼禮儀,送他上學,還到買一些劍譜啊笈啊給他看。大概還是不死心吧。”
如此說來,他們現在之所,前就是當年金瑤長大的地方。
布衫老者接著道:“小孟十一二歲的時候,孟詩還想效仿一個什麼典故,給他換個地方住,好好學。但是賣契還在思詩軒,就只把小孟送到書館裡住。但後來小孟又自己回來了,說什麼都不肯再去了。”"";"/;"/"/"
猜你喜歡
-
完結309 章
香火店小老板
一、 夏孤寒被家族除名的那一年,和一只老鬼缔结了同生共死契约。 老鬼长得帅,身材好,武力值爆表。 看着哪哪儿都好。 就是总喂不饱。 二、 夏孤寒的香火店开在鬼门关边上。 平日里生意惨淡,直到他意外爆红之后,门可罗雀的香火店客似云来。 总是对着镜子自说自话的当红小生; 半夜总会听到敲门声和啃食声的豪门贵妇; 把眼珠子当玻璃珠玩的红衣女孩…… 夏孤寒:我并不需要这些客人,谢谢!
73萬字8 14804 -
完結21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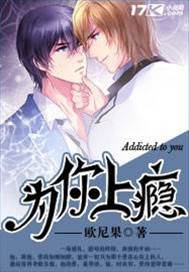
為你上癮
一場婚禮,游戲的終結,真情的開始。 他,林浩,愛的如癡如醉,放棄一切只為那個愛在心尖上的人,最后落得身敗名裂!他的愛,是笑話。 他,時炎羽,愛的若即若離,利用他人只為完成自己的心愿,最后痛的撕心裂肺,他的愛,是自作多情。 沒人能說,他們兩的愛能走到哪一步,錯誤的開端終將分叉,再次結合,又會碰撞出怎樣的火花?
54.2萬字8 694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