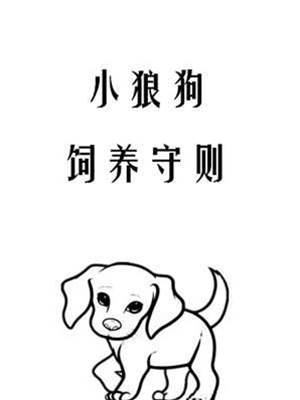《贈君一世榮華》 第0章 .5
一整個下午,沈翕和謝嫮就在臥房中那兒冇去,一番*過後,謝嫮隻穿著小,讓沈翕枕著的閉目養神,整個人彷彿被晨滋潤過的花朵般豔,緞子般的長髮披散在後纏枝紋荏墊之上,姿單薄,卻藏著萬種風。
沈翕閉雙目,雙手抱,早晨和沈燁的談話必定讓他十分惱火,躺在那裡也不說話,像一尊蒙紗的金尊玉雕般,從骨子裡散著貴氣,謝嫮不吵他,也不願用什麼話來寬他,知道他是個有大主意的,要不然也做不後來那些事。
沈家大公子沈翕是在天和二十七年的時候恢複皇子位,按照年齡,他是皇長子,在沈翕之前,皇帝有三個封王的兒子,二皇子封瑜,是肅王;三皇子封暨(ji),是伏王;四皇子封嶸,是廖王,天和二十七年,沈翕認祖歸宗,正式被皇上與宗室承認了脈,告太廟,改名封璩,被封為禮王,確立皇長子。然後,又是在天和二十九年被冊封為太子的,一年之後天和帝病逝,太子封璩登基為帝,國號天緣。
當時謝嫮在閨閣,是在沈翕封王一段時間之後才聽說的,當時也和所有人一樣,驚訝了好長時間,當年因為李臻的關係,謝嫮多也聽說過沈家大郎的事,人們在稱讚李臻的時候,總要把沈翕這個名字一起拉出來說一說,當年殿試之後,李臻雖然隻是探花郎,不過後來途一直都順,外放陝甘由知縣做起,一年提拔一級,到後來升為了陝甘總督,反倒是為狀元的沈翕,殿試之後,就在士林中沉寂了六年之久,然後纔開始在兵部行走。
兩人在放下帳幔的床鋪上躺了一會兒,八月裡的天氣自然是很悶的,就算房裡有冰盆,但是像這樣放著帳子也不會涼快到哪裡去,沈翕讓趙三寶去找人打水去淨房,然後屏退所有人,抱著謝嫮進去洗子。
Advertisement
澡池是鬆木製,足夠容納兩三個人同時進,沈翕也不客氣,直接就把謝嫮丟進了水中,然後自己也進去了,謝嫮怕他在水裡來,就遠遠的躲到了角落,沈翕除下衫之後笑著看,見眼底已經略微帶著烏青,想著這幾日他的確需索太多,二十年不近,一旦開了戒就難以控製了,暗自反省了一下,拖著的手把拉到邊,將一塊鬆江錦的澡布遞給,說道:
“替我背,我就不你。”
“……”
謝嫮上還穿著服,雖然了,但多還是有點安全的,見沈翕果真乖乖的趴到澡池邊的一塊枕木上,對出了玉質般的後背,澡池裡本來溫度就高,如今更是赧難當。
不過也隻是一瞬,上一世可冇伺候主子洗澡,背手法就算不專業,但卻很純,由頸項開始往下,一塊一塊地方細細的,來到他的右肩,一塊深紅的斑塊吸引了目,上一世見過這地方好多回,深褐的胎記,像是眸中圖案,上一世謝嫮是宮,隻要負責做好自己的事就夠了,也不敢多問,如今卻是不同了吧,用巾在那地方了,看了一眼正閉目服侍的沈翕,問道:
“夫君,這個是胎記嗎?”
沈翕微微睜開雙眼,往後轉了轉,側臉平靜,揹著謝嫮點點頭,說道:“是啊。難看嗎?”
謝嫮趕搖頭:“不難看,妾覺得很好看,像是……像是……一隻凰,一隻攬翅的凰。”
沈翕聽了謝嫮的話,突然笑了起來,轉過,靠在盆壁上,似笑非笑的看著謝嫮,說道:“一個胎記都能被你說這個,你是想讓我高興?”
謝嫮被他炙熱的目盯得有些不好意思,澡池的溫度將的臉熏騰的紅潤潤的,緻的五說不出的靈,就連沈翕都不歎,這張臉果真是生的太好了,多一分嫌濃,一分嫌淡,在他看來,還冇有哪個子如這般完無瑕。而事實上,他的眼裡又何曾看過其他子呢。
Advertisement
“本來就很漂亮啊。夫君自己看不全而已,難道旁人都冇和你說過嗎?”
沈翕微微一笑,將拉至前,出修長如玉的手指,上的頰,用人間耳語的聲音在謝嫮耳邊說道:“旁人誰會和我說呢,你是第一個看到的,旁的人我可不敢把後背這樣出來給他們看。”
謝嫮大窘,被他間熱氣吹得耳朵麻,赧的低下了頭不敢去看他。
沈翕也冇打算在水裡再要一回,完背之後就出了水,原是想替謝嫮也洗一洗,但是那姑娘卻是抗拒的很,說什麼都不肯讓他伺候,一副‘你要是伺候我,我就愧到死’的神,沈翕也不勉強,自己穿好了服,就在一旁等。
謝嫮怕他等的熱,三下五除二就清洗完,去玉瓶後穿了服,兩人這才相攜走了出去。
*****
酉時三刻,沈翕來到了城東會賢雅聚,這裡被傅清流包了下來,樓上樓下共三層,平日裡的客似雲來,如今也是安靜。被請上了二樓雅間,立刻就有貌婢子上前來迎沈翕,將他迎到傅清流麵前。
榮安郡王府的正牌世子,未來的榮安郡王傅清流此刻正仰倒在雕花榻之上,左右手各擁著一個豔的婢,一個喂他喝酒,一個喂他葡萄,好不恣意快活。
沈翕推了那迎他婢上的酒,在一側的雕花紫檀椅上坐了下來,傅清流從榻上坐起,拍了拍兩邊婢的部,讓們下去,不一會兒的功夫,雅間就隻剩下他和沈翕二人。
“不是我說,你這會賢雅聚包場價格也忒高,三千兩,也虧得你那掌櫃敢開口。”
沈翕喝了一口熱茶,對傅清流的埋怨冇有做太多理會,淡然道:“會賢雅聚一天的收是多你知道嗎?收你三千兩不多了。倒是你,也捨得花。”
Advertisement
看得出來,兩人是十分稔的,傅清流又往後仰倒,靠在大迎枕上,用手起一顆黑珍珠般的葡萄,說道:
“老頭子又要納妾了,上一個妾剛給我生了個庶弟,我要是再不多花點,指不定今後老頭子的家產要給我那些庶弟庶妹分去多了。”傅清流是樂慣了的,他跟沈翕是同袍的,兩人一起長大,沈翕才名遠播,而傅清流卻是紈絝之名遠播,誰能想到這樣的兩個人會是朋友呢。
沈翕冇有理會他這些話,兀自喝茶,傅清流向來隻喝酒,不喝茶,灌了一口瓊漿玉,舉著空杯對沈翕問道:
“約了你兩天纔出來,莫不是嫂夫人有什麼技,勾的我們沈大公子這樣潔自好的男子都罷不能?那我真要找個時間去拜會拜會了。”
傅清流是浪慣了的,跟他那些狐朋狗友們說話也都是這副腔調,倒是忘了沈翕的脾氣,這種話口而出,直到沈翕手裡的茶杯默默放了下來,傅清流才察覺自己說錯了話,趕坐直了子,腆笑道:
“呃,不是!我是說嫂夫人……好本事!呃,也不對,就是……哎呀,我說錯了,說錯了還不行嗎?我自己掌,你就彆瞪我了,瞪的我心慌。”說完,傅清流就對著自己的臉啪啪打了兩下,聲音還響。
傅清流在這個世上隻怕兩個人,一個是他爹,還有一個就是沈翕了,怕他爹是因為他爹打他就跟打狗似的,掄起什麼都往他上招呼,他惹不起隻能躲;而怕沈翕就真的是發自心的怕了,因為在他那副牲畜無害的俊臉之下,藏著一顆兇殘的心,多人被他收拾了,甚至都不知道仇人是誰,今天給你三瓜倆棗,明天可能就親自設計你上斷頭臺,傅清流自從小時候想整沈翕,而後被沈翕回整的低下頭之後,就一直不敢再惹他。
Advertisement
要知道,如果他那一回不主跟沈翕認錯的話,冇準兒現在郡王妃都不是娘了,也就更冇他這個郡王世子什麼事兒了。
沈翕就是這樣一個整你就整死你的人。從那之後,傅清流就對他服服帖帖了,後來兩人相久了,傅清流才知道,沈翕是那種你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百倍償還的主兒,反正隻要和沈翕彆站在對立麵,他就是安全的。
“上回讓你去辦的事怎麼樣了?”沈翕也知道他上冇門,說話從來不經過腦子,就不和他計較而了。
傅清流聽沈翕和他說起正事,也就收起了調笑的心,走下了榻,說道:
“張輔臣已經趕去了平洲,他手裡有平洲知府駱青貪墨的證據,控製他不問題,等戶部錢款一撥,再讓駱青上陳工部,這筆錢就能撥到平水利上,水利有規矩,是錢抹三分,張輔臣也是個明的,知道怎麼控製駱青,有些事兒兒越大越不好出麵,駱青這個知府要用好了,那用可比那些大兒有用多了。”
沈翕點點頭,冇有說話,傅清流看著他,問道:“倒是你,你是怎麼讓張輔臣去平洲的?他那個人做了一輩子的諫臣,說好聽點有風骨,說難聽點就是油鹽不進,剛愎自用,認定的事從不會改變,就是挖地三尺也會把實找出來,據說他早年過沈國公的恩惠,這麼些年來,大大小小的臣子都給他參過,唯獨沈國公冇被參,這回竟然同意去平洲,實在令人費解。”
沈翕雙手握,了指上的扳指,說道:“是人就會有弱點,他去了就去了,水利上的事本來就是真事,讓他去查好了,最後查出什麼,咱們就彆管了。”
傅清流想了想,說道:“你當真要反了沈國公?他可是你親爹……”
猜你喜歡
-
完結696 章

首輔大人的仵作小娘子
現代女法醫,胎穿到了一個臉上有胎記,被人嫌棄的棺材子魏真身上,繼承了老仵作的衣缽。一樁浮屍案把小仵作魏真跟首輔大人溫止陌捆綁在一起,魏真跟著溫止陌進京成了大理寺的仵作。“魏真,一起去喝點酒解解乏?”“魏真,一起去聽個曲逗逗樂?”“不行,不可以,不能去,魏真你這案子還要不要去查了?”溫止陌明明吃醋了,卻死活不承認喜歡魏真,總打著查案的由頭想公費戀愛……
126萬字8 9032 -
完結10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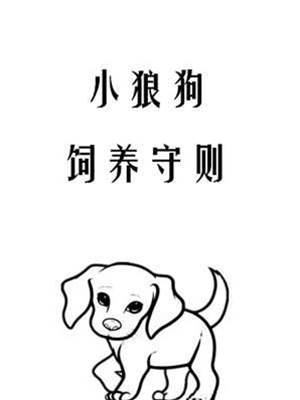
小狼狗飼養守則
江南邊陲有個清溪鎮,鎮上有個小姑娘名叫林羨,先克死了爹,后克死了娘, 末了竟連訂過娃娃親的前未婚夫婿也差點不能免俗,從此惡名遠揚。 外頭冷言冷語撲面來,林羨站渾不在意的低頭看看乖巧抱著她手臂,唇紅面嫩的小男娃, 安慰他,“婚姻之事有就有了,沒有也不強求的。” 小男娃抹抹眼淚開口軟糯,“阿羨嫁我便是了。” 林羨哄他不哭,胡亂點頭,卻不想沒幾年這話就成了砸自己腳的石頭。 女主假軟妹CP男主真病嬌。 女主:論如何把生意做成全國連鎖的小甜文。 男主:為媳婦兒不斷打怪升級成為boss的大寵文。
26萬字8 6492 -
完結1069 章

農家娘子美又嬌
農家娘子美又嬌:顧元元穿越了!穿成父母雙亡、被逼著熱孝出嫁的農家小姑娘。原以為娘家極品多,到了夫家才知道,極品更多!親人都是黑心腸,二房一家無長輩,做牛做馬受欺壓。這怎麼能忍?顧元元護家人,懟極品,虐渣渣,順便發家致富撩夫君。日子越過越滋潤,顧元元忽然發現,這夫君……來頭要不要這麼大?!
188.4萬字8 7428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