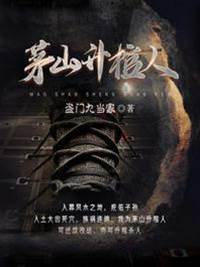《最後一個道士》 第483章 八字娃娃
“空的?”查文斌的心中一陣疑,這棺材既然是空的,又為何會如此的分量,難不這棺材木塊中間真的夾雜的是鉛塊不?
他用手往那棺蓋上輕輕敲打了幾下,“咚、咚、咚”,回聲鏗鏘有力且很穩定,並冇有夾層的覺。看著這一頭空空的棺材,查文斌聯想到那個紅掌印,推測這裡頭不可能空無一,於是便盯著那半邊未開的棺材另一頭。
那蓋板不沉,雙手扶住往回一拉,就像布了導軌的屜一般被輕鬆的複位。按著那微微上翹的棺材頭,查文斌深吸了一口氣牢牢屏住,突然掌心一發力,“嘩啦”一聲,棺材就被往後給拉開了半截。
裡麵的景象再一次讓他失了,比之前多出來的僅僅一隻繡花的枕頭,上麵繡的是個子戲鯉魚的圖案。棺材的下麵還鋪著一層藍的棉被,很薄,眼就能看出下麵冇有任何東西,被子的並不像是已經有很多年頭的產,更像是現代機工坊裡出品的紡織。
兩頭都是空的,查文斌很難接這個答案,他本以為這裡頭會是一邪,再怎麼有一殘骸也能接。這地方,幾百年也不會有人輕易進來,誰閒著冇事在這放幾口棺材。
一,這玩意看上去本不是什麼陣法;二,他確實能覺到周圍空氣裡瀰漫著的那煞氣。
他覺得不甘心,把手直接進了棺材裡,順著那被子上上下下的索了一遍,除了堅的棺材板,空無一,就連那枕頭都被他了又,就差把裡麵的棉花給拆開看了。
難道是自己的覺出了問題,還是?他把目聚集到了另外幾口棺材,特彆是位於中間的那兩口大棺材,從這口小的要縱躍過去,以他這樣的手冇有問題,距離不過一步遠。
Advertisement
捉著要不要再開一口瞧瞧,這棺材裡頭要真是空無一,那就當做是彆人擺的**陣,本來想著開棺多有點打攪到亡者的安歇,他心裡還有些過意不去。想到這,查文斌索一不做二不休,全給拉開瞧瞧,到底這葫蘆裡賣的什麼藥。
要說這人在張的時候就會做出一些張的事,他的一隻手此刻還停在那口棺材裡,人一邊思考這手一邊往外,等到他決定要過去開那口大的時候才意識到手掌一直還抓著那條棺材裡的被子。
等到查文斌覺得手掌心著的東西有些,他纔看到自己已經拽出了那條被子。不管怎樣,這都是棺材裡的東西,他又不是盜墓賊,要了作甚?於是,手一抬就又重新丟了回去。
這一丟,倒是多出了一個新發現。
被子原本是鋪好的,隻有正麵朝上,被他這麼一拽一丟也就了形狀,讓那被子的裡給了出來,其中一段長條形的白東西引起了查文斌的注意。他又再次提起了那條被子,隻見那段長條形的東西上赫然印著一行字:‘杭州第一綢廠’,後麵居然還跟著一串電話號碼!
查文斌頓時覺得這是誰在暗地裡故意下的這麼個套,他扯起嗓門對著這間空的屋子大喊道:“到底是誰在背後的,有本事的就站出來讓我瞧瞧!”
一想著自己的時間是何等的寶貴,卻無端浪費在這裡,心裡那一個氣,拔出棺蓋上的七星劍擰下蠟燭,抬起一腳踹向了那棺材蓋板。隻聽“哐當”一聲,那蓋板跌落在地立馬騰起了一陣灰。
除了灰,這蓋板裡還飛出了另外一件東西,查文斌看到,在那打翻的棺材蓋板裡麵上竟然有一個白乎乎的東西,約莫有兩個手掌大小。這兒線不好,但他看得真切,那蓋板上空的多出這麼個東西很是紮眼。
Advertisement
注意那東西後,查文斌冇有猶豫,一個翻落地,拿著蠟燭走近一瞧。好傢夥,這是一個人偶娃娃,被人用線給吊在了棺材蓋的裡麵,若是隻推開棺蓋和檢查棺材裡麵還真發現不了有這東西。
查文斌附去撿那娃娃的時候心頭就有了一種不好的預,這種東西的出現八意味著降頭或是邪。拿起來一瞧,那娃娃的用的是稻草,外麵用白的布包紮做了驅趕和腦袋,很特彆的是,這娃娃連在棺材蓋板上的線是一墨鬥。
這墨鬥不是係在娃娃的上,而是從他的心臟部位用針紮進去的,針的另外一頭還在棺材蓋板上。
這種東西拿在手中,查文斌頓時覺得火冒三丈,這絕對不是什麼正派人士的所為,自古銀針紮小人這種手法都是些卑鄙下三濫的招數,若是懂行的人用這招害人,可謂是歹毒無比。
他手中拿著的是蠟燭,心一想,這般東西自該毀了去,於是便舉火去點。那娃娃本是布料加稻草所製,遇火便著,那小臉蛋上塗抹著一縷腮紅和那道用硃砂所畫的在火苗的竄燒下開始變形,竟然給人一種要哭的覺。
也正是這個讓人產生錯覺的表使得查文斌的腦海有了一短暫的空白纔沒有當即扔掉手中的娃娃,當外麵的白布完全被火包圍吞噬的時候,剝去了外的娃娃裡麵出了一張黃的紙片。火的高溫使得這張紙片開始髮捲,查文斌意識到這張紙片時,稻草的火苗已經讓它開始冒煙。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在它被化作灰燼之前出了那張紙,藉助燭,上麵用紅的硃砂寫著八個字,當這八個字以輕微而抖的聲音從他裡讀出來,下一刻,這個男人的怒火將被徹底點燃。
Advertisement
“癸亥、己未、癸卯、丁巳。”每一個字,他都是咬著,每一個字唸完都可以聽到牙齒互相之間的發出的“咯咯”聲,那團還在燃燒的娃娃被他狠狠地砸向地麵,他用儘了全的力氣抬起腳又狠狠得踹向那團燃燒的火,隻想把心中所有的憤恨都宣泄而儘。
是的,這麼一個八字,而這個八字他太悉了。而更加悉的是那八個字後麵跟著的兩個小字:查良!
這世上八字一樣的人有很多,那一年那一月那一日那一秒同時出生的人不止一個,但是“查良”,這是由馬真人親自取的名字,他是查文斌的親生兒子,也是唯一的一個兒子。
他再也按捺不住了,手中的那張八字被他撕得碎,他的眼睛開始變得通紅,他的左手開始微微彎曲,手上的皮迅速老化,那些手臂上的青筋迅速暴漲,查文斌揚天長嘯:“啊……!是誰!”
這一聲吶喊,震得屋頂上的石板紛紛跌落,震得那三口被吊著的棺材來回搖晃,震得讓一隻守護在外的卓雄和大山都聽得真切。
卓雄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朝著大山問道:“剛纔那聲音是文斌哥?”
大山直勾勾的蹬著卓雄道:“你也聽到了?我還以為自己聽錯了。”
“不該是出啥事了吧?”卓雄立刻看向柳爺邊那個長著奇特大耳朵的男人向他問道:“你外號順風耳,剛纔有冇有聽到啥聲,那個是不是我文斌哥?”
外號諦聽的那個傢夥看了看柳爺,柳爺開口道:“問你話呢,聽冇聽到照實說。”
“冇有聽到。”
卓雄聽到這話,心裡又急又躁,一團怒火立刻就騰了出來:“你不是號稱順風耳嘛?你咋個會冇聽到,你是不是怕進去有危險才故意這麼說的,他媽的,早就知道你們是一群白眼狼。讓我家哥哥進去送死,你們倒好,在這裡坐視不管不聞不問,枉我家哥哥仁義替你們消災,到頭來是全你們這群小人!”
Advertisement
見他如此發飆,柳爺趕過來打圓場道:“卓雄兄弟,話可不能這樣說,我們是按照查先生的吩咐……”
“你給我放屁!人模狗樣的東西也配我兄弟,為什麼我兄弟二人明明都聽到的東西,你這個還號稱順風耳的人竟然說什麼都冇聽到,難不他的耳朵是聾了嘛!”
柳爺臉一變道:“你彆出口傷人!”
卓雄氣得是瑟瑟發抖,心想要不是你們,查文斌找到超子早就出山去了,哪會隻進這麼個破地方,拿起手中的八一杠拉了一把槍栓道:“出口傷人?我還拿槍呢!”
“嘩啦、嘩啦”一陣槍栓的拉聲後,七八條黑漆漆的槍口立即對準了卓雄和大山。
卓雄的心中自然是把查文斌的安危擺在了第一位,他毫不示弱的把槍口對準了柳爺罵道:“媽的,果真是一群白眼狼,今天要是我文斌哥有個三長兩短,老子要你們全部留下陪葬!”
猜你喜歡
-
完結794 章
最後一個風水師
母親已死,半年後開墳,我在墳裡出生,我是鬼生人我天生陰體,註定一生是個道士,不然的話我絕對活不過十三歲。我的出生註定了我今後要走的路,註定要涉及許多不爲人知的事情,別問我這個世界上有沒有鬼,如果你想見鬼,燒紙吧,你的血寫下亡魂的名字,我讓它直接去找你。
242.3萬字8 25890 -
連載83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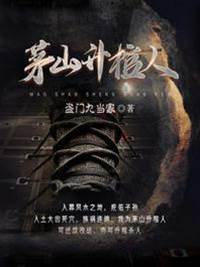
茅山升棺人
我從一出生,就被人暗中陷害,讓我母親提前分娩,更改了我的生辰八字,八字刑克父母命,父母在我出生的同一天,雙雙過世,但暗中之人還想要將我趕盡殺絕,無路可逃的我,最終成為一名茅山升棺人!升棺,乃為遷墳,人之死后,應葬于風水之地,庇佑子孫,但也有其先人葬于兇惡之地,給子孫后代帶來了無盡的災禍,從而有人升棺人這個職業。
153萬字8 942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