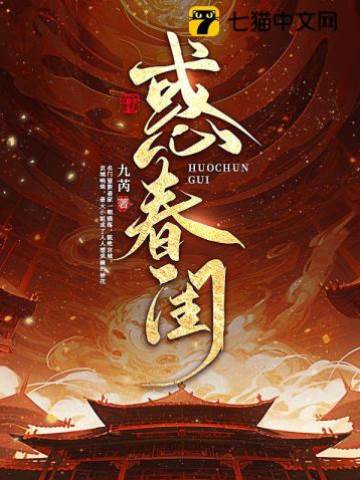《他定有過人之處》 第二十一章
幾日過去,大風又吹了好幾番。
秋輾轉,自窗外一直照到桌案上,裡,幾頁信紙正攤開著。
神容端坐案後,剛看完信,拿著筆寫了一番客套話,停下後又看了看信紙。
裴二表哥的信拖了好幾日,直到現在才終於看了。
紫瑞在旁邊為研墨,看到握筆的手背上有一點紅印,問道“主的手怎麼了?”
神容聽到這話,翻過手背看了一眼。
一雙手細白,被山宗抓過後難免就留了這點痕跡,居然好幾日了還未褪掉,不想竟被看見了。
紫瑞不知,還有點擔心“莫不是不慎磕到了,可要取藥來?”
“不必,又不疼。”
沒什麼覺,記得那男人當時沒用太大力,但就是製著不了。
人壞,招也多。暗暗想完,了一下手背,繼續回信。
裴家二郎這封信寫得長,卻也沒什麼實際的事。無非是保重,好好休養,若有可能,再給他描述一下驪山盛景就最好了。
神容托腮,想嘆氣,驪山山脈地風倒是瞭如指掌,但景還真不曾細看過,哪次山是去看風景的,分明都是有事才會去的。
偏偏哥哥還裝得像點,這要如何裝?本就不在驪山。憑空造,隻怕反而人生疑。
抬頭問紫瑞“驪山風你可還記得?”
紫瑞皺著眉回答“奴婢哪裡注意過那些,都不曾記得有沒有去過了。”
神容乾脆擱下筆,起走出房門,去廊下把東來喚過來,將同樣的問題又問了他一遍。
東來垂頭站在跟前,也搖頭。
擰擰眉,忽聽廣源的聲音冒了出來“貴人,我倒是知道一些。”
他從東來後走出來,垂著兩手,邊想邊道“我記得驪山有一景緻頗佳,尤其是這時節的傍晚,夕一照,不勝收。”
Advertisement
神容見他知道,便問細了點“哪一?”
廣源一愣,繼而訕訕地笑“隔了太久了,那還真不記得了。”
“南片的斷崖上。”
忽來一道聲音,沉沉打斷了幾人。
神容循聲轉頭,前幾天纔在跟前耀武揚威的男人正從廊下走過來,刀夾在臂彎裡,馬靴踏地有聲。
廣源一喜,迎上前去“郎君來了。”
“嗯。”他停下腳步,看著神容“那一在南片的斷崖上,聽到了?”
神容淡淡看他“你去過?”
山宗笑“我哪裡沒去過?”
神容一想也就回味過來了,廣源會知道,肯定也是當初在山家時隨他去過。
那裡是皇家權貴才能去的地方。但當初先帝十分倚重他,山家又有地位,據說連山中溫泉的泉眼都賞過給山家用,那種貴族奢侈的地方,他會去過一點都不稀奇。
山宗也不近前,隔著幾步說“大白天的,人在幽州,想著驪山?”
神容微抬下頜“那又如何,我寫信要用便問了。”
山宗聽了也沒問寫給誰,就隻是笑笑。
忽然看他“你怎麼來了?”
總不可能是特地來告訴驪山景緻的。
山宗收斂了笑“我隻是經過,來知會你一聲,稍候就去山裡等我。”說完就又轉走了,腳步很快,看起來的確隻是經過。
廣源追去送他了。
神容便想了起來,應該是他那天說的時候到了,他說過到時候要去山裡等他。
山宗已徹底不見人影。
回到屋裡,坐去案後,照著他剛才說的寫了幾句,很快就停了筆“行了,這樣也差不多了,二表哥歷來好說話,敷衍些也沒事,就這麼回信吧。”
一旁紫瑞幫收信封,一邊附和“確實,奴婢就沒見過比裴二郎君更好說話的人了。”
說完屈了個,出門找人去送信了。
Advertisement
走了,神容便著手山,東來立即去準備。
也不知山宗這來去匆匆的到底是又去了哪裡,隻留了一小支人馬在舍外麵,剛好可以用來負責護送山。
神容繫上披風出門,帶著東來上路。
從城中一路馳馬而過,出城時,忽然瞥見一抹悉人影,馬速放慢了些。
對方也看到了,退在道旁向福了福。
是趙扶眉,一個人站在城門口,仍然穿著那日初見時的一素淡襦。
“真巧,在這裡遇到了貴人。”微微笑著說“我正好送老軍醫返鄉,人剛走。”
神容朝遠看了一眼,看到了馬車遠去的蹤影。
彼此還算不上絡,神容也不知該與說什麼,便點了個頭,時刻要走,也就沒下馬。
趙扶眉倒沒什麼離別緒,看起來很豁達的模樣。
站在馬下,仰頭看神容,忽然又笑起來“山使先前也是從這道門出去的,貴人這是又要去找他嗎?”
神容不看一眼,隻因覺出口氣裡那個“又”字有些古怪,彷彿不該去一樣。
隨即就笑了一笑,點頭“你說得對,我是要去找他。”
說完直接扯韁馳了出去,餘裡隻見趙扶眉又退讓了幾步。
趕到山裡時,竟然已經有人馬先到了。
從山口,到薊山而去,一路上都是兵甲齊整的兵卒。
神容下馬,走到山道上,看見還在養傷的胡十一居然也出現了,他和張威一左一右分列兩邊,今日全都一不茍地穿著甲冑,拿著兵,好像十分防範的模樣。
古怪地問“你們這是做什麼?”
張威道“頭兒吩咐的,咱們帶著軍所的銳來這裡守著。”
神容左右看了看,更覺周遭肅殺“軍所銳?難道他把盧龍軍都調來了?”
Advertisement
胡十一莫名其妙“什麼盧龍軍,咱們幽州軍。”
神容留心到他們的刀鞘上都鑄有篆的“幽州”二字,心想八是改名了,也沒什麼好奇怪的,國中兵馬大多以地名來命名。
隻是不知他們為何要搞這麼大陣仗,轉頭看了看,往薊山走去了。
山宗還沒來,果然是等他。
迎著山風,走到那發現紛子石的山眼,如今在這兒礦眼了。
往下看,隻看到黑乎乎的一片,那山石間似出現了細微的裂紋。
抬頭看看天,秋季到了末尾,這時候能開出來是最好的,再拖是真拖不下去了。
左右等了又等,天都暗了一分。
轉頭問“人還沒到?”
東來在另一頭站著“是。”
神容輕輕扯著手裡的馬鞭,在礦眼附近來回踱步。
直到又過去許久,都快懷疑那男人是不是在玩兒,終於聽到了靜。
一馬長嘶,山宗直奔而,躍下馬,朝這裡走來。
神容一路看著他到了跟前,他黑上不知從何沾了灰塵,擺掖在腰間,一手提刀,走時,長闊邁,步步生風。
看著他“我等了你快兩個時辰了。”
山宗竟還笑“那還不算久。”
神容掃過他肩頭和袖幾沾上的灰塵,又看看他那收的腰。
本是探尋,往下再看他胡裹著的兩條修長的,又覺得看的不是地方,轉開眼,抬手捋過耳邊發,會意地說“和那日我見你模樣差不多,料想你是去了上次一樣的地方。”
山宗不自覺看了看的眼睛。
神容眉眼出是出了名的,眼瞳黑亮,眼角微微帶挑,一顰一笑都著上獨有的氣韻。
他覺得這雙眼睛有時候實在過於厲害了點。
“沒錯。”他刀一收,說“我給你找人去了。”
Advertisement
神容一怔,又看那遠赫赫威嚴的兵卒“你給我找了什麼樣的人,需要這樣嚴?”
“你馬上就會看到了。”山宗轉,臉上沒了笑,隻餘肅然“帶上來。”
山林間傳出一陣陣奇怪的聲響,那是鎖鏈拖,掃過林間山石樹木的聲音。
兩列兵卒持刀,押著一群人緩慢地自山道上過來,遠看如同押著一條蜿蜒的黑蚰蜒,古怪又荒誕。
等到了近,才發現那群人渾都被黑布罩著,一個一個,足有幾十人,看形個個都是男子,如靜默。
神容莫名覺得這群人不是善類,轉過頭時聲音都低了一些“這是乾什麼?”
山宗看著那群人“他們太久沒見天日了,需要緩緩。”
忽然反應過來“你給我找的莫非是……”
“底牢的。”他直接說了,看著臉,像在看反應。
神容隻覺震驚“不是你我別起這些人的念頭麼?”
他笑了一下“那不是你說有我在,就能鎮住他們?”
的確說過。
山宗又看向那群人,一手按在刀上,就這麼看了許久,放話說“揭開。”
黑布接連揭去,被罩著的人紛紛暴在天下。
神容忽然後退了半步。
山宗偏頭,看到站在側,穿著胡的形更顯纖挑,一雙手的手指著馬鞭,眼睫微,朱飽滿,輕輕抿著。
他眼睛移開時不低聲說了句“不用怕。”
神容說“我沒有。”
沒怕,隻是從未見過這樣一群人罷了。
他定有過人之
猜你喜歡
-
完結521 章

一品女仵作
女法醫池時一朝穿越,成了仵作世家的九娘子。池時很滿意,管你哪一世,姑娘我隻想搞事業。 小王爺周羨我財貌雙全,你怎地不看我? 女仵作池時我隻聽亡者之苦,還冤者清白。想要眼神,公子何不先死上一死?
96.1萬字8.18 24943 -
完結132 章

國子監小食堂
孟桑胎穿,隨爹娘隱居在山林間,生活恣意快活。一朝來到長安尋找外祖父,奈何人沒找到,得先解決生計問題。陰差陽錯去到國子監,成了一位“平平無奇”小廚娘。國子監,可謂是天下學子向往的最高學府,什麼都好,就是膳食太難吃。菜淡、肉老、飯硬、湯苦,直吃…
66.7萬字8 17393 -
完結312 章

和離后,戰神王爺每天想破戒
穿越後,鳳卿九成了齊王府棄妃,原主上吊而死,渣男竟然要娶側妃,鳳卿九大鬧婚宴,踩着渣男賤女的臉提出和離。 渣男:想和離?誰會要你一個和離過的女子! 顧暮舟:九兒,別怕,本王這輩子認定你了! 鳳卿九:可我嫁過人! 顧暮舟:本王不在乎!這一生,本王只要你一個! 攜手顧暮舟,鳳卿九翻雲覆雨,憑藉自己高超的醫術,在京都名氣響亮,豔壓衆人。 渣男後悔,向她求愛。 渣男:以前都是我不對,過去的就讓他過去吧!我們重新開始好不好? 鳳卿九:不好意思,你長得太醜,我看不上! 渣男:我到底哪裏比不上他? 她冷冷地甩出一句話:家裏沒有鏡子,你總有尿吧!
55萬字8.18 124421 -
完結17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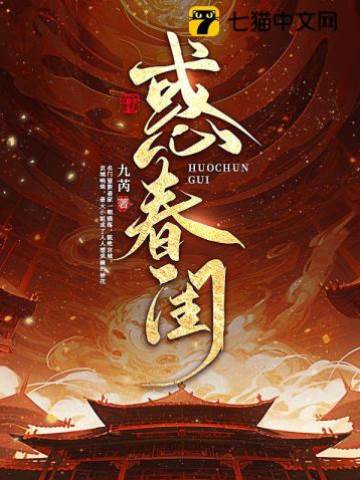
惑春閨
名門望族薑家一朝隕落,貌絕京城,京城明珠,薑大小姐成了人人想采摘的嬌花。麵對四麵楚歌,豺狼虎豹,薑梨滿果斷爬上了昔日未婚夫的馬車。退親的時候沒有想過,他會成為主宰的上位者,她卻淪為了掌中雀。以為他冷心無情是天生,直到看到他可以無條件對別人溫柔寵溺,薑梨滿才明白,他有溫情,隻是不再給她。既然再回去,那何必強求?薑梨滿心灰意冷打算離開,樓棄卻慌了……
31.5萬字8.18 857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