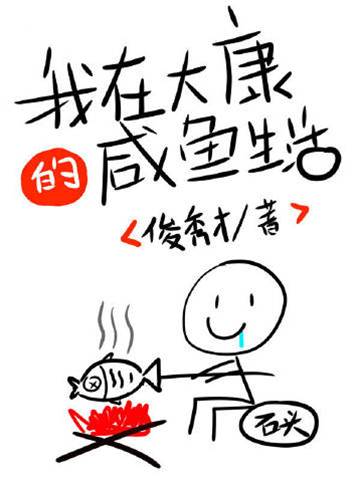《變臣》 第三章 窮則思變
「慘了,這娃兒被雷劈傻了,連雨都不知道躲。」
「還不如直接被雷劈死呢,江寡婦得養他一輩子,這家算是毀了。」
「快來看傻子,哈哈。」
大雨如注,雷聲隆隆,鄉人站在簷下,指點著雨中的江安義。話語斷斷續續續地隨風飄耳中,江安義忿悶異常,自小遵從聖人教誨,行事溫文爾雅,與人相和善,可是,都是鄉裡鄉親,何苦出言如此惡毒。
年喪父、慘遭雷劫、債主上門,一件件遭遇讓江安義滿腔氣苦無發泄,真恨不得一道閃電將自己化為灰燼,連同那些心懷惡意的人。
「哥、哥……」瘦小的子在狂風中艱難地行進,呼聲被風雨扯得零零落落,一聲聲「哥」聽在耳中分外親切。江安勇披著蓑、戴著鬥笠深一淺一地跑來。
跑到近前,江安勇著氣解開蓑,踮起腳尖往哥哥上披,「哥,呼呼……娘怕你淋壞了,……讓我來接你,呼呼,快回吧,上都了,別著涼。」
蓑帶著溫,驅散著江安義心頭的寒冷。一陣斜風吹來,江安勇上的褐布短衫被打了一片,江安義忙道:「我反正都了,你別也淋了。」
江安勇「嘻嘻」地笑道:「我子壯,這雨就像洗個澡,不礙事。哥你是讀書人,別淋壞了。」
江安義心頭一熱,眼睛變得又酸又,急忙仰起臉,讓雨水滴打在臉上,溫熱的覺順著臉落。不容分說將蓑扯過一半蓋在弟弟上,江安義舉著鬥笠擋在前麵,兄弟倆依偎在一起,蹣跚地向家跑去。
江黃氏站在門前焦急地張,看到冒雨跑回的兒子,嗔怪地招呼道:「快進屋換上乾服,小心涼。」
江安義下笨重的蓑,連同鬥笠一起掛在簷下的木鉤上,雨水滴落在簷前破碎的石階上,滲土中不見。妍兒抱著幾件服等在旁邊,板著小臉,老氣橫秋地教訓江安義:「哥,你這麼大了怎麼也像二哥一樣不懂事,著了涼娘又要心疼了。」
Advertisement
幾滴雨水濺在妍兒的小臉上,仰著的麵容有如花開帶,江安義疼惜地替拭去臉上的雨滴。
換過服,江黃氏將江安義到邊,道:「娘想過了,既然你說了年底前還債,娘不能讓你失信,就賣田吧。」
江安義知道大鄭朝採用均田製,男丁年後能分到二十畝田,允許田地買賣,鼓勵開墾荒地。但立國百餘年來,人口增長了五倍,土地兼併十分嚴重,府多以荒地當田,稅賦照征。
父親死後家中沒有年的男丁,二十畝田被收回,現在家中的十畝地是幾代人省吃儉用購置的,這十畝地就是孃的命,賣了田,一家人怎麼活,江安義嚇得呆住了。
江黃氏語氣堅定起來:「欠債還錢天經地義,當初多虧你二伯借錢給我們才過了難關。既然現在你二伯家要用錢,那就還債。」
頓了頓,江黃氏的聲音哽咽起來:「義兒你要爭氣,好好讀書上進,將來能進學中舉,賣了的田還能買回來。」
回到書桌前,江安義手中拿著書,腦袋裡糟糟的,一個字也看不進去。屋簷下,安勇和妍兒張著手接著雨簾,兄妹倆彈著雨珠嬉鬧著。年不識愁滋味,弟妹年紀還小,自己怎麼能裝作什麼都不知道,讓娘一個人承力。
夜,風雨不歇。江安義睡不安寧,輕輕推開安勇橫過來的,翻了個。窗外,雨聲淅瀝,鎮上的開始了,快五更了吧。過了會,正屋裡有了靜,娘起床了。
娘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到爹的牌位前焚香禱告,細碎的聲音輕輕傳來,「……都好,你不要掛念……孩子們都懂事,隻是眼下有了難……你不要怪我……」抑的哭泣聲時斷時續地傳出,夾雜著風雨搖竹葉的「沙沙」聲,分外淒涼。
Advertisement
來年自己十六歲,按大鄭律算年了,年後有田地分配,但是未墾過的荒地,同時還要服徭役,家中人手不夠,花費會更多?如果自己一時考不中秀才怎麼辦,靠賣地能支撐多久,地賣盡後,難道真要賣掉妍兒嗎?江安義再也躺不安穩,翻坐起,腦中閃過一家人分離的場景,出了一冷汗。
人的長大有一個過程,快慢因人而異,聽到孃的哭訴,江安義覺得心到極,四分五裂開來,痛到極反而放鬆下來,一下子長大了。
夫子說「修齊家治國平天下」,眼下家都要保不住了還談什麼其他。自己的妖魔既然有法子,那便是天無絕人之路,至於是生路還是絕路,先走下去再說。江安義咬著牙,上天要是震怒,就讓雷神劈死自己好了,隻要能保住家人的平安,自己心甘願。
渾渾噩噩地起床,渾渾噩噩地坐在桌邊,渾渾噩噩地喝著糜子粥,江安義神魂不定。妍兒發現哥哥的反常,詫異地問道:「哥,你怎麼不吃『紅燒』。」將芋頭比做「紅燒」說法很得家人的歡心,妍兒每見芋頭都要笑稱吃「紅燒」了。
被妹妹喚醒,江安義下定了決心,心輕鬆了下來,思路也活躍起來。說起吃食無非是「山珍海味」,那尺許長的蝦沒見過,不過「飛斑走兔」倒是尋常,鎮周圍都是山,山中走不,野、野兔、竹鼠、野羊、野豬等常見,偶爾還有野牛、黑熊、老虎出沒。鎮上有二家獵戶,農閑時不人會上山,采山貨、獵野味賣給王記山貨鋪,對農家來說是筆不小的財富。
那妖魔常空手進深山老林,借著天地自然之生存,其中有因地取材挖陷阱、下繩套抓野的法子,法子簡單易學,鎮上的獵戶都是用弓箭狩獵,沒聽說誰會布陷井抓野。一招鮮,吃遍天,家裡生計不妨從設套抓開始。
Advertisement
雨過天晴,今天安勇沒有事,吃罷早飯腰間別把鐮刀上山砍柴。江安義忙住弟弟,對江黃氏道:「娘,家裡的柴火不多了,我跟安勇一起上山去。」作為農家的孩子,江安義不可能整天坐在書桌前讀書,劈竹、砍柴、挑水、下菜地的活都得乾,江黃氏點頭答應了。
妍兒跑過來牽住兩人的服,央告道:「哥哥哥哥,上山記得給我摘點果子來,山裡紅、野栗子,妍兒好喜歡。」
大雨洗過的蒼山含翠,綠水帶幽,這是未曾破壞的自然景最樸實的展現。則矣,然而雨水也讓山路變得泥濘難行,鬱積在樹葉上的雨水震落下來很快打了服。
兄弟倆山腳下選了雜樹集的地方,很快就砍好了兩捆木柴,來的時候答應妍兒找野果子,兩人沿著崎嶇的山路向上行去。山風陣陣,空氣格外清洌,八月的山野彩富,綠的、黃的、紅的、紫的隨地山林間潑抹著,各的野果在荊棘叢中飄香,道旁草叢中不時驚起一兩隻山雀、野,「蓬」的一聲展翅飛遠,驚落一枝雨水。
江安義深深地吸了口清冽的空氣,覺得整個人都輕快了許多,慢慢地邊走邊看,在草叢中、灌木叢中發現了不走過的痕跡。江安勇靈巧地像隻野羊,一會兒就鑽灌木叢中不見了,再出現時,腰間布袋子已經鼓了起來,手中還捧著一捧野果,含糊不清地讓江安義嘗嘗。
江安義心中有事,有意往林深草茂走,細心地檢視著鳥出沒的痕跡。選好地方,江安義拿出準備好的細繩,彎枝布陷井,一邊忙碌一邊對江安勇道:「這是我從書中學來的捕之法,你認真看好,行的話以後就要你上山來設套。」
Advertisement
江安勇高興地跳起來,一隻野值二十多文,一隻兔子能賣三四十文錢,這個法子真能抓到野的話,娘就不用那樣辛苦了。忙了一個多時辰,兩人設了四陷井,待直起腰時,太當空照,汗水晶瑩如珠。
挑著柴回到家裡,看著妍兒吃著野果,瞇著笑眼滿心陶醉在幸福中,江安義暗暗祈禱:但願陷坑有效,隻要能讓家人過得開心,我就算墜地府也不要。
第二天一早,兩人趁著江黃氏不注意溜出了門,小跑著向山上奔去。山中野從未經歷過陷井,四個陷井居然有三個繩套套住了獵,二隻兔子一隻野。江安勇樂壞了,忙手忙腳地按住猶自活蹦跳的野兔,解開腰帶牢牢綁。秋天的獵膘胖,二隻野兔和一隻野加起來有十多斤了。
拿著獵,兄弟倆興高采烈地回了家,老遠就看見江黃氏滿麵怒容地站在院中。江安勇沖哥哥做了個鬼臉,跑了過去,不等娘發火,獻寶式地將背著的獵舉了起來,笑道:「娘,你看,哥抓住了什麼?」
兩隻兔子一隻野能賣上百餘文錢,抵得上江黃氏編一個多月竹籃的收了,江黃氏顧不上生氣,眉開眼笑招呼兒子將獵放在地上。妍兒看見野上斑斕的羽,出小手輕輕地,不料旁邊的兔子突然狠地一掙,嚇得妍兒一跳,趕躲在江安義的後,惹得江安勇哈哈大笑。
妍兒拉著江安義的衫,惱怒地瞪了二哥一眼,小心地探出頭,烏溜溜的眼珠帶著幾分驚恐地看著掙紮的兔子。獵居然是活的,江黃氏也手足無措起來,嚷道:「小心別跑了,勇兒,你仔細拎著,這就上山貨鋪去。」
江安義回來的路上盤算過,開口勸道:「娘,既然這法子好使,以後抓到獵的機會多得是。咱家飯菜過素,弟弟妹妹都太單薄,您也要補補,要我說留下一隻兔子自家食用,離還債還有時間,錢應該有著落。」
江黃氏看到兒們滿懷希翼地著自己,嘆了口氣,點頭同意。
猜你喜歡
-
完結1953 章

北宋大丈夫
后人都說大宋無丈夫。 從而是弱宋。 弱宋不能自守,偏安一隅。 遂使神州陸沉。 沈安很想做個大丈夫,但他得先背著四歲的妹妹在汴梁城中求活……
509.8萬字8 13150 -
完結472 章

最強呂布之橫掃千軍
雇傭兵穿越到即將在白門樓被殺的呂布身上,逆天改命反敗為勝,靈魂和肉體融合,讓他一夜之間回歸少年風華。多年沙場經驗,少年無窮力量,試問天下誰敢相抗?
108.2萬字8 12857 -
完結1353 章
官居一品
數風流,論成敗,百年一夢多慷慨.有心要勵精圖治挽天傾,哪怕身後罵名滾滾來.輕生死,重興衰,海雨天風獨往來.誰不想萬里長城永不倒,也難料恨水東逝歸大海.
456.8萬字8 18550 -
完結105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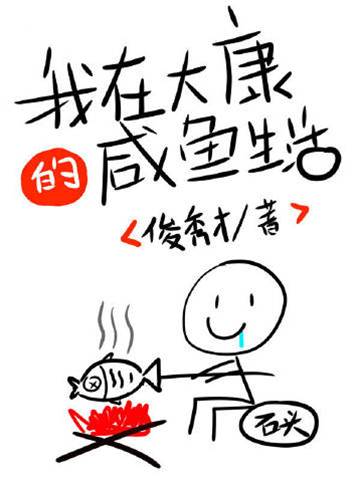
我在大康的咸魚生活
轉生開局就是親王世子,俗稱小王爺 大康國朝安穩,四海清平,商業發達,皇帝大伯又是出了名的寬厚待人 我以為我已經站在了人生的巔峰,可以一直飛,一直爽,不斷飛,不斷爽…… 結果現實卻和我開了個天大的玩笑 世間最殘忍的一幕,就這麼展現在了我的面前…… 我本想當一條與世無爭的快樂鹹魚,可你們為什麼偏偏不讓我如願呢?
321.5萬字8 5199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