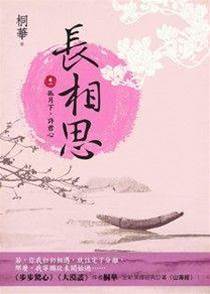《春閨秘錄:廠公太撩人》 第七十八章心結
在夢裡,年臉大變,心都快跳出來了,驚慌地喊道「三弟!」
他想都沒有想就沖了上去,想接住三弟,一旁的僕從都被這個變故驚住了,反應遲滯了一下。書趣樓()
於是,僕從們便見到二爺衝上前,正好接住了三爺。
幸好沒事!僕從們正想鬆一口氣,便聽到了一聲劇烈痛呼「啊……!」
痛呼的,是二爺!隻見二爺倒滾在地,臉容痛得都扭曲了,而他右眼上,正著一樹枝。
樹枝……原本在三爺手中的樹枝,現在到了二爺右眼!
鮮從二爺右眼汩汩流下來,一下子就淌了滿臉,目皆是鮮紅……
「二哥!」葉安世大了一聲,倏地睜開眼,額頭上全是冷汗。
二哥,二哥傷了眼睛,滿臉都是,快些大夫來,快些大夫來!
葉安世想開口,卻發現自己嚨乾,他迷糊地看了看周圍,發現自己是在映秀院,整個人瞬間清醒過來了。
又夢見了,似乎還能看到那些黏膩的鮮。那麼久遠的事,他以為自己忘記了,卻清晰雋永地深刻在夢境裡。
葉安世曾無數次地想如果當時沒有拉著二哥去明照湖就好了,如果當時沒有折下那樹枝就好了,如果……
哪有那麼多「如果」呢?二哥的右眼因此瞎了,再沒能參加試,而且永遠與仕途絕緣了。
Advertisement
二哥毀掉的,豈止是一隻右眼?二哥的滿腹才學和遠大抱負,再也不能施展了。
葉安世直到出仕後,才深刻知道,自己是怎麼年無知地毀掉了二哥的人生。
意外?的確是意外。可是每一場意外的背後,都潛藏著無數的輕忽,並不是一句「意外」就能揭過去的。
更別說,在二哥傷後,家中還發生了那麼多禍事。長姐葉奼執意認為這一切都是母親在背後指示的,誓言一定要母親付出代價。
沒幾天,母親就落了胎。聽府中的下人說,那是個已經了形的男胎,還有兩個月就能生下來的。
原本,他會有個弟弟的,他還想過定要對弟弟很好,就像二哥對自己那樣……
可是這一切,都在他爬樹那天戛然而止。
此後二哥就變得沉默寡言,再也不會帶著他玩;長姐總是惡狠狠地盯著他,說他們母子從裡到外都泛著惡毒狠。
母親不久便移居佛堂,葉家就好像變了個樣。明明是一家人,彼此卻像陌生人,乃至像仇人。
這些年來,二哥總是這副漠然態度,想必還在記恨當年的事吧?
葉安世窮盡半生,也沒法解開這個兄弟死結。除非,他能還二哥一隻眼睛……
宿醉的後果漸漸出現了,他隻覺得太生痛,卻不得不掙紮著起來,因為父親葉居譙派人來喚了。
直到他在延院外看見葉安固,腦中還是混沌,不上前笑著打招呼道「二哥,二哥你來給父親請安?」
Advertisement
聞到他上的酒味,葉安固皺了皺眉,隨即漠然地點了點頭。
他像是想起了什麼,突然站住了,冷冷問道「鉦哥兒出事,是不是你所為?」
他聽大嫂和父親說起了儀鸞衛之事,總覺得太蹺蹊了。第一時間湧上他心頭的,便是當年那些事。
同樣是遇到關鍵事之際,同樣是突然出了意外,怎麼會那麼巧?
聽到這質問,葉安世瞪大了眼,苦道「二哥,你竟這樣想……我怎麼會做這樣的事?」
葉安固上下打量著他,眉眼冷道「你不會?誰知道你不會?不然鉦兒的怎麼那麼巧就斷了?」
這些話一落,兩人都沉默了。葉安固心頭有些懊惱,然而他冷淡慣了,麵上也收不回這些話。
葉安世到無比難過,還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心灰意冷。原來,二哥是這麼看自己的,二哥心底裡還是覺得自己惡毒狠吧?
葉安世突然喪失了辯解的心思,隻是雙肩塌著,沉默地越過葉安固,走進了延院。
他不知道,他後的葉安固一直看著他,目異常複雜。
此時,在映秀院,葉綏和陶氏正在清點二房送來的禮,忙得停不下來。
葉綏看著擺在院中那一箱箱禮,好奇地說道「娘親,怎麼會有這麼多年禮呢?我還以為會很的。」
畢竟,二伯對父親的態度,昨日親眼見到了。可是沒有想到,二伯竟然會送來這麼多年禮,從裳首飾到賞玩件都不缺,看起來都是品。
Advertisement
「你二伯,其實很好。儘管他對你父親冷淡,但送來三房的東西,並不比大房的差。」陶氏這樣答道。
葉綏點了點頭。如此看來,二伯當真是個矛盾的人。儘管他態度冷淡,卻送來了這麼多品。可見,他心裡還是很關心父親。
葉綏再一次問道「娘親,到底當年發生了什麼事?大家都是這樣的態度?」
這件事,必定與二伯瞎掉的那隻眼睛有關,隻是是怎麼樣的?
陶氏看著二房送來的東西,想到了自己相公的醉酒,想了想,還是說道「你二伯那隻眼睛,是你父親不小心弄瞎的。隻是當年他們都小,你父親是無心之失……」
陶氏徐徐說道,將自己所知道的事說了出來。陸陸續續從自己相公口中聽到這事,然而這件事,是他心中的傷疤,他並未說得十分細緻。
雖然細節不清楚,但足以讓陶氏明白了當時的況。
聽說二伯小時極聰慧,頗有文名。相公意外從樹上摔了下來,手中的樹枝剛好進了二伯的眼中。二伯因此瞎了,從此與仕途絕緣。
已經出嫁的大姑葉嫵認為,是老夫人故意教唆相公這麼做的,為的便是毀了二伯。
為此,老太爺將老夫人遷了佛堂,相公與二伯的關係逐漸變差,最後就了現在這樣。
葉綏聽了,久久沉默。一場意外,瞎了二伯的眼,傷了葉家兄弟和睦,阻了祖母與父親的親緣,如果沒有人從中刻意推,,是怎麼都不會信的。
Advertisement
大姑母葉嫵……葉綏對沒有什麼印象,似乎大姑母比父親二伯年長許多歲,在葉家出事前就病死了。
原來,二伯和父親之間的心結,是這麼結下的,到底怎樣才能解開呢?
永昭十八年年末,葉綏心頭思慮的,便是這個問題。可是不知道,對葉家三房來說,一場巨大的危機已在悄悄醞釀。
猜你喜歡
-
完結97 章

廢後謀
那年,看見他,仿佛就已經中了她的毒,日日思念不得見,最後她嫁給了他的兄弟,他只望她能幸福,哪成想,她的夫君一登基,就將她打入皇陵守孝,既然如此,他不會在放過與她相守的每一個機會了,就算全天下人反對,又如何,他只要她。
17.4萬字8 9476 -
完結5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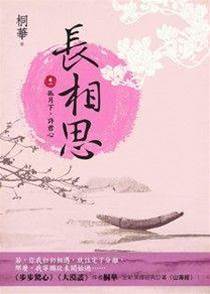
長相思
生命是一場又一場的相遇和別離,是一次又一次的遺忘和開始,可總有些事,一旦發生,就留下印跡;總有個人,一旦來過,就無法忘記。這一場清水鎮的相遇改變了所有人的命運,
63.4萬字8 5817 -
完結353 章

嫁給白月光的宿敵之后
蘇明嫵本該嫁進東宮,和青梅竹馬的太子舉案齊眉,然而花轎交錯,她被擡進了同日成婚的雍涼王府中。 恨了符欒半輩子,住在王府偏院瓦房,死前才知策劃錯嫁的人是她的心頭硃砂白月光。 一朝重生,蘇明嫵重生在了洞房翌日。好巧不巧,她正以死相逼,要喝避子湯藥... 天子幼弟符欒,十四歲前往涼州封地,十六歲親自出徵北羌,次年得勝被流箭射穿左眼。這樣心狠的大人物,大家心照不宣,蘇明嫵這朵嬌花落入他的手裏,怕是要被磋磨成玩物不止。 尤其是這個美嬌娥,心裏還掛念着她的小情郎,哪有男人能忍得? 雍涼王聞此傳言,似笑非笑點了點頭,好巧,他深以爲然。 婚後滿月歸寧那日,經過樓閣轉角。 “嬌嬌,與母親講,王爺他到底待你如何?可曾欺負你?” 符欒停下腳步,右邊長眸慵懶地掃過去,他的小嬌妻雙頰酡紅,如塊溫香軟玉,正細聲細氣寬慰道:“母親,我是他的人,他幹嘛欺負我呀...” 她是他的人,所以後來,符欒牽着她一起走上至高無上的位置。
53.8萬字8.18 5708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