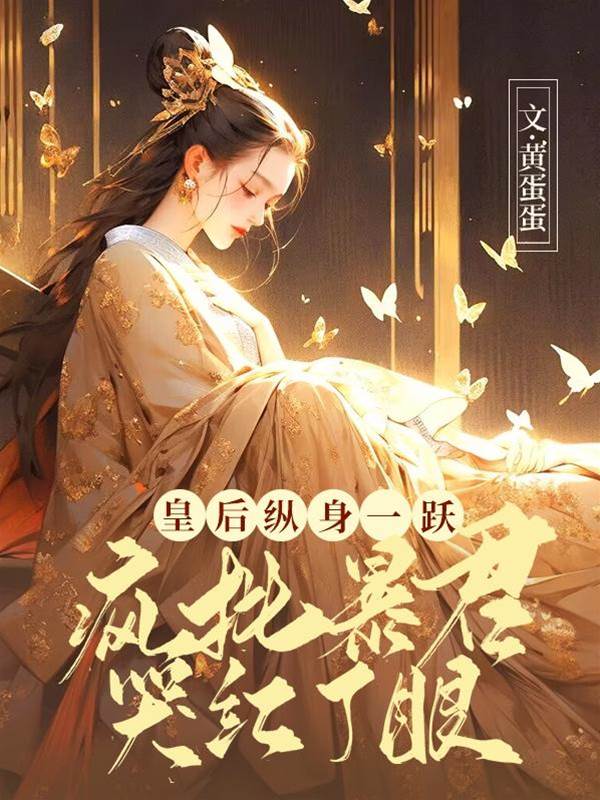《啞女的戀愛經》 第41章 嫌隙
郭盼弟看見郭巧的裳,稀罕得要命。
聽說是清啞織出來的,立即嚷著要教。
一旁的吳氏和阮氏愣住了,這才想起招眼的麻煩。
阮氏正想如何回,就聽清啞道:“上回教的你會了?”
郭盼弟一扭子,不好意思道:“還不。”
明白了清啞的意思:貪多嚼不爛。
才學織錦沒兩年,哪裡能像清啞那樣,會自己設計呢。
見不再堅持,吳氏和阮氏都松了口氣。
因又有人來,清啞便帶郭盼弟到樓上去坐。
郭盼弟悄聲告訴,李紅棗和張福田回家過年了。張家和李家在人前顯擺的很,說的他們在城裡賺大錢一樣。
“清啞姐姐,要是你去了,肯定比紅棗賺得多。那手藝算什麼!”
盼弟氣鼓鼓地,使勁踩踏李紅棗。
因為李紅棗含糊跟人說,張福田不喜歡清啞,所以才和好的。盼弟不敢把這話告訴清啞,一肚子火氣沒發。
清啞不想說這話題,便問“水芹呢?”
郭盼弟搖頭道:“不曉得。在家吧。我當然先來給大伯娘拜年。要不等會我們去找?”
清啞搖頭。
不想去別人家。
郭盼弟又湊近說了一樁,“水芹娘想跟你們家結親呢。”
見清啞愣神,補充道:“就是三哥,大貴。”
清啞便明白了,陳水芹家看上郭大貴了。
“我娘說,大伯娘不樂意。”
郭清啞覺怪怪的,為妹妹,怎麼沒聽說這回事呢。
正想著,下面又來人了,是楊安平媳婦帶細妹來磕頭道謝。
娃兒多在家裡忙,所以郭盼弟沒見過細妹,待聽下面“細妹細妹”地,弄明白後,失聲笑道:“細妹?還真是細妹!細細的妹子!一陣風都能刮走。”
巧兒跟著笑,只有清啞沒出聲。
Advertisement
堂姊妹說些閑話,不覺就到了晌午。
郭家男人在裡正家吃飯,吳氏就留了郭盼弟吃飯。
如此混了一天,就到了年初二,天放晴。
一大早,郭大全兩口子就忙著去竹塢。
一來蔡氏娘家就剩母子兩個,做婿的於於理都要早去探;二來江明輝雖然說年初二來郭家,倘或有意外況來不了呢?郭大全兩口子去竹塢一趟,心裡也好有個數,反正晚上就回來,江明輝來也好,不來也好,橫豎耽擱不了事。
他兩口子帶著郭勤郭儉,搖自家烏篷船往竹塢去。
阮氏在年前跟娘家說好了,今年有新親上門,要晚些日子回娘家。
吳氏很滿意的識趣,說等初十後讓回娘家住幾日。
至午後,江明輝便來了。
穿著清啞為他做的湖藍錦,俊秀非常。
看見坐在門口曬太的清啞,映著後屋頂上的積雪,靜謐得好像一副人畫,他急切的心便沉澱下來,出一樣燦爛的笑容。
有了他,清啞這閑坐吃喝的日子也趣味盎然起來。
還是跟以前一樣不出聲,但看著他和巧兒逗趣,不時地看看,使個眼,又笑地問些沒要的話,怎麼樣都甜、都自在,渾不知明日有愁煩。
郭大全一家四口是天快黑了到家的。
見面說話一團喜氣,等吃過晚飯,江明輝、郭大貴、清啞和郭勤幾個小的去了大貴房中玩遊戲,他才和蔡氏將在竹塢聽見的流言告訴爹娘和郭大有夫妻,蔡氏憤憤地在一旁添油加醋。
郭守業聽了頓時沉臉。
吳氏氣得渾發抖,“我就曉得那死婆娘不安分!”
又問蔡氏,“這子,怎沒聽你和你娘說?”
語氣頗有怨怪的意思。
蔡氏忙道:“哎呀娘,往年不這樣的!”
Advertisement
郭守業沉聲道:“說這些有什麼用!人善被人欺,馬善被人騎,還不都是和張家退親鬧的,他們以為我們等急嫁兒呢。江家婆娘死要臉面,得了便宜賣乖,故意讓人家說。”
郭大有和郭大全對視一眼,道:“我看是錢鬧的。”
郭守業夫婦都詫異地看向他。
郭大有輕聲道:“清啞不該畫那些畫給明輝。”
吳氏聽了更是氣得心口疼。
心裡把江婆子罵了個狗淋頭,怪不知好歹。
郭大全問弟弟:“你清啞別畫給他了,清啞聽了沒?”
郭大有點頭道:“聽了,沒畫了。”
郭守業見吳氏眼神閃爍,曉得要強子的,鄭重叮囑道:“你別跟那江婆娘一樣不曉得好歹,誤了清啞。明輝可是個好娃兒。先忍一忍,等將來他們親了,咱們再想法子幫襯,他們小兩口單過。眼下……”
他說著沉思,以他的脾氣,也是吞不下這口氣的。
郭大有話道:“眼下我們什麼都別說。親以前,清啞都不許幫明輝畫稿子。要是縣城的鋪子開張後生意好,那時候江家自然要求上門來;要是生意不好,更不用畫,落得自在。生意好的話,他們再要清啞畫畫,就要提條件,把話說在明。到時候看江婆子怎麼樣。”
郭守業和吳氏等人都聽得眼睛發亮,都笑了。
阮氏道:“這法子好,不聲不響他們來求。”
蔡氏問:“要是生意不好呢?”
郭大全“哼”了一聲道:“生意肯定好——瞧明輝在鎮上怎麼樣就曉得了。年前他才有幾幅好畫,都不個樣子!”
郭大有也點頭附和。
“就這樣。”郭守業吩咐道,“你們別在明輝跟前擺臉子。”
眾人都答應了。
吳氏特別叮囑蔡氏:“你管好,別說。”
Advertisement
蔡氏連連答應。
當下眾人裝著沒事一樣,也不跟江明輝說。
第二天,郭家請本家親戚來陪新姑爺吃飯。
來了許多人,席間,郭裡正等人把江明輝誇了又誇,弄得他臉都紅了。喝了些酒,瞅了個空跑去外面廊下,對清啞說,“我們村的人都誇你針線好,手巧,說我穿了這裳比富家公子還面呢。”神頗為得意,染了胭脂一樣的面,別有韻味。
清啞安靜地看著他,眼中出喜悅的芒。
江明輝就覺得心的,既心滿意足,又有些不足。
心滿意足是因為眼前的好;不足則是怕它太短暫、流逝太快。因歎氣道:“唉,過幾天就要去縣城了。爹和大哥都我早些去。去了,就不能像以前一樣常來了。”
清啞想說“兩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然習慣使然,心裡想到了,卻忘記說出來,但目比往常和,江明輝卻看懂了——在安他呢。
“你可會想我?”他問。
清啞沒有猶豫地點點頭。
江明輝更加歡喜。
人都覺得不說話心思難猜,只有他知道的純善。
“我用心掙錢,早些接你過門。”
他低聲音對道。
清啞卻搖頭。
這一回,江明輝沒弄懂的意思。
可他來不及問了,郭大全出來他進去。
※
江明輝在郭家待了三天,不好意思再待,回去了。
然他在家不過住了一晚上,就熬不住了,借口跟清啞琢磨竹畫,又到郭家來了。
這一回,又住了三天才回去。
走時和清啞依依不舍。
他是千言萬語說也說不完。
清啞是萬語千言說不出口。
然終究還是要走的,還有好些事等著他呢。
幾乎是一上船,他的思念就開始洶湧。
待回到家,因見他空著手,一張圖稿都沒帶回去,江大娘不高興了,問他,他說清啞忙,沒空畫。他說的實,他們兩個說悄悄話都來不及,哪裡有空畫圖稿!
Advertisement
江大娘很生氣,說畫一幅畫要多時候,就忙那樣。
江明輝聽了很無語,加上心不好,懶得跟說,避開了。
江大娘便有些驚疑不定,不知郭家什麼想法。
正月十五過後,江明輝便帶著小堂侄竹去了霞照縣。江家老大和老二也都跟著去了,因為要押送貨,也順便認路。下回還要送貨呢,以後這條路要常走的。
兄弟幾個懷揣憧憬,忐忑不安地來到陌生的城鎮。
霞照縣既是南北通衢要道,也是水路重鎮。
朝廷在此設錦署衙門、開織錦大會,是英武年間的事。
英武帝乃曆史上見的英明睿智帝王,其雄才大略遠超曆朝君主,最是敢破舊革新,開創了許多利國利民的舉措。
當年,錦署衙門被權貴把持,造衙門淪為權貴斂財之地,他便下旨廢除了造,改從民間選拔實力雄厚、技優秀的錦商為皇商。
織錦大會由此產生。
逐利乃人之本,這也不能避免商勾結。
但天下錦商都參與競爭,角逐的結果達到一個微妙的平衡,破除了一家獨大的局面,錦署長和權貴再不能隨心所地安排隨便什麼人接掌織造生意。
十來家實力雄厚、技優秀的錦商便穎而出,為皇商。在他們下面,更有一批二流、三流的錦商汲汲營營,一個不慎,就會被代替,為昨日黃花。上要應對朝廷權貴和員,下要防範同行競爭,因此各家無不兢兢業業,如履薄冰。
曆經百年風霜,數家錦商為織錦世家,底蘊厚。
即便是朝廷權貴,也不能輕易搖他們的本。
不僅因為他們每一家背後都有著盤錯節的關系,更因為他們與普通商賈相比,雖也逐利,卻多了些涵,以詩書充實本,提高織錦的品味,不是等閑商家可比。
因此這行便不是有錢有權就可以手的生意了。
霞照縣雲集了天下錦商,越來越昌盛,附近的紫砂、漆、竹和南方的瓷也逐漸匯集過來,是把個小小的縣城發展為水陸重鎮,其繁華富庶便是州府治地也比不上。
江明輝就好像一滴水,融這富貴繁華溫鄉中。
這滴水卻沒有消失不見,而是興起了小小的浪花。
*
猜你喜歡
-
完結1183 章

貴妃每天只想當咸魚
蕭兮兮穿越回古代,成了太子的小老婆之一。 本應該是宮斗的開始,可她只想當咸魚。 爭寵?不存在的! 咸魚才是生存之道,混吃等死才是人生真諦! 可偏偏, 高冷太子就愛她這一款。 …… 蕭父:閨女,你要爭氣啊,咱家可就指望你攀龍附鳳了! 蕭兮兮:不,我只是一條咸魚 宮女:小主,您要爭氣啊,一定要打敗那些綠茶婊成為太子妃! 蕭兮兮:不,我只是一條咸魚 太子:愛妃,你要爭氣啊,孤就指望你傳宗接代了! 蕭兮兮:不,我只是一條咸魚 太子:無妨,咸魚我也可以。 …… (1V1寵文,雙潔,超甜!)
191.1萬字9.48 5393384 -
完結563 章

丞相府的小娘子
沈梨穿越了,穿到一窮二白,剛死了老爹的沈家。上有瞎眼老母,下有三歲幼兒,沈梨成了家里唯一的頂梁柱。她擼起袖子,擺攤種菜,教書育人,不僅日子越過越紅火,就連桃花也越來越多,甚至有人上趕著給孩子做后爹。某男人怒了!向來清冷禁欲的他撒著嬌粘上去:“娘子,我才是你的夫君~”沈梨:“不,你不是,別瞎說!”某人眼神幽怨:“可是,你這個兒子,好像是我的種。”沈梨糾結:孩子親爹找上門來了,可是孩子已經給自己找好后爹了怎麼辦?
87.5萬字8 21269 -
完結1427 章

娘娘是個嬌氣包,得寵著!
現代牛逼轟轟的神棍大佬林蘇蘇,一覺醒來發現自己成了個棄妃,還是有心疾那種,嬌氣得風吹就倒。爭寵?不存在的,鹹魚保命才是生存之道!可偏偏,身邊助攻不斷!太后:趁著皇帝神志不清,快快侍寢,懷上龍子,你就是皇后!林父:皇上受傷,機會難得,閨女快上,侍疾有功,你就是皇后!只有宮妃們生怕她林蘇蘇一朝得寵。於是!今日宴席,皇上微熏,絕不能讓林蘇蘇去送醒酒湯!遂,一眾妃嬪齊心協力,把林蘇蘇困在了冷宮。可誰來告訴她! 冷宮那個眼尾泛紅的男人是誰啊!到底是哪個不長眼的,又把皇帝送到了她眼前啊!!
128.6萬字8 80306 -
完結3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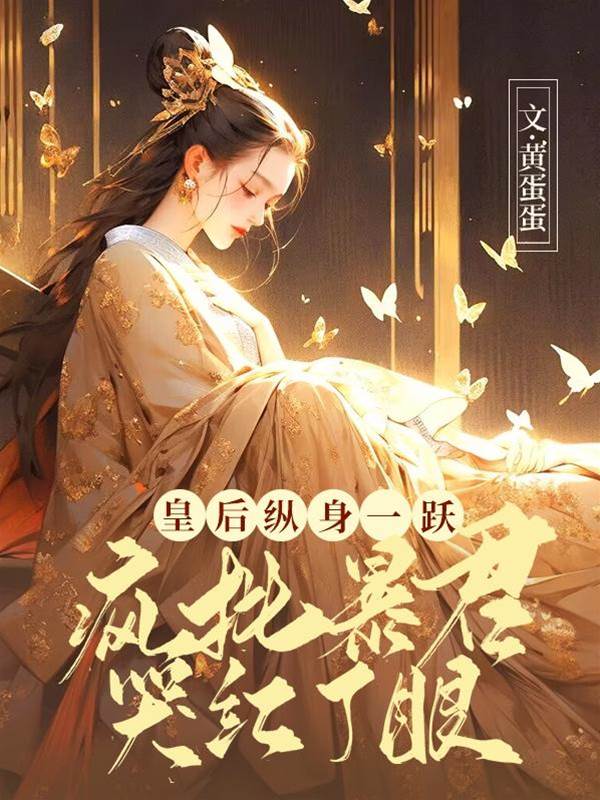
皇後縱身一躍,瘋批暴君哭紅了眼
【1v1,雙潔 宮鬥 爽文 追妻火葬場,女主人間清醒,所有人的白月光】孟棠是個溫婉大方的皇後,不爭不搶,一朵屹立在後宮的真白蓮,所有人都這麼覺得,暴君也這麼覺得。他納妃,她笑著恭喜並安排新妃侍寢。他送來補藥,她明知是避子藥卻乖順服下。他舊疾發作頭痛難忍,她用自己心頭血為引為他止痛。他問她:“你怎麼這麼好。”她麵上溫婉:“能為陛下分憂是臣妾榮幸。”直到叛軍攻城,她在城樓縱身一躍,以身殉城,平定叛亂。*刷滿暴君好感,孟棠死遁成功,功成身退。暴君抱著她的屍體,跪在地上哭紅了眼:“梓童,我錯了,你回來好不好?”孟棠看見這一幕,內心毫無波動,“虐嗎?我演的,真當世界上有那種無私奉獻不求回報的真白蓮啊。”
53.4萬字8.18 4176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