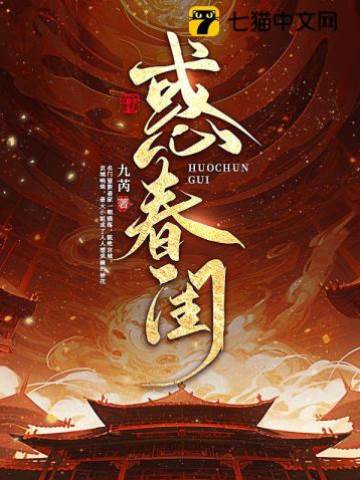《錦衣之下》 第一百二十三章
過了好半晌,今夏才略略松開手,只覺得他的左臂似乎使不上勁,忙問道:“你的手傷了?”
“在岑港時,被火銃了一下,皮外傷。”陸繹輕描淡寫道。
因在夜里,看不清他的臉,直至牽著馬進了城,今夏借著火打量他的臉,才驚覺他臉煞白……
岑壽直到此時方才上前施禮:“大公子!”
“你先回去休息好不好?”今夏擔心陸繹還有別的要事在,又怕他有傷,如何吃得消。
一路星夜兼程而來,加上有傷在,陸繹全憑意志支撐著,現在已覺到力不支,點了點頭,朝岑壽道:“你哥回京城辦點事,過些天才來,你不必擔心。”
這原是岑壽想問的話,當下也放下心來。
陸繹行了兩步,忽眩暈,眼前一陣發黑,步伐不穩,岑壽趕忙上前幫忙今夏扶住他。
“大公子……”
“快快!你背上他。”今夏急道,“他胳膊上有傷,得趕讓我姨看看。”
聽聞陸繹傷,岑壽二話沒說,將陸繹背上,急步往別院奔去。今夏快步跟上。
***********************************************************
還未到別院,陸繹已然暈厥過去。
為陸繹重新將傷口包扎了一遍,沈夫人方才起,把醫包遞給旁邊的丐叔。
“姨,他怎麼樣?要不要?”今夏忐忑問道,“……這次的傷會不會牽上次他的傷?引起舊傷復發什麼?”
“丫頭,你盼他點好行不行?”丐叔邊捆扎醫包邊道,“我看他全須全尾的,睡得還香,好,沒事。”
“你懂什麼,他臉白像紙一樣,哪里好!”今夏急了。
Advertisement
示意丐叔莫開口,沈夫人聲安今夏道:“胳膊上是被火銃所傷,好在彈片已經取出來了,傷口理得也很妥當,并未化膿。只是估計他這兩日一直在馬背上,傷口難以愈合,只要接下來好好休養就沒事了。”
“可他怎麼會暈過去?”今夏仍是不安,“你替他理傷口,那麼疼他也不醒。”
“累了當然要睡,等他養好神,自然就醒了。”
“他,真的只是睡著了?”
沈夫人無奈笑道:“是,他睡著了,難道你還得非得把他喚起來才甘心。”
聽言之鑿鑿,今夏這才稍稍安心,在床邊坐下:“我守著他,萬一有事,我就趕去喚您。”
雖說此舉著實多余,但橫豎也不會放心,倒不如就讓守著。沈夫人點了點頭,與丐叔出了屋子。
“這孩子,對我這孫子也太上心了。”丐叔邊行邊搖頭嘆道。
沈夫人秀眉微蹙,思量道:“你也知曉陸繹的份,原本我也不愿與他行得近,擔心陸繹對不是用真心,但此番看來,他對今夏,還真是上心。否則也不會帶著傷趕這麼遠的路來,想必是聽說了倭寇攻打新河城一事,生怕有危險。”
丐叔怔了下:“你不是不喜朝廷之人麼?”
“是,我是不喜歡,簡直是深惡痛絕。”沈夫人嘆了口氣,“但今夏與我不同,陸繹的份正好能護著,娶為妻也好,納作妾室也罷……”
“等等等等,那丫頭哪里是個當妾室的料。”
“是不是那塊料另說,總得有個堅實些的靠山,便是他日東窗事發……”
“什麼東窗事發?”丐叔轉頭看。
沈夫人搖搖頭,不肯再說下去了。
*********************************************************************
Advertisement
陸繹醒來時,看見暖暖的夕照在紗窗上,些許余暉進來,把今夏的發綴得閃閃發亮……
就伏在他的床邊,偏著頭,手握著他的手,也不,睡得比他還沉幾分。
這幕,陸繹靜靜地看著許久,直至夕西下,最后一抹余暉也從屋中消失,他仍留地看著難得沉靜的眉眼。
有人輕輕推開門進來,是楊岳。
“今夏,過來吃點東西。”他先將手中托盤放到桌上,又取了火石燃起油燈,看見陸繹時楞了楞,繼而笑道,“陸大人,您醒了!”
陸繹想撐起子,無奈手被今夏握著,只得微微欠起,示意楊岳莫要驚擾。
“睡著了?”楊岳歪頭來看,見今夏果然睡著了,悄聲道,“陸大人,要不您吃點,您都躺了整整一日,該了吧?”
陸繹搖頭,輕聲問楊岳:“是不是累著了?”
楊岳笑了笑,道:“倭寇到了之后就沒睡過,您暈過去又把嚇得不輕,一直守在這里不肯窩。岑大人幾番想替換,回去歇著,就是不肯。沒想到,自己倒睡著了,想是熬不住困勁兒了。”
聽見聲音,今夏不適地挪了挪子,抬頭就先去看陸繹,見他也正睜著眼看自己,頓時清醒了一大半,喜道:“你醒了!上還有沒有哪里不舒服?我馬上把我姨來……”
“我很好,你不用忙。”
“真的沒事麼?”
今夏就著燈細瞅他的臉,相較之前已恢復了些許,仍是不放心地探探他額頭,又替他把了把脈。
“沒發燒,脈搏平穩……你把舌頭再出來給我瞧瞧吧。”
陸繹一直乖乖由著擺布,聞言,還真把舌頭給看,稱得上是百依百順。
Advertisement
“我說夏爺,你別折騰了,讓陸大人趕吃點東西是正經。”楊岳在旁都有點看不下去。
今夏如夢初醒,跳起來道:“對,你肯定了吧,趕吃點東西……大楊,你煮了什麼?”
“魚粥。”
僅僅聽到一個魚字,今夏就頗痛苦地皺了皺眉頭:“那些魚還沒吃完?”
“早呢,腌了好幾條,回頭炸了吃。”
陸繹起,接過楊岳遞來的外袍披上,趿了鞋下地,行到桌旁,笑問道:“怎得,我不在這陣子,你們發財了,天天大魚大?”
今夏替他盛了碗粥,邊吹邊抱怨道:“哪里有,就只有魚。這些日子我們天天吃魚,走路上貓都盯著瞧。”
“這里是何?”
陸繹看著屋子收拾得頗為雅致,并不像驛或是客棧。
“這是淳于家的別院,淳于老爺逃難去了,管事徐伯把這別院讓我們先住著……此事說來話長,你先吃著,我慢慢告訴你。”
就這樣,陸繹邊吃著,邊聽今夏嘰嘰呱呱把這一路的事統統都講了一遍。原就聲音清脆,口齒又甚是伶俐,這些事教說得有聲有,比茶樓里頭說書的還要彩幾分。
聽罷,陸繹想著竟然經歷那麼多危險,心下不由暗暗后怕,皺眉道:“早知如此,我該和你們一道來新河城才對。”
“你呢?我聽說岑港一直攻不下,圣上下旨撤了俞將軍的職務。”今夏頓了頓,不滿道,“還有人在背后嚼舌,說俞將軍被撤職,因為你去了,向圣上告了他的黑狀。”
旁人會這麼想,陸繹并不奇怪,然一笑道:“岑港已經大捷了,圣上應該很快就會恢復俞將軍的職務。”
“岑港大捷?太好了!”今夏想著,嘆口氣道,“汪直說,他死之后,兩浙必定大十年,看來一點不錯。現下原本在他麾下的倭寇分崩瓦解,變十幾,甚至幾十倭寇勢力,在沿海各鬧騰。那個渡口的難民……我還從未見過那種景象,總覺得兩浙得像一窩粥。若這時候撤換兩浙總督,恐怕是上加吧?”
Advertisement
陸繹嘆道:“不僅如此,胡宗憲手下頗有幾員大將,如俞大猷、戚繼等人,都是抗倭多年經驗富的將軍。若他被撤換,恐怕連這幾位將軍也要調配走人。”
“這是為何?”今夏不解。
“一朝天子一朝臣,何況只是兩浙總督,被胡宗憲重用的人,必定是下一任兩浙總督忌諱的人。除非這些將軍在朝中有過的靠山,才能保住職位,繼續留在兩浙建功立業。”
陸繹終于想明白了,為何嚴世蕃如此肯定他會幫胡宗憲。只因保住胡宗憲,就是保住他手下這些抗倭將軍,保住了這些將軍,兩浙才不至于被倭寇侵擾,以致生靈涂炭。
眼下朝中,在嚴世蕃的縱下,彈劾胡宗憲的折子不計其數,何況兩浙倭有愈演愈烈之勢,置胡宗憲只在圣上轉念之間。即便他上折子為胡宗憲開,恐怕也抵不過那些水般彈劾的折子,無法力挽狂瀾。
更不消說,只要替胡宗憲開,就會立即被嚴世蕃捉住把柄。
這樣的棋局究竟該如何應對?陸繹深顰起眉頭。
今夏支肘托腮,也想不出什麼好法子來,懊惱道:“圣上若像看重嚴嵩那般,對胡宗憲也如此看重,任憑旁人說什麼,估也舍不得撤胡宗憲的職。”
聞言,陸繹微微一怔,似乎想到了什麼,握了的手道:“你再說一遍。”
今夏渾然不覺自己的話有何用,但還是重復道:“我是說,圣上若對胡宗憲就像對嚴嵩那般,都不過來就好了,哪里會舍得撤他的職務。”
“對!就是這話。”陸繹喜道。
今夏莫名其妙道:“這話也只能說說,抵不上用的。”
陸繹朝笑道:“不,你說得很對,只要讓圣上對胡宗憲好倍增,縱然彈劾再多些,也不了胡宗憲兩浙總督的位置。”
長久以來,陸繹心深都以嚴世蕃為敵,而嚴世蕃最擅謀劃,設下的步驟如棋局般撲朔迷離,他只得步步為營,謹慎小心。今夏無意中的一句話,卻點醒了他,在此事上,他無須去想嚴世蕃究竟還有多后招,因為能決定一切的只有一人,就是高高在上的圣上。
說起來,這是朝廷的悲哀,但圣上的個人喜好的的確確左右著大明朝。
嚴世蕃所布下的這盤棋,他不下了。撥開棋局的迷霧,直接擒住能夠決定一切的人,才是最好的法子。
今夏仍是不解:“圣上在京城,胡宗憲在兩浙,連見都見不著,朝中還盡是彈劾他的人,你怎麼讓圣上對他好倍增?”
陸繹微微一笑:“圣上也只是個人,是人就有喜好。何況在他上打主意,比起對付嚴世蕃,還是輕松些。”
“你有法子了?”
“會有的。”
猜你喜歡
-
完結1853 章

法醫狂妃
她是21世紀女法醫,醫剖雙學,壹把手術刀,治得了活人,驗得了死人。 壹朝穿成京都柳家不受寵的庶出大小姐! 初遇,他絕色無雙,裆部支起,她笑眯眯地問:“公子可是中藥了?解嗎?壹次二百兩,童叟無欺。” 他危險蹙眉,似在評判她的姿色是否能令他甘願獻身…… 她愠怒,手中銀針翻飛,刺中他七處大穴,再玩味地盯著他萎下的裆部:“看,馬上就焉了,我厲害吧。” 話音剛落,那地方竟再度膨脹,她被這死王爺粗暴扯到身下:“妳的針不管用,換個法子解,本王給妳四百兩。” “靠!” 她悲劇了,兒子柳小黎就這麽落在她肚子裏了。 注:寵溺無限,男女主身心幹淨,1V1,女主帶著機智兒子驗屍遇到親爹的故事。 情節虛構,謝絕考據較真。
344.3萬字8.18 283217 -
完結1051 章
暴走正妃要休夫
大婚當日辰王司馬辰風正妃側妃一起娶進門荒唐嗎,不不不,這還不是最荒唐的。最荒唐的是辰王竟然下令讓側妃焦以柔比正妃許洛嫣先進門。這一下算是狠狠打臉了吧?不不不,更讓人無語的是辰王大婚當晚歇在了側妃房里,第二天竟然傳出了正妃婚前失貞不是處子之事。正妃抬頭望天竟無語凝噎,此時心里只想罵句mmp,你都沒有和老娘拜堂,更別說同房,面都沒有見過你究竟是從哪里看出來老娘是個破瓜的?老娘還是妥妥的好瓜好不好?既然你一心想要埋汰我,我何必留下來讓你侮辱?于是暴走的正妃離家出走了,出走前還干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192.9萬字8 34760 -
完結17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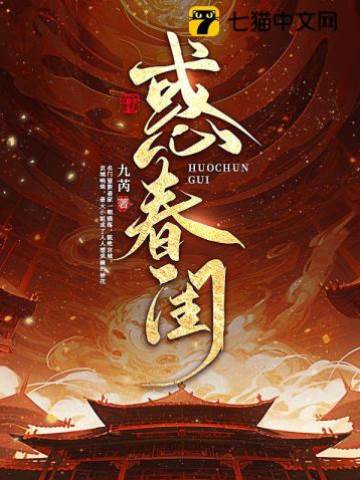
惑春閨
名門望族薑家一朝隕落,貌絕京城,京城明珠,薑大小姐成了人人想采摘的嬌花。麵對四麵楚歌,豺狼虎豹,薑梨滿果斷爬上了昔日未婚夫的馬車。退親的時候沒有想過,他會成為主宰的上位者,她卻淪為了掌中雀。以為他冷心無情是天生,直到看到他可以無條件對別人溫柔寵溺,薑梨滿才明白,他有溫情,隻是不再給她。既然再回去,那何必強求?薑梨滿心灰意冷打算離開,樓棄卻慌了……
31.5萬字8.18 789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