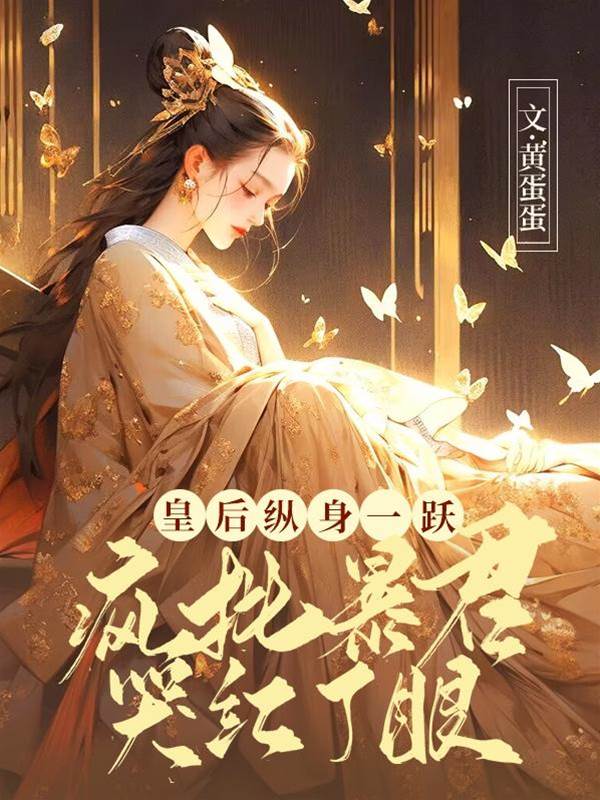《簪中錄》 第6章菩提四方(3)
宮中終于有消息來了,原來皇帝這次頭疾發作嚴重,暫不過來了。于是李舒白一行人便起,隨著宮監到離宮查看落況。離宮自然沒有大明宮那樣的奢華廣大,也沒有九宮那樣占地廣袤,但走走停停也足足走了一個來時辰。
黃梓瑕自然一直在李舒白后跟著。材輕盈,那一件普通的宦服穿在上卻顯得格外清勻修長,就算一言不發低頭跟在后面,卻也格外令人覺得好看。
李汭一路上瞧著,笑道:“四哥,你邊人怎麼換了?這小宦好像沒見過。”
李舒白若無其事,說:“景祐和景毓那幾個,也不知誰傳染了誰,都得了風寒。”
李潤卻一再打量著黃梓瑕,臉上稍有迷茫,覺得與自己記憶中的誰有相似之,只是一時想不到這小宦會像那個他曾驚鴻一瞥的。
李汭又問:“你這小宦什麼名字,年紀多大了?”
李舒白笑了笑,轉頭問黃梓瑕:“昭王似乎與你有眼緣,反正我也看不上你笨手笨腳的樣子,不如你跟了他,如何?”
黃梓瑕愣了一下,見所有人的目都聚集到自己上,便慢慢跪下來,低聲說:“小人聽說,一鳥難棲二枝,一仆難侍二主。茶樹發芽后則難以挪移,橘樹移到淮南便枳樹。小人蠢笨,怕是離開了夔王府后一時難以適應,反倒會沖撞貴人,犯下過錯。”
李汭笑道:“四哥真是調教有方,這一番話說下來,若是我堅持,反倒奪了他的志向了。”
李舒白似笑非笑,說:“確實伶牙俐齒。”
幸好此時康王李汶喊著累,一群人才放過了黃梓瑕,沿著原路返回。
重重宮墻花苑中,李舒白漸漸放慢了腳步,待走到一帶尾竹前,他邊已經沒有了其他人,只有黃梓瑕還跟著他。李舒白冷冷地回看著:“黃梓瑕,你跟著我干什麼?”
Advertisement
黃梓瑕低眉順眼地說:“良禽擇木而棲,我想留在王爺邊,以我的微薄之力,幫王爺的一點小忙。”
“什麼忙?”他冷冷問。
“遠的,如那條小紅魚,近的,如京城最近的‘四方案’。”
他的目落在低垂的面容上,冰冷而輕蔑,仿佛將看做空氣中一點微塵:“這些事,有的你不配幫,有的,與我毫無關系,需要你多事?”
站在尾竹之下,細細的竹葉籠罩在上,讓略顯蒼白的面容蒙山一種淡淡的碧綠,顯得更加沒有的纖細。抬頭仰著他,聲音低微卻毫不遲疑:“然而,大理寺與刑部既然束手無策,皇上又發了頭疾,我想,唯一能為皇上分憂的,恐怕只有夔王您了。”
“你不就是想要找個靠山,幫你洗所謂的冤屈嗎?”他毫不留地一口說破,“剛剛昭王讓你過去,你不是也有機會?”
“跟著他,沒有機會。”黃梓瑕面容蒼白,眼中淡淡一抹淺碧,卻毫無遲疑猶豫,“我不需要一個棲之所,更不需要安立命,我需要重新站在下,將我家所有蒙的屈辱都洗去。”
李舒白沉著一張臉,目冰涼地打量著。而仰著他,面容上除了哀求的神之外,還有一種暗暗的倔強,如深夜的霧氣,難以覺察,但分明就在那里。
李舒白冷冷地哼了一聲,轉向著水殿走回去。黃梓瑕跟在他后,他沒有回頭,卻也沒有放緩腳步。
到宮門口時,發現幾位王爺都在等著與夔王辭行。聽宦們說皇帝幾日后還要召集群臣一起為離宮的山水題詞聯句,眾人不覺都相視苦笑。
等人都走了,李潤與李舒白落在最后,李潤難免嘆道:“皇上真是寬心的人,如今藩鎮割據,宦勢大,皇上卻依然整日游宴作樂……”
Advertisement
李舒白淡淡道:“皇上是太平天子,這也是他和天下人的福分。”
李潤笑一笑,說:“四哥說的是。”他的目落在黃梓瑕的上,那張溫和善的面容上滿是疑。
李舒白問:“怎麼了?”
“這位公公,我似乎在哪兒見過似的。”他示意黃梓瑕。
李舒白便說:“我今日也是初見,不如讓到你邊服侍?”
“四哥說笑,剛剛九弟被拒絕過,我難道還自討沒趣麼?”他笑著,眉間一點朱砂在笑意盈盈中更顯瀲滟溫。
黃梓瑕低頭站著,不是看不到垂手可及的安穩春日,只是已經選擇了最艱難的一條路,就不會再回頭,茍且生不是的人生。
等諸王都走了,李舒白才上了車,黃梓瑕站在車門口,還在遲疑,卻聽到他的聲音:“上來。”
趕上了車,靠著車門站著。
馬車緩緩行走。待離開了離宮范圍,前后都是山野,李舒白抬眼看著外面的景象,冷冷地說:“我給你十天時間。”
靠著車門看著他,一聲不響地等著他繼續說下去。
他把目緩緩從窗外收回,落在的上,那一雙眼睛如寒星般,明明里面沒有任何溫度,卻深邃明燦至極,令呼吸微微一滯。
“今日午間,我們在建弼宮所說的那個案件,我給你十天時間,你有把握嗎?”
“或許。”黃梓瑕簡單地回答。
他靠在車壁上,神態悠閑:“現在,你有一個機會,可以洗自己的冤屈,重獲清白,當然,也能讓你的父母冤仇得報,真相大白。”
黃梓瑕略一思索,問:“王爺的意思是,如果我幫您破了這個案件,您就可以對我施以援手,幫我洗家族冤仇嗎?”
Advertisement
“當然不是。”山路崎嶇,他見的軀隨著顛簸而晃,便微抬下,示意在自己面前的小矮凳上坐下,才說,“我有一件事,想要找一個人幫我去做,但你如今無憑無據忽然出現在我面前,我如何相信你的能力?”
“我知道了。”黃梓瑕微微點頭,“若我在十天破了這個案子,才有資格得到王爺的信任。”
李舒白微一點頭,說:“至,你要讓我看到你是值得幫助的人,我沒有那麼多閑工夫,斷不會去幫一個本沒有能力,只會口頭上說說而已的人。”
黃梓瑕坐在矮凳上,低頭思索著,問:“刑部與大理寺人才濟濟,定然出了眾多人手在理此案,王爺準備讓我以什麼份去參與此事?”
“我會直接帶你去刑部,調查此案卷宗。”李舒白干凈利落地說。
“好。”黃梓瑕抬手一鬢邊,將自己束發用的那木簪拔了下來。簪子一離開頭發,滿頭的青頓時傾瀉下來,披散了滿肩滿。還帶著半水汽的頭發如烏黑的水藻,糾纏著半遮住了蒼白的面頰。
愣了一下,訥訥地將頭發拂到后,說:“抱歉,以前習慣了用簪子記號,忘記了自己現在是小宦,只有一簪子束著發……”
李舒白微皺眉頭,沒說話。低頭抬手,將自己的長發握住,在他的面前將自己的頭發挽一個發髻。
這個跋涉了千山萬水卻從未有過毫猶疑懼怕的,在這一刻,卻不自覺地在他的面前出一種怯的神來。
李舒白掃了一眼,看見低垂的面龐微微出一種暈紅。在這一刻他仿佛忽然察覺了,比他的手鎖住咽時還要深得會到,面前這個人,其實只是一個,而且是一個十七歲,并不像表面上顯的那麼冷靜的。
Advertisement
仿佛覺到了他在打量自己,默默地抬眼了他一瞬。只這一流眄間,他看見面容上極清朗明凈的雙眼,半遮半掩地藏在的睫下,仿佛是融化了秋水的神韻,鑲嵌在桃花般的面容上。
的五雖不是頂漂亮,卻難得眉宇清揚,有著五月清空般潔凈的靈秀。一種仿佛不解世事,又仿佛太過了解世事,顯得與俗世有點隔閡的疏離,在此時茫然又警覺著他的目中約呈現。
是個人。
他想起李潤剛剛說的,對十四歲的黃梓瑕的印象。
十四歲一舉名天下知的,如今已經長了十七歲裊裊亭亭的子。負莫大的冤屈,盡了天底下所有人的唾罵,卻并沒有被擊垮,反而迎難而上,力去尋求真相,期以自己的力量洗冤屈,使真相大白。
估計只看到的模樣,誰也不會相信,就是黃梓瑕吧——無論是有著名,還是背負惡名的那個黃梓瑕。
黃梓瑕盯著他,了自己的臉,略有張與無措。
“和通緝畫像上的模樣,十分相像。”李舒白將自己的臉轉向一邊,盯著錦簾上繁復糾纏的花枝,說,“以后,別再以這種模樣出現在人前。”
“是。”應了一聲,將自己的頭發束,然而才問:“王爺還記得,之前他們說的案發時間嗎?”
他毫不遲疑,說:“正月十七,二月二十一,三月十九。”
“今日是四月十六。也就是說,如果時間差不多的話,應該是到兇手快要手的時候了。”改用手指在車壁上緩慢地畫著那幾個數字,若有所思,“十天,兇手該有靜。”
“憑著這幾個數字,你能在京城上百萬的人中找出兇手麼?”
“不能。”停下比劃的手勢,若有所思,“在不知道兇手特征和機的時候,要在茫茫人海中抓捕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李舒白漫不經心地打量著:“所以,你沒有把握?”
黃梓瑕的手指又開始下意識地在車壁畫著,口中自言自語:“正月十七,死者老更夫,兇手留言:凈;二月二十一,中年鐵匠,兇手留言:樂;三月十九,死者四歲小孩,兇手留言:我……”
“四方案,第一樁,京城正北,第二樁,京城正南,第三樁,城西偏南。”李舒白又隨口說道。
黃梓瑕若有所思:“按理,如果真是面向四方的話,應該是盡量尋找正北、正南、正西的方位,但第三樁卻是在城西偏北,未免有點奇怪。”
“或許是正西方位沒有他的目標,或許是為了更方便地避人眼目下手?”
“嗯,目前看來,一切皆有可能,但還不知道確切原因。”黃梓瑕說著,又掐著指頭在那里回憶:“第一個死者為老人,第二個死者為壯年鐵匠,第三個死者為孩。”
李舒白靠在錦墊上,找了個最舒服的姿勢,才徐徐說:“此事我曾問過刑部的推丞。其他兩個老弱也就罷了,或許是死者要尋找一個最沒有抵抗能力的對象下手,但第三個孩,讓我覺得最為奇怪——因為,那是一個已經凍得奄奄一息的四歲孩子,被父母拋棄在路邊,過路人發現送來后,已經難以救治。就算兇手不下手,估計這個孩子也活不過那一夜了,然而這個兇手卻偏偏潛善堂,殺死了那個孩子,這豈不是多此一舉嗎?”
“嗯,這確實是奇怪的一點。一個本就已經瀕死的孩子,有什麼必要冒著被人發現的危險,潛進善堂去非要殺一個臨死的孩子呢?”黃梓瑕皺起眉,手指又開始無意識地在車壁上劃著“常樂我凈”四個字。
李舒白看著隨手涂畫的樣子,只微微皺眉,他把目轉向外面約簾而來的山水影跡,聲音依然平靜無波:“關于此案,就這麼點線索,若你要在十天破這個案子的話,關鍵在哪里?”
“既然找不到前幾次的線索和證,那麼最好的辦法,就是預測他下一次手的時間和地點,以及目標。”黃梓瑕頭也不抬,只著自己的手指,慢慢地掐算著。
“我也這樣想。所以,若你有把握的話,我可以給你幾天時間,和京城的捕快一起去調查此案——不過,你需要管好自己的頭發,不能再讓別人發現你是個子。”
“不需要。”黃梓瑕抬手輕輕了自己頭上的簪子,轉過臉看著他,神雖然依舊凝重,但的雙已經微微揚起,出自信而從容的一種弧度,“我已經知道兇手作案的依憑和原因,若我設想不錯的話,兇手只要敢出現,我就能找出他將會出現的地方。”
李舒白看有竹的模樣,微微一怔:“你已經有把握?”
“對,只需要王爺給我一本黃歷。”窗外輕風徐來,緩緩從簾外進,徐徐轉的日照進來,正籠罩在黃梓瑕的上,照得一明奪目,那雙如同清一般明凈清澈的眼睛,一瞬不瞬地盯著面前的李舒白,毫無猶疑。
李舒白一時恍惚,須臾才說:“好,那我拭目以待。”
猜你喜歡
-
完結399 章
醫妃驚華
她是二十一世紀資深醫學專家,卻穿越成落魄陪嫁公主。嫡姐僞善做作恨不能取她性命,便宜未婚夫溫和謙厚暗藏野心,還有一大堆豺狼虎豹,一個個恨不能將她剝皮抽骨。在夾縫中生存的她開始了鬥渣男鬥朝堂鬥江山的生活,好不容易把那所謂的婚姻擺脫掉,卻又被那孱弱腹黑的妖孽太子給盯上了。從此又開始了鬥心鬥情鬥天下的漫長道路。這是一羣驚才絕豔的男女在亂世裡譜寫的一段愛情與江山的博弈。
74萬字7.92 42249 -
完結800 章

娘娘她不想再努力了
花漫漫沒想到自己會穿進一篇宮鬥爽文裡麵,成了書中的炮灰女配。她試圖逆襲,卻發現隻要自己不按照劇情行事,就會心痛如刀絞。既然如此,那她乾脆就躺平當鹹魚吧!但讓人費解的是,那位以陰狠詭譎著稱的昭王殿下,為何總愛盯著她看?……昭王發現自己的耳朵似乎出了點問題。他隻要盯著某個人,就能聽到那人的心中所想。比如說現在,花漫漫哭得梨花帶雨:“能得到王爺的寵愛,真是妾身前世修來的福氣!”然而她心裡想的卻是——“艾瑪,今天這辣椒油有點兒帶勁!哭得我停都停不住。”……(1v1甜寵,雙潔,日更)
137.5萬字8 32392 -
完結5096 章

傲世邪妃:誤惹腹黑王爺
一朝穿越,重生異界!她是帝都豪門的千金。上流的名媛圈內皆傳,她是一朵高階的交際花,對男人,皆來者不拒。她發現自己患了一種致命的癌癥,在某一夜的大廈之上,她被曾經的情敵下了毒香,與情敵一起墜樓而亡。再次睜眼,她卻發現自己變成了王妃。還穿越到了一個玄幻的大陸!修鍊、靈氣、煉藥?
449.7萬字8 159802 -
完結259 章

權臣重生后只想搞事業
赫赫有名的野心家秦鹿穿越成寡婦,膝下還多了個兒子。 公婆不慈,妯娌刁鉆,母子倆活的豬狗不如。 面對如此慘狀,桀驁如她懶得與這群無賴糾纏,帶著兒子麻利分家。 天下格局晦暗,強權欺壓不斷,對于生活在現代社會的秦鹿來說是一種煎熬。 既然不喜,那就推翻這座腐朽江山,還天下百姓一片朗朗晴空。 ** 鎮壓朝堂三十年的權臣韓鏡一朝重生,還不等他伸展拳腳,就被母親帶著脫離苦海。 自此,想要重臨朝堂的韓相,一腳跨進了母親為他挖的深淵巨坑里。 畢生夢想是封侯拜相的韓鏡,在母親魔鬼般的低語中,朝著至尊之位,連滾帶爬停不下來。 ** 君臨天下后,娘倆的飯桌上突然多了一個人。 男人長的風流恣意,顛倒眾生。 帝王憋著好奇:給我找的后爹? 【穿越娘親,重生兒子。女主和原主是前世今生。】 【男主不知道有沒有,出現的可能會很晚。】 【女主野心家,能造作,不算良善卻有底線。】 【金手指粗大,理論上是爽文。】
90.4萬字8.18 6983 -
完結3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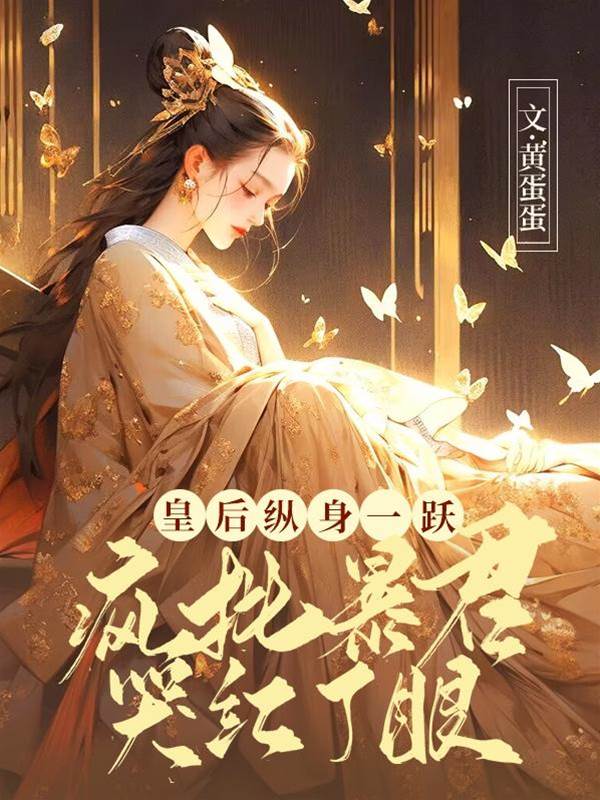
皇後縱身一躍,瘋批暴君哭紅了眼
【1v1,雙潔 宮鬥 爽文 追妻火葬場,女主人間清醒,所有人的白月光】孟棠是個溫婉大方的皇後,不爭不搶,一朵屹立在後宮的真白蓮,所有人都這麼覺得,暴君也這麼覺得。他納妃,她笑著恭喜並安排新妃侍寢。他送來補藥,她明知是避子藥卻乖順服下。他舊疾發作頭痛難忍,她用自己心頭血為引為他止痛。他問她:“你怎麼這麼好。”她麵上溫婉:“能為陛下分憂是臣妾榮幸。”直到叛軍攻城,她在城樓縱身一躍,以身殉城,平定叛亂。*刷滿暴君好感,孟棠死遁成功,功成身退。暴君抱著她的屍體,跪在地上哭紅了眼:“梓童,我錯了,你回來好不好?”孟棠看見這一幕,內心毫無波動,“虐嗎?我演的,真當世界上有那種無私奉獻不求回報的真白蓮啊。”
53.4萬字8.18 41760 -
完結267 章

盛京第一寵
大哥丰神俊朗,內心很毒很暴力;二哥風流紈絝,人稱盛京第一公子; 繼母雌雄莫辯,神出鬼沒;爹爹戰功赫赫,英勇威武; 身爲資深團寵,沈卿卿本該嬌寵一世。可一朝變故,沈家男兒無一倖存,她被心愛的表哥囚禁在深宮,生不如死。 沈卿卿臨死的那晚,宮裏漫天火光,叛軍逼城。她閉眼的最後關頭,看見了她的繼母……不!是變成了男子的繼母! 他手握滴着血的長劍,動作亦如往常的溫柔,熾熱的氣息在耳邊,“卿卿不怕。” 她的魂魄飄在皇宮上方,親眼看見“繼母”給她報仇,還當了皇帝。 一睜眼,沈卿卿回到了十三歲這年,繼母把她圈在臂彎,給她看話本子:“我們卿卿看懂了麼?” 沈卿卿:“……”
40.1萬字8 1366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