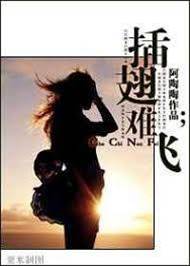《墜落春夜》 第21章
已經超過歷來所有人跟著他日子的總和。
但郁家澤已經漸漸不帶出席一些聚會,在當時的烏蔓看來,這是一種信號。
因此在朋友圈刷到他帶著別的小明星一起聚餐的照片時,烏蔓覺得這大概就是他提再見的方式。
把別墅里的東西清空,給郁家澤留了張紙條,好聚好散。
這中間他們幾個月都沒有再聯系,從外地拍完戲回來,忽然發現自己重新租的公寓被搬空了,只留下一張沙發。
郁家澤坐在空落落的房間里正在看書,空看了眼,說:“你這班飛機晚點了四十五分鐘,搬家公司已經把你的東西搬回去了。”
烏蔓的視線落在他拿著的書上,是一本《圣經》。他指節修長,單手就能將整本厚重的古典裝本拿在手心。
愣愣地放下行李:“您怎麼會在這里?”
“我的小鳥逃走了。”郁家澤將書攤在一邊,語氣溫:“我讓飛了幾個月,是時候該回籠了吧?”
烏蔓局促地垂下眼:“您不是帶了新的人去飯局嗎?”
他踱步到跟前,扣住下,迫使抬頭看他。
“那個人什麼名字我都忘了。”郁家澤呢喃,“這世界上可以有很多人,但我只養了一只獨一無二的小鳥。”
“您這個意思是說我不是人嗎?”
郁家澤怔了一下,爾后悶悶地笑起來,膛震地將向懷里。
Advertisement
“你總是這麼可。”他越抱越,“是不是不喜歡我還有別人?”
烏蔓沒有回答。
輕咬住:“沒有。我知道我們之間的關系,我沒有資格要求什麼。”
“小鳥真聰明。”郁家澤抱著輕晃,像哄孩子似的,“那你誠實地告訴我,你看到那張照片是不是心理不舒服。”
烏蔓把頭埋在郁家澤的膛間,很長很長的沉默后,郁家澤聽到一聲很低的嗯。
他彎起眼睛,更大幅度地彎下腰,蹭了蹭的腦袋。
“我不說結束,我們之間就沒有結束,懂嗎?”
沙發上的圣經被風反吹過去一頁,有句話被黑水筆劃了一道下線——
[耶路撒冷的眾子啊,我指著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囑咐你們,不要驚我親的,等自己愿。]
從那之后,烏蔓沒再聽聞或者目睹郁家澤和別的人糾纏。
或許他真沒再找別人,又或許他藏得更不聲不讓知道。
總之很多年,沒在郁家澤邊發現有別的人的痕跡。直到唐映雪出現。
但那又怎樣呢?這一天早晚會來的。
也許不用等電影上映,和郁家澤不清不楚的關系就會結束。反倒不用頭疼該怎麼向郁家澤解釋那些真槍實彈的吻戲。
好的。
烏蔓從回憶里,拍了拍臉,專注于下一場的拍攝。
這場是和鐘岳清的對手戲,在劇本的結尾段落,兩個人終于攤開天窗說亮話,鄧荔枝向徐龍發。
Advertisement
端著菜走向餐桌,鐘岳清吊兒郎當地坐著,在魚竿。
他斜眼了魚缸:“這條黑魚怎麼還在呢?”
烏蔓坐下:“也沒別的魚,禿禿的不好看,干脆就一直放著了。”
“那我明天去市場給你買幾條金魚吧。”
烏蔓低頭笑了笑:“都多久了,你才想起來魚缸是空的嗎?”
鐘岳清魚竿的手一頓。
“你不要就算了。”
“是我不想要嗎?”
“你怎麼回事?更年期提前了?”
“我是人,我有正常的七六。生氣就是更年期吵架,想做/就是如狼似虎不要臉?”
“……我們剛開始在一起的時候你不是這樣的。”
烏蔓在桌子底下用力摁住自己,聲問:“那我剛開始是怎麼樣的?”
鐘岳清懵了有一會兒,支吾說:“你很乖、很溫順、很可……”
烏蔓打斷他:“你不要再說了,那本就不是我。”
兩個人四目相對,一片沉默。
起喃喃:“我去喂魚。”
烏蔓走到魚缸邊,撒飼料的手不穩,倒出了好多。
“荔枝……”
沒有轉過,背對著攝像機,只能聽見緩慢的敘述和波的肩頭。
“阿龍,其實我很容易嫉妒,我也很沒有安全,我很你,但我從來都不敢跟你當面說這些,哪怕我們結婚這麼多年了。或者說,正是因為結婚這麼多年了,再提這些你會覺得我更矯。而當初我不說,是因為我只能偽裝這些表象去吸引你。”
Advertisement
鐘岳清驚愕過后,一聲嘆息:“你很久沒說過我了。”
“阿龍,我過你。”
鐘岳清著魚竿的手猛地收。
烏蔓放下飼料,轉過,平靜地看著他。
“所以我們就走到這里吧。”
他把魚竿暴躁地擲到一邊,摔兩截,痛道:“我不同意!”
“那你去洗浴會所的時候,有想過我會不同意嗎?”
鐘岳清整個人眼可見地發頹,剛才的氣勢然無存。好半天才找回語句。
“那只是找找刺激,男人不都是這樣。我的人是你,你早上醒過來的眼屎,吃飯時打的嗝,夏天的汗臭,冒時流的鼻涕,睡沉時流的口水,你的這些我都。但這些的前提,就是消磨我對你的。”
烏蔓笑了一下,接著笑出了眼淚。
“你直說惡心不就得了嗎?那為什麼當我上你的時候,我都覺得這些是可的。徐龍,我還以為你是著我的,是我錯了。”
掏出口袋里的一張離婚協議書,皺的,顯然是被一團丟掉又撿回來過。
“我已經簽好了。”放到桌上,“到你了。”
烏蔓直背脊,轉離去,沒有回一次頭。
“卡——”
汪城喊了停,烏蔓卻還恍惚地向走前,眼淚大顆大顆地往下掉。
最后撞在了一個人的懷里。
沒看清是誰,只是覺得這個懷抱的氣息讓人覺很安心。一不地窩著,任由眼淚在對方上。
Advertisement
“好了,阿姐,你要再哭。我幫你去揍一頓鐘岳清。”
鐘岳清跟上來冤:“蔓蔓你別再哭了,這樣搞得我真良心不安。”
追野出指腹掉的眼淚,烏蔓回過神,拂掉他的手站直。
“沒你的戲你來做什麼。”
可是還記得這小孩兒在上次拍攝里的逾矩。
“出戲了就這麼兇,剛才還那麼。”追野嘟囔,“當然是來看我的阿姐和男人分手,這麼爽的場面怎麼能錯過。”
鐘岳清玩笑道:“臭小鬼挖我墻角,得你!”
烏蔓低著頭眼淚,聽見追野在頭頂上方說:“你惹我阿姐哭,我可不就得搶過來。”
“……你們夠了。”無奈地打斷他們吵,重新抬起頭,越過追野,看見了攝影棚門口的郁家澤。
他手上拎著一個Lady M盒子的蛋糕,微笑地注視著棚。
猜你喜歡
-
完結7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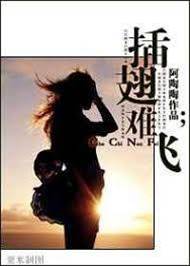
插翅難飛
美麗少女爲了逃脫人販的手心,不得不跟陰狠毒辣的陌生少年定下終生不離開他的魔鬼契約。 陰狠少年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女孩,卻不知道怎樣才能讓女孩全心全意的隻陪著他。 原本他只是一個瘋子,後來爲了她,他還成了一個傻子。
23.5萬字8 17235 -
完結658 章

名門寵婚之老公太放肆
他和她的關係可以這樣來形容,她之於他,是他最愛做的事。 而他之於她,是她最不愛做的事。 ……安城有兩樣鎮城之寶,御家的勢,連家的富。 名門權貴聯姻,艷羨多少世人。 連憶晨從沒想過,有天她會跟安城第一美男攀上關係。 「為什麼是我?」 她知道,他可以選擇的對象很多。 男人想了想,瀲灧唇角勾起的笑迷人,「第一眼看到你就想睡,第二眼就想一起生兒子」 她誤以為,他總會有一句真話。 ……一夕巨變,她痛失所有。 曾經許諾天長地久的男人,留給她的,只有轟動全城的滅頂醜聞。 她身上藏匿的那個秘密,牽連到幾大家族。 當她在另一個男人手心裏綻放,完美逆襲贏回傲視所有的資本。 ……如果所有的相遇都是別後重逢,那麼他能對她做的,只有不還手,不放手! 他說:「她就是我心尖上那塊肉,若是有人動了她,那我也活不了」 什麼是愛?他能給她的愛,有好的也有壞的,卻都是全部完整的他。
106.3萬字8 71276 -
完結235 章

追妻漫漫行長的心尖寵
【京城大佬 美女畫家】【雙潔】【追妻火葬場】 陸洛晚如凝脂般的肌膚,五官精致絕倫,眉如彎月,細長而濃密,微微上挑的眼角帶著幾分嫵媚,一雙眼眸猶如清澈的秋水,深邃而靈動。 但這樣的美人卻是陸家不為人知的養女,在她的大學畢業後,陸父經常帶著她參加各種商業聚會。 …… 在一年後的一次生日派對上,原本沒有交集的兩人,被硬生生地捆綁在了一起,三年漫長的婚姻生活中一點一點地消磨點了陸洛晚滿腔的熱情,深知他不愛她,甚至厭惡她,逐漸心灰意冷。 一係列的變故中,隨著陸父的去世,陸洛晚毫不猶豫地拿出離婚協議,離了婚……從此遠離了京城,遠離沈以謙。 後來,命運的齒輪讓他們再次相遇,隻不過陸洛晚早已心如止水。 而沈以謙看著她身邊層出不窮的追求者,則不淡定了,瞬間紅了眼。 在某日喝的酩酊爛醉的沈以謙,將她按在懷中,祈求著說:“晚晚,我們重新開始好不好?” —— 都說沈以謙風光霽月,聖潔不可高攀。 在兩人獨處時陸洛晚才發現,他要多壞有多壞,要多瘋就有多瘋。 他道德高尚,也斯文敗類。他是沈以謙,更是裙下臣
46萬字8 1579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