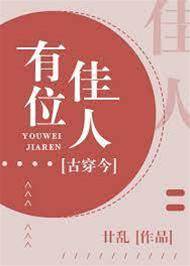《反派他過分美麗》 第49章
溫雪塵在二人背後凝許久,方才低聲歎道:“……殊途之人,何必要求同歸。”
徐行之固執地回他:“我偏要求一個同歸。”
待九枝燈經脈流轉平穩下來,徐行之去了一趟清靜君居住的浮名殿,和他對談了一個時辰。無人知道他們在此期間究竟說了些什麼。
隨後,徐行之將九枝燈從玉髓潭帶出,安置在自己殿中。
孟重已經從會場返回,見他抱九枝燈殿,角微,似是想說些什麼,但終究還是出乖巧的笑意來:“師兄回來啦。”
徐行之嗯了一聲,把九枝燈安放在自己與孟重共眠的榻上,替他掖被子。
孟重自從看到九枝燈被擱上那張床,眸便沉了下來。
徐行之在榻邊坐下,細細端詳著九枝燈的眉眼。
真是神奇,當初他一條胳膊就能抱起來扛在肩上的小孩兒,如今已長得這麼大了。
“師兄。”孟重在他背後他。
“何事?”
“九枝燈師兄倒下的時候,我就在他邊。”
徐行之聞言回過頭來。許是在玉髓潭邊呆得久了,霧氣眼,將他一雙烏的眼睛洗得細雨濛濛。
他問:“怎麼了?”
“九枝燈師兄是突然發作的。”孟重神很是複雜。他關注著徐行之的表,將抿上一抿,方才猶豫道,“師兄,據我所知,魔覺醒,總靈犀一念影響,絕非偶然。我想,九枝燈師兄該是在那時了什麼不該的心思,因此……”
徐行之打斷了他:“我知道了。”
對於徐行之這麼平淡的反應,孟重略有意外和不甘:“師兄難道不想知道?”
“聖人論跡不論心。”徐行之答道,“……論心無人是聖人。重,我且問你,你難道一生之中就從未過什麼不該的念頭?”
Advertisement
孟重不說話了。
不需孟重提醒,徐行之自然是知道這一點的。
但他永遠不會去問,在自己登臺時九枝燈了什麼心思,以至於心念異生,徒增業障。
或者說,不管九枝燈想了些什麼,都不該付出這樣慘烈的代價。
半日後,九枝燈醒了,隻字不語地倚在床畔。
徐行之只出去轉了一圈回來,屋子裏的銅鏡就被打碎了。
徐行之什麼也沒說,蹲下,把碎片一片片收拾起來。
九枝燈清冷中含有一抖的聲音自床榻方向傳來:“……師兄,抱歉。”
徐行之輕描淡寫地:“嗨,馬有失蹄,人有失手,有什麼的。”
九枝燈問道:“元嬰大典辦完了嗎?”
“嗯,辦完了。”徐行之回過來,殿外的自窗邊投,遍灑在他臉龐之上,晃得九枝燈有些睜不開眼睛,“……怎麼樣,師兄著禮服的模樣好不好看?”
此時的徐行之已經換回平日裝束,但九枝燈卻看得眼眶微微發熱。一熱氣兒在他眼窩裏衝撞,幾乎要他落下淚來。
師兄在元嬰大典之上著而立、帶當風的畫面像是被烙鐵燙在了他的雙眼之中。
他還記得清清楚楚,當時的自己著彩奪目的徐行之,第一次由心間最底氾濫出了一片腐爛的泥淖,翻滾著,囂著,它想要把徐行之拉他的之中,永遠不放他離去。
他是魔道後裔,此事已不可更改。但是,若他能回到魔道,奪位為魔道之主,將來把魔道與正道相合併,是否就能和師兄平起平坐了呢?
若他與師兄平起平坐後,能否在那時跟師兄相求,結為道呢?
或許是知其太過奪目而不可得,九枝燈放肆地想像著與師兄在一起後的一切可能。
Advertisement
他只是想一想,又有何罪呢?
……然而,誰他生而為魔。哪怕只是想上一想,便已是極大的罪愆。
九枝燈倚在枕上,自嘲地想,自己真是一個天大的笑話。
此時外頭陡然傳來一陣混,間或有“周公子”、“周公子你慢些”的聲,轉瞬間,腳步聲已到了屋外。
周北南一腳踹開了門:“徐行之!”
徐行之嘖了一聲:“投胎啊你。要是把門踹壞了,你得給我修好才能走。”
周北南一眼看到安歇在床的九枝燈,臉上青白之略褪,即將衝口而出的質問也被他強行咽了下去,噎得他直瞪眼:“……出來!”
徐行之把剩下的碎片打掃進簸箕裏:“就出就出。瞎喚什麼。”
九枝燈沉默地注視著徐行之的背影,一直到門扉掩上,他依然貪地注視著背影消失的地方。
把徐行之揪出殿后,周北南張口便質問道:“徐行之你怎麼回事?你逃了元嬰大典?”
“逃便逃了唄,這點小事還值得你周大公子千里迢迢跑來啊。”徐行之滿不在乎。
“小事你大爺啊!”周北南氣得腦仁疼,“應天川來風陵贈禮的禮告訴我說,九枝燈中途化魔,你竟然抱他當眾離去?你與他是何關係?”
徐行之無辜的:“師兄弟啊。不然呢。”
周北南一口氣:“我信,可旁人信嗎?那可不是單純的元嬰大典!是推舉你繼任下一任風陵之主的繼任典儀!你他媽說跑就跑,還帶著個魔道一起跑?你知道外面都在傳些什麼齷齪的東西嗎?”
徐行之笑嘻嘻的:“那是他們自己想得齷齪,關我何事。”
周北南被氣得一個倒仰:“你這一天天的就惹是生非吧!遲早你栽一回狠的就知道疼不疼了!”
Advertisement
說到此,外頭又有腳步聲傳來,不過這回的聲音斯文了許多。
有弟子的引薦聲傳來:“曲師兄,這邊。”
周北南神一振,跳將起來:“曲馳,快過來!”
朱素帶的曲馳從月亮門間踏。他額上生了一層薄汗,看來亦是得了消息後便馬不停蹄地趕來了。
曲馳看向徐行之,籠統問道:“……沒事吧。”
他既是問徐行之有沒有事,也是在問九枝燈有沒有事。
徐行之一言以蔽之:“沒事。”
曲馳呼出一口氣:“好,那就好。”
“不是……這就沒了?”周北南一口老憋在嚨裏,“曲馳,你年歲最大,倒是訓他兩句呀。”
曲馳行至近旁,緩聲道:“訓他又有何用呢。事已經做下了,不如想一想接下來該怎麼辦。”
三人在階前席地坐下,曲馳和徐行之之間夾著個氣呼呼的周北南。
周北南沒好氣地:“說吧說吧,你接下來怎麼打算?讓九枝燈留在風陵山?”
徐行之掰了梅枝,在地上無聊地寫寫畫畫:“不然呢?”
“也是。”周北南嘀咕,“廿載橫死,他那兩個兒子正狗咬狗的,熱鬧著呢。這姓九的小子在魔道裏沒基,挑著這個時間把他送回去,不是要他命呢嗎。”
曲馳卻有些懷疑:“但是魔道會放棄他嗎?今日之事鬧得太大,魔道那邊也該聽到風聲了,他脈覺醒一事是瞞不了的。萬一他兩個兄長認為九枝燈是威脅……”
周北南挑眉:“如何?他們敢殺來風陵山?”
“不會。”徐行之托腮沉,“四門與魔道止戰已久,小燈如果不願回去,他們也不會蠢到上門挑釁,自找死路。……曲馳和我擔心的是另一件事。”
Advertisement
言罷,二人對視一眼,異口同聲道:“……九枝燈的母親。”
周北南頓覺棘手:“也是。那可怎麼辦?”
“多年前我與曲馳去過一次魔道總壇,是去幫小燈送家書。”徐行之頭也不抬地用梅枝繪製著什麼,“待會兒我打算再去一回。”
周北南霍然起:“你要去搶人?徐行之,你——”
“說話怎麼這麼難聽。我是接小燈母親來與他團聚。”徐行之補充道,“……同時也是替小燈表明他不願參與爭鬥的心跡。到時候在風陵山下修一座草堂,讓小燈母親住在裏面,他們母子二人也能時時見面了。”
周北南:“……他們若是不肯給呢。”
徐行之面淡然:“哦,那就用搶的唄。”
周北南:“……”
徐行之手下作稍停,思忖了許久,他剛想問曲馳些什麼,曲馳便繞過周北南,接過徐行之手裏的梅枝,在沙地上續上了徐行之未能完的草圖:“……穿過明堂後,到這裏左轉。”
徐行之不無訝異:“你還記得啊。”
曲馳埋首道:“十數年前我隨你一起送信,去過石夫人的雲麓殿。我記尚可,你若是不很能記得路,我再跟你去一次便是。”
徐行之一把環住曲馳的脖子,嬉笑:“曲師兄,我真想親你一口。”
曲馳溫道:“別鬧。”
周北南瞪直了眼睛:“曲馳,你不怕罰?上次你跟他去魔道總壇,可是足足罰了三月閉……”
曲馳似乎並不把可能罰的事放在心上,寬容道:“無妨無妨。大不了這次被關上一年半載,我正好趁此機會專心參悟。等再出關時,修為說不準能趕上行之。”
曲馳向來如此,潤無聲,待人溫厚。也正因為此,四門首徒之中,威信最高之人既不是冰冷倨傲的溫雪塵,亦不是跳無常的徐行之,反倒是看似溫良平厚、無甚脾氣的曲馳。
周北南看著這兩人並肩謀劃,著實彆扭,不自覺地便探了子過去,聽他們議論,偶爾上一兩句。
幾人剛商量出來個所以然,便有一道聲音陡然橫了進來:“徐師兄。”
徐行之抬首,發現來人竟是徐平生。
徐平生淡然注視著他,禮節周到地揖了一揖,聲調平常道:“徐師兄,師父我來問,九枝燈是否在你這裏。”
徐行之頷首。
“那便請他到山門前的通天柱去吧。”徐平生道,“有一位名喚石屏風的夫人在通天柱下等他。”
不等徐行之反芻過來“石屏風”所為何人,他們後的殿門便轟然一聲朝兩邊打開了。
九枝燈一步搶出門檻:“來了嗎?”
徐平生被他赤瞳的模樣驚得倒退一步,方才皺眉答道:“沒錯。是石夫人。”
向來淡然事的九枝燈此時竟是難掩激之,急行幾步,但仍未忘禮節,朝曲馳與周北南各自深揖一記,又轉向徐行之,畔都在抖:“……師兄,我想去換一件服。”
徐行之回過神來,揮一揮手:“你去吧。”
待九枝燈和徐平生一齊告退之後,周北南才驚詫道:“……‘石夫人’?我們還未去,他母親倒先自己來了?”
曲馳自語道:“我怎麼覺得有些不對勁?”
徐行之一語未發,著面,抬步徑直往山門行去。
周北南忙縱躍起,追趕上了徐行之步伐,邊追邊回頭看向沒能來得及關閉的殿門。
——九枝燈方才在那裏聽了多久?
這念頭也只在周北南心裏轉上了片刻。很快他便釋然了。
……聽一聽也好,讓這魔道小子知道徐行之待他有多用心,以後專心守在徐行之邊,安安靜靜的別鬧事,那便是最好的了。
十幾年前,前往魔道總壇送信的徐行之也未能得見石屏風真容,只是隔著一層鴛鴦繡屏,影影綽綽地看了個虛影。
時隔十幾年,徐行之遙隔數十尺之距,終於見到了石屏風石夫人,九枝燈的母親。
一棵百年古鬆下,搖曳著一張仕圖似的人面。石夫人從態上便著一纖弱之,弱到彷彿一陣風吹來便能將帶走,生有小山眉,圓鼻頭,分開來看很,但卻很很地在一起,形態不錯的五偏生拼湊出了一苦相。
扶著樹幹,薄啟張,牙齒不住張地發著抖。
九枝燈換了一最新的風陵山常服,從上到下的配飾都取了最新最好的,幾乎是與徐行之前後腳來到山門。
猜你喜歡
-
完結132 章
你卻愛著一個傻逼
我深深地愛著你,你卻愛著一個傻逼, 傻逼他不愛你,你比傻逼還傻逼, 愛著愛著傻逼的你,我比你更傻逼, 簡單來說,本文講述一個,誰比誰更傻逼的故事。 簡隋英簡大少爺好男色的事情簡家上下無人不知, 連同父異母的弟弟簡隋林帶回家做客的同學也被他看上了。 可惜任簡大少明示暗示,那個叫李玉的男孩始終堅一臉正直的說,我不是同性戀。 開始抱著玩玩心態的簡大少屢次碰壁之後被激怒了,想要霸王硬上弓, 結果偷雞不成蝕把米,自己成了被攻的那個。 而原本無比厭惡簡隋英的李玉,卻在三番四次被挑釁繼而發生了關系後食髓知味, 對簡隋英的態度起了變化。而身為同父異母弟弟的簡隋林,對哥哥似乎也有著不同尋常的情愫…… 本文講述了一個直男被掰彎的血淚史,語言京味兒十足。 紈褲子弟簡隋英看似吊兒郎當的一副流氓樣惹人討厭,高幹子弟李玉則是一副清高又正直的樣子
35.2萬字8.18 21923 -
完結2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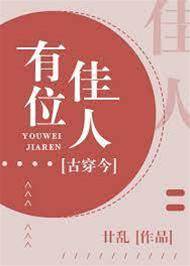
有位佳人[古穿今]
沈嶼晗是忠勇侯府嫡出的哥兒,擁有“京城第一哥兒”的美稱。 從小就按照當家主母的最高標準培養的他是京城哥兒中的最佳典範, 求娶他的男子更是每日都能從京城的東城排到西城,連老皇帝都差點將他納入后宮。 齊國內憂外患,國力逐年衰落,老皇帝一道聖旨派沈嶼晗去和親。 在和親的路上遇到了山匪,沈嶼晗不慎跌落馬車,再一睜開,他來到一個陌生的世界, 且再過幾天,他好像要跟人成親了,終究還是逃不過嫁人的命運。 - 單頎桓出生在復雜的豪門單家,兄弟姐妹眾多,他能力出眾,不到三十歲就是一家上市公司的CEO,是單家年輕一輩中的佼佼者。 因為他爸一個荒誕的夢,他們家必須選定一人娶一位不學無術,抽煙喝酒泡吧,在宴會上跟人爭風吃醋被推下泳池的敗家子,據說這人是他爸已故老友的唯一孫子。 經某神棍掐指一算後,在眾多兄弟中選定了單頎桓。 嗤。 婚後他必定冷落敗家子,不假辭色,讓對方知難而退。 - 新婚之夜,沈嶼晗緊張地站在單頎桓面前,準備替他解下西裝釦子。 十分抗拒他人親近的單頎桓想揮開他的手,但當他輕輕握住對方的手時,後者抬起頭。 沈嶼晗臉色微紅輕聲問他:“老公,要休息嗎?”這裡的人是這麼稱呼自己相公的吧? 被眼神乾淨的美人看著,單頎桓吸了口氣:“休息。”
49.8萬字8 8186 -
完結109 章
一頭母豬
沒事就愛“哭”。 母胎單身22年的元豐一直想找個女朋友 來大城市打拼6年了 他拒絕了小珍、小麗、花花、阿玲… 不是不想答應,而是因為他有個難以啟齒的秘密。 狗血俗套無腦.放飛自我瞎寫
23.2萬字8 15308 -
連載147 章

禁止套娃[無限]
過去的經歷讓溫時不再相信任何人。這個世上能信的只有自己。****溫時意外卷入了一場無限游戲。[恭喜玩家覺醒‘我就是我’技能。我就是我:耗費一百積分即可召喚平行世界的‘我’一次。]溫時漠然:“召喚來送死嗎?”直到——恐怖古堡之夜,古堡的主人要…
72.4萬字8.18 1152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