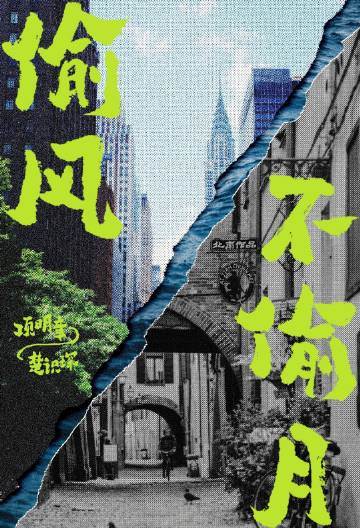《反派他過分美麗》 第99章
沒下過樓梯,從高下來向來是直通通地往下跳,現在鋪了一條好端端的路在面前,反倒不會走了,就像第一次下樓的小貓,踮著腳尖,謹慎地一步一挪。
誰都不會嘲笑這孩子稽的姿勢。
待雙腳重歸地面,徐行之問:“曲馳如何了?”
“乾爹安置下了。”
提及此,周默然了片刻。
回到現世之後,第一時間向夥計打聽有無見到一個秀氣病弱的男人。夥計是個年輕人,一邊好奇地打量短褐穿結如同野人的打扮,一邊大大咧咧地應道:“那門剛一打開我就給吵醒了,我以為這是啥兇像,就沒敢過去細看,躲櫃後一直盯著它呢。你說的那個人,第一個從裏頭出來的人已經向我打聽過了。我沒瞅見。”
周尚懷揣著一分希的心忽忽地沉了深潭之中。
Advertisement
現在衷心希曲馳就這麼一直安睡下去,不必醒來追問陶閑在何:“舅舅和舅娘在看顧他,徐師兄盡可放心。”
言罷,看遍小小茶樓,見門猶在,不問道:“孟大哥呢?”
徐行之語焉不詳:“他在找我們落下的重要之。”
來不及問徐行之口中的重要之所為何,周盯準了窗外,發出了一聲短促的驚。
徐行之循著的目去,只見沉澱著一灣濃墨的天際不知何時已消卻了手不見五指的模樣,正如向盛滿殘墨的硯中衝一清水,黑淡了,化作了悠悠流的態。
先衝破黑暗、披灑而下的是一道澄紅芒,落在對面畫樓琉璃瓦之上,隨即,紅潑潑灑灑地穿過雲層落下來了,積丘山,決昆侖,吞江海,頃,一染了金的圓日豁然跳出屋脊,其勢滔滔,擁攬天下。
Advertisement
“……那是什麼?”周在夢囈和。哪怕在最好的夢境裏,也從未見過如此勝景。
徐行之將手搭在肩膀之上,把推到了清朗的晨之下。
周起初有些恐懼,在暗之中索了太久,乍見到這渾圓的日頭,就像第一次見到怪的羊羔。但還是充滿勇氣地走了出去,仰頭視日,覺得眼睛灼痛,周卻奇異地溫暖了起來。
“……是日出。”徐行之沉聲道,“是現世的太,我們的太。”
猜你喜歡
-
完結140 章
三嫁鹹魚
林清羽十八歲那年嫁入侯門沖喜,成為病秧子小侯爺的男妻。新婚之夜,小侯爺懶洋洋地側躺在喜床上,說︰“美人,說實話我真不想宅鬥,隻想混吃等死,當一條鹹魚。”一年後,小侯爺病重,拉著林清羽的手嘆氣︰“老婆,我要涼了,但我覺得我還能繼續穿。為了日後你我好相認,我們定一個暗號吧。”小侯爺死後,林清羽做好了一輩子守寡的準備,不料隻守了小半年,戰功赫赫的大將軍居然登門提親了。林清羽
42.5萬字8 13571 -
完結126 章
禁宮男後
他百般折磨那個狗奴才,逼他扮作女子,雌伏身下,為的不過是給慘死的白月光報仇。一朝白月光歸來,誤會解開,他狠心踹開他,卻未曾想早已動心。當真相浮出水麵,他才得知狗奴才纔是他苦苦找尋的白月光。可這時,狗奴才身邊已有良人陪伴,還徹底忘了他……
27.3萬字8 6719 -
完結114 章

貌合神離
你有朱砂痣,我有白月光。陰鬱神經病金主攻 喬幸與金主溫長榮結婚四年。 四年裏,溫長榮喝得爛醉,喬幸去接,溫長榮摘了路邊的野花,喬幸去善後,若是溫長榮將野花帶到家裏來,喬幸還要把戰場打掃幹淨。 後來,溫長榮讓他搬出去住,喬幸亦毫無怨言照辦。 人人都說溫長榮真是養了條好狗,溫長榮不言全作默認,喬幸微笑點頭說謝謝誇獎。 所有人都以為他們會這樣走完一生,忽然有一天——溫長榮的朱砂痣回來了,喬幸的白月光也回來了。
32.8萬字8 9088 -
完結12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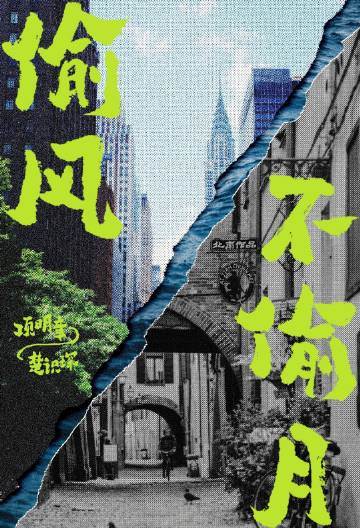
偷風不偷月
穿越(身穿),he,1v11945年春,沈若臻秘密送出最后一批抗幣,關閉復華銀行,卻在進行安全轉移時遭遇海難在徹底失去意識之前,他以為自己必死無疑……后來他聽見有人在身邊說話,貌似念了一對挽聯。沈若臻睜開眼躺在21世紀的高級病房,床邊立著一…
39.3萬字8 612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