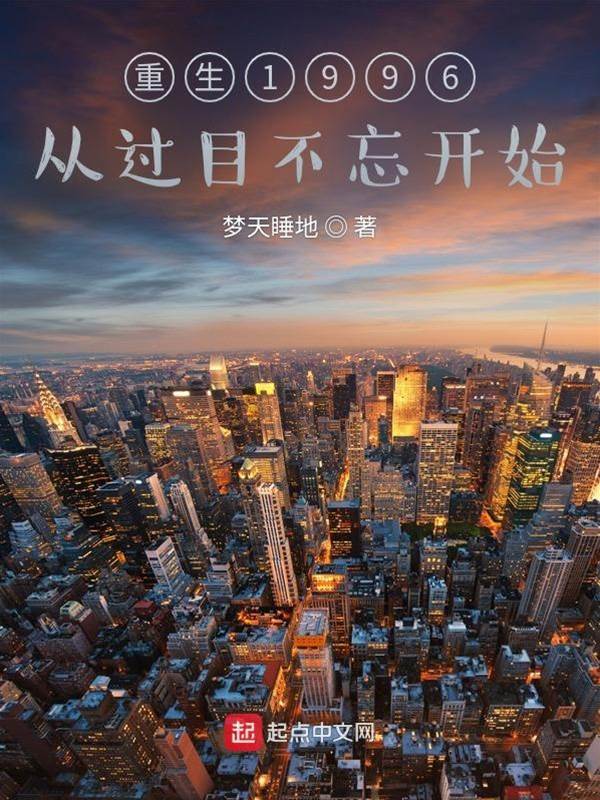《我和渣夫都重生了》 第635章 遲疑
而最可惡的是,坐在那個位置上的男人,為了一己之私,對遼城放棄的徹底,什麼作為都沒有。
這樣的人,這麼配呢。
原本隻是來瞭解事經過的,但聽了老李頭說的話,顧景璿覺得,當初接這個案子的員,也得好好查查了。
花兒娘是個兩鬢斑白的老婦,佝僂著腰,雙眼卻是幽深的讓人心跳加快,臉蒼白,邊跟著一個年的孩子。
「花兒娘,我們今天去城裡的時候,發現戴家夫人跟那個禍害都被抓了,府要大家去報案,」老李頭解釋道。
「他們是誰?」花兒娘沒有接老李頭的話,而是盯著門口站著,穿著錦的人,眼裡滿是戒備跟恨意。
誰家遭了這樣的災,能不恨呢。
時憫安到覺得自己同。
「他們是我在路上遇到的,他們想知道……」老李頭話還沒說完,花兒娘就變了臉,隨手抓起一木,砸向了眾人,然後怒吼一聲:「滾!」
Advertisement
顧景璿護著時憫安,倒退了幾步,避開了木的襲擊。
小九護著紅芍,其餘的人,都不用擔心。
「你們不許欺負我娘,」花兒的弟弟長開手臂,想要護著自己唯一的親人。
想到那麼滿的一家人,如今變這樣,時憫安心裡很不好。
戴峰仁,殺他十八次都不夠解恨的。
「我們沒有想要欺負你娘,我們是想給你爹,給你姐姐報仇,」時憫安半蹲著,著滿臉仇恨的小臉,很認真的說。
「嗬!」花兒娘冷笑一聲,摟著自己的兒子,諷刺說:「報仇,你們拿什麼去報仇,你們知道戴家在遼城,有多勢力嗎?」
已經不奢報仇,隻想著把兒子帶大,平平安安的,就夠了。
不想唯一的兒子出事。
「戴夫人跟兒子,是我讓抓的,」顧景璿著說。
老李頭驚呆了,著手指指著他,錯愕道:「你……你不是說,你不是當的嗎?」
Advertisement
「我是沒有當,但我有點勢力,」為了安人家,隻能這麼解釋。
花兒孃的眼裡閃過一驚喜,忙問:「你們能砍了戴峰仁嗎,他害的我男人,我閨,」
「我希能砍了他,但需要被害人的名字,時間,還有證據……」顧景璿一一說明。
這話,讓花兒娘猶豫了。
看著懷裡的兒子,遲疑著……
老李頭害怕會被牽連,表示自己忙,就先走了。
誰也沒攔著,他不是最重要的。
「這樣,我想知道,當初審這個案子的人,是誰,人家是不是包庇了戴家?」他換了個問題問。
花兒娘見他對這些追究著,深吸一口氣,鼓足了勇氣說:「人家那是為了救我!」
這答案,讓眾人錯愕不已。
「這話怎麼說的,我們可聽老李頭說了,你被打的很慘,」時憫安說。
怕人家還是沒弄清楚。
甚至都不知道人家到底什麼份,花兒娘見人家問的仔細,到底是心了。
Advertisement
有很多話,想要說一說的。
「我是捱打了,可府的人跟我說,我撼不了戴家,甚至還會牽連唯一的獨子,我不敢了,隻想著回家等死,至村裡人不會眼睜睜的看著我兒子死的,沒想到,當初提醒我的人,給我送了銀子,表示那是戴家賄賂他的,還讓我好好的活著,說是總有一天,能看到戴家敗落,」嘶啞著嗓子,說出了當年的。
猜你喜歡
-
完結1221 章

農女福妻有點嬌
孤兒姜荷重生了,有爹有娘,還附贈了小姐姐和嗷嗷待哺的弟弟。寶葫蘆在手,發家致富就是小意思,有田有錢還有家人,這日子美的不要不要的。她的田園生活,就少了個相公。某男幽幽的說:我不就是你相公?
206.3萬字8 203280 -
連載174 章

重生之嫡女不乖
前世,她太過懦弱、太過信任他人,被心上人和至親連手推入最難堪的境地,卻原來,所有的脈脈柔情和溫暖關懷,都不過是爲了她不菲的財産和那個不欲人知的秘密。 狠毒的舅母,將她生生毒死。 自黑暗之中醒來,她竟重生到了四年前, 那時,父母剛剛雙亡,她剛剛踏入伯爵府, 再一次,她站在了命運的轉折點前。 帶著濃濃恨意重生的她,化身爲一半佳人一半魔鬼的罌粟花,誓要向那些恣意踐踏她尊嚴的人,索回一切……
87.9萬字8 6567 -
完結78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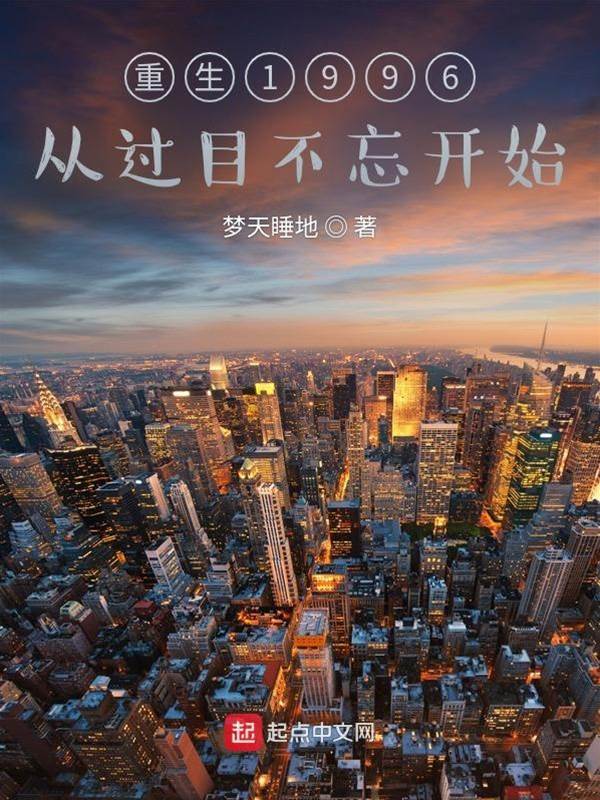
重生1996從過目不忘開始
一場車禍讓人到中年依舊一無所成的張瀟回到了1996年,回到了那個即將中考的日子。重活一生的張瀟不想再窩囊的活一輩子,開始努力奮斗,來彌補前世留下的無盡遺憾。
155.3萬字8 6186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