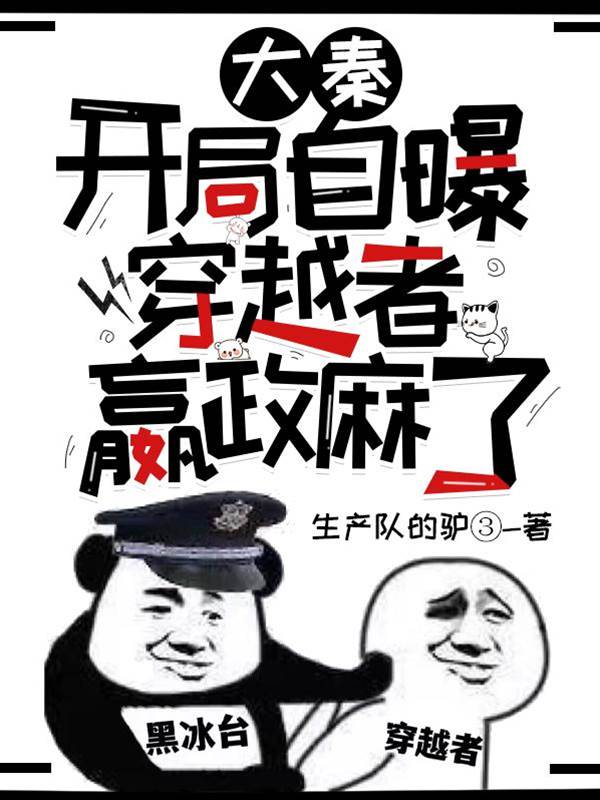《首輔為后:陛下,臣有罪!》 第二百九十八章 迎戰顧瑾
顧文君本沒有把心思放在顧瑾、顧瑜上。
正全心戒備著一旁的季誦遠,反而忽視了顧瑾與顧瑜之間的眼神流。
季誦遠笑了兩聲,眾人也便都一起附和著調笑緩和氣氛,反而沒有計較秦宸這近乎無禮的比較。顧文君心有所悟,看來這京城學坊,確實是事事都以季誦遠為首。
顧文君腦海里思緒轉得飛快,面上依然鎮定,不聲地轉移話題。
“好了,玩鬧到此為止,季公子,我們還是揭曉正題吧。”
單刀直,想立刻開始比試,免得夜長夢多。
可是季誦遠卻牢牢掌控局勢,睨笑著:“誒,不急!以公子相稱,還是過于生疏了。文君,我們年紀也相仿,不如直呼名字,你總不會看不上我,不愿把我當朋友吧?”
這一句。
便暴了季誦遠強勢心機,咄咄人的真實子。連“朋友”都要帶著三分迫,人就范,毫不給人拒絕的后路,不愧是“季”家子!
前有太后之死,后有貴妃之仇。
顧文君可一點也不想和季家搭上關系。
但是其他人卻都吃了一驚,季誦遠竟然會這麼給顧文君面子?為什麼?那顧文君不就是一個運氣好的貧酸書生嗎!
就算僥幸靠著幾次事件揚名了,又能如何。這當行事,出門在外,依然講究的是一個門第出。
顧家都不認顧文君的份,顧文君又算得什麼,就因為世不清不楚的,甚至連寒門都夠不上。
評述家門,最多就只能得一個“野”字,實屬難堪。
所以,哪怕是有別的算計,季誦遠這番姿態也給足了顧文君臉面了。哪怕是顧瑾,也沒資格和季誦遠稱兄道弟,他紅了眼,心里又氣又恨。
Advertisement
恨不得代替顧文君親自應下。
憑什麼!
直到反復回想那個心定制的計劃,確認應該沒有,顧瑾才勉強平下了妒意,坐住了子。
有人悄悄議論:“你們聽到了季誦遠說的了嗎?他該不會是認真的吧……”
也有人不屑:“顧文君畢竟是文山書院的首席,季誦遠為京城學坊的代表,禮節地問候試探罷了,你還當他真的會和顧文君朋友麼!”
“管他是真是假,如果我是顧文君,就應下來再說!反正能當季誦遠的朋友,可一點也不虧!”
……
不只是京城學坊的書生這樣想,就算是文山書院的,也全都羨慕極了。這可是戶部尚書之子季誦遠啊!太后的直系姻親,皇親貴胄,怎麼就讓顧文君給攀上了。
往后他日,只要搭著季誦遠的梯子,往上爬還不是指日可待!
與這前途大事一比,什麼比試都沒那麼重要了。
可這群羨慕不已的人卻不知道,顧文君不僅一丁半點都不想與這季誦遠結,甚至還要想盡辦法斗倒季誦遠背后的季家!
顧文君不愿鬧得不愉快,但是也不能怯場。
只能笑笑:“不敢當,我怎麼能和季公子平起平坐。”
心中警惕萬分,仍是推拒了。
圍坐了一圈的兩派書生們恨不得支起耳朵,事無巨細地探聽,結果就聽到這番拒絕。他們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
“什麼!”
立刻就有人倒一口冷氣,“顧文君竟然拒絕了季誦遠,他該不會是瘋了吧!”
“切,什麼才子,也就真是被捧上天,得意過頭了。這顧文君是傻了,還真以為被夸耀幾句,就能抵得過家門背景麼,真是愚蠢!”
Advertisement
“沒事,季誦遠很快就會讓這徒有虛名的小人清醒的,等著吧。”
季誦遠的笑意瞬息之間便收斂起來,連帶著整個學府的氛圍都起了變化。剛因為玩笑放松下來的書生們也紛紛張起來。
空氣微凝,僵化得猶如實質。
“啪!”季誦遠將手中的酒杯到桌上,發出清脆的聲響,酒水濺了出來,嚇得伺候左右的婢匍匐跪倒,低垂下頭瑟瑟發抖。
眾人的神更是一變再變。
季誦遠瞇了瞇眼,那雙狹長的眸子如蒼鷹般銳利明。
他啟道:“好!自然是比試,也不是來友稱道的,沒有平起平坐,那就干脆來一論高下!”
顧文君垂在一邊的手了,又再次松開。
差點以為,季誦遠要大發一通火氣。但是看來,季誦遠比想象中的,還要得住脾氣,城府很深。
顧文君不卑不地回禮:“文會自然是以文論長短,這是京城學坊提出的比試,不知道題目是什麼?”
季誦遠站了起來,將手背到后。
“每年都是比較詩詞六藝,實在無趣得很,不如這次,我們就來比作賦做文章,以口代筆,議論時事!”
顧文君突然預不妙,“哪件時事?”
“就是這近來京城最大的事,當然是楊衙令楊大人獲罪問斬了!聽聞朝廷上下對京衙連出錯十分不滿,有人提議,是選制度的問題。不知道——各位怎麼看?”
聞言,所有人的緒都被挑起來。
大家都是年輕書生,本來就一心向上,關注政治。
尤其是這關系到各自前途命運的選拔改制,自然熱響應。“好!這樣的文會才有意思吶。”
Advertisement
“如果真要變革,那確實該好好談討。”
唯有顧文君覺不好。
果然,師長能想到的事,季家也一樣能想到,他們已經開始未雨綢繆,為阻攔陛下改革選制度提前造勢了。
誰都知道,季家是太后的外戚。
要說哪一家了推舉選的最大利,必定是季家!
見神微妙,季誦遠向挑眉,“考慮得如何,可以讓你們先來。”
不懷好意!
顧文君謹慎勸誡:“書生議政是大忌,季公子,我們最好還是換一個比試題目。”
季誦遠張揚地一笑,越發俊:“哈哈哈哈,我們這群書生就是未來的朝廷棟梁!你太過張了,顧文君。如果你怕了,那就換我們京城學坊先!”
“文君!”秦宸走過來輕聲提醒,他暗中拉了拉顧文君的袖子:“這可是代表書院的比試,我們不能怯。”
不知道什麼時候,徐修言也站到顧文君后。
徐修言勸:“誰先說,就占了先機。最好別拱手讓給他們。”
顧文君想到顧瑾之前與他單獨談過話,看了徐修言一眼,沒有看出什麼不對。
但一時之間,白袍和青涇渭分明起來,重新分了互相對峙的兩列。
騎虎難下。
季誦遠是非要著開口,著這些書生們站隊。
顧文君正要說話,卻被顧瑾搶了先,“既然文君這麼猶豫不決,就讓我這個做兄長的先來吧,就當拋磚引了。”
呸他的這句“兄長”!
先要來一個顧瑜姐姐,再來一個顧瑾哥哥,顧文君真要被這對死纏爛打的雙生兄妹給惡心壞了。
見針,顧瑾倒是會找機會話,撿到了一個便宜。
Advertisement
“該死!又是顧瑾這個小人”秦宸眉目一沉,暗暗咒罵。
顧瑾看了一眼季誦遠,季誦遠點頭表示了許可。
然后顧瑾這才提氣,高聲道。
“在下以為,這是楊衙令自失責,獲罪是他自己的問題,與選制度反而沒有太大干系!
何況,這選制度是太祖時期便立下的,沿用多年沒有出過大的紕,足以證明其厲害,祖制怎可輕易更改。
從陛下到滿朝文武,都不會冒然老祖宗的規矩。想必,這改革也是不知道哪里傳出來的風言風語,必定是空來風。”
“糟糕!真顧瑾先把這話說完了。”秦宸聽得頭疼,“這些論據甩出來,還人怎麼反駁。”
徐修言也是臉不好。“這題目,哪一方先說了不改為好,哪一方就贏了。我們再回應,就只能說同意改制,可選制度這樣的大事,怎麼想也是不能改的!”
顧文君邊勾起一淡笑:“天底下,沒有什麼是永恒不變的。”
算是知道,季誦遠到底在打什麼主意了!
猜你喜歡
-
完結942 章
獨步逍遙
貪戀紅塵者,不求成仙,不求成佛。 隻求世間繁華,你我安好。 但若天地不仁,神佛貪婪。 我唯有怒而提劍,斬出一個浩瀚宇宙,可獨步之,逍遙諸天。 …
87.9萬字8 6523 -
連載11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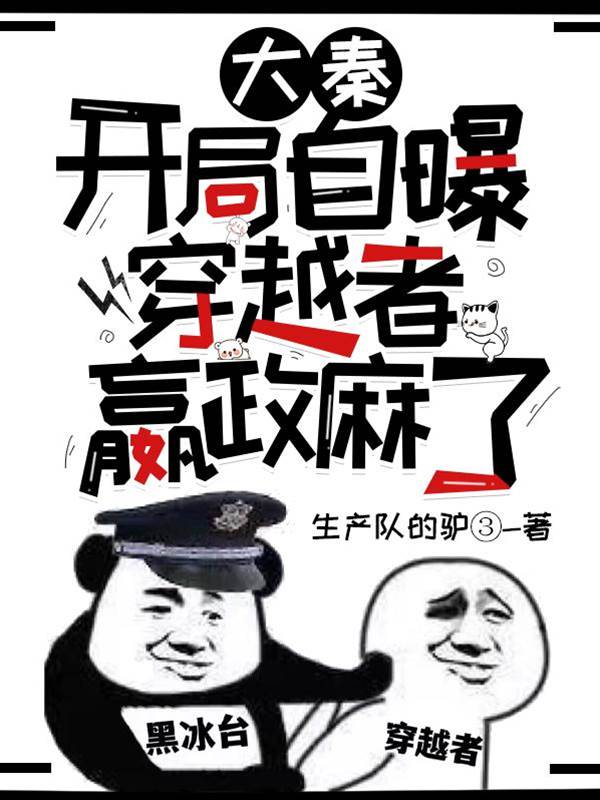
大秦:開局自曝穿越者,嬴政麻了
始皇帝三十二年。 千古一帝秦始皇第四次出巡,途经代郡左近。 闻听有豪强广聚钱粮,私铸刀兵,意图不轨,下令黑冰台派人彻查。 陈庆无奈之下,自曝穿越者身份,被刀剑架在脖子上押赴咸阳宫。 祖龙:寡人横扫六国,威加海内,尓安敢作乱犯上? 陈庆:陛下,我没想造反呀! 祖龙:那你积攒钱粮刀兵是为何? 陈庆:小民起码没想要造您的反。 祖龙:???你是说……不可能!就算没有寡人,还有扶苏! 陈庆:要是扶苏殿下没当皇帝呢? 祖龙:无论谁当这一国之君,大秦内有贤臣,外有良将,江山自然稳如泰山! 陈庆:要是您的贤臣和内侍勾结皇子造反呢? 祖龙:……谁干的?!我不管,只要是寡人的子孙在位,天下始终是大秦的! 陈庆:陛下,您的好大儿三年就把天下丢了。 祖龙:你你你……! 嬴政整个人都麻了!
247.2萬字8 916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