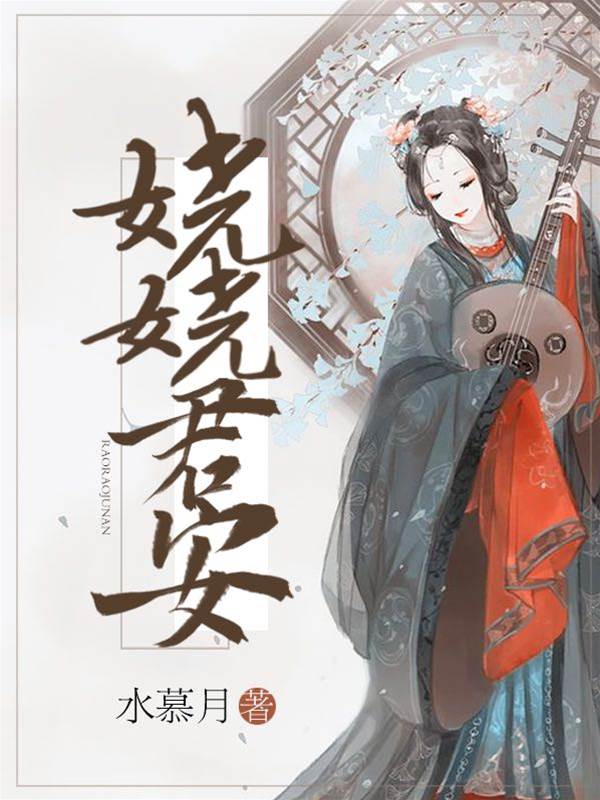《宮闈花》 第69章 東宮雙姝
握珠子的死死握,樓樾手上青筋暴起,面容再也平靜不了——
蘇流螢向他坦白的這些,竟是比方纔綠沫的消息更讓他震驚!
然而,不等他開口說什麼,南山已匆匆找了過來,說是他離席太久,慧帝已在問他了。
爲免讓人懷疑,樓樾心裡即便有再多的話,此刻也沒時間再同蘇流螢說,只是折飛快的朝承乾宮趕去。
樓樾走後,蘇流螢慢慢的地上爬起來,全冰寒,也沒了一力氣。
其實,方纔爲了免得樓樾擔心,心裡還有一個疑問沒有告訴他。
之前那名刺客頭領在臨死前告訴,真兇給過他畫像,指明要命。可是,如今陳妃死了,寧嬪也落馬,反而只有卻安然無恙……
想起樓樾方纔對說的話,驀然想到——
難道,這些日子以來,是樓樾一直派了影衛在暗中護著,所以才讓免遭了毒手?
除此之外,也想不出其他原因了,更不相信一心要死的真兇會突然放過。
承乾宮的宮宴還在繼續,燈火通明熱鬧非凡,耀眼的燈火幾乎照亮了半個皇宮。竹管樂的靡靡之聲遠遠的傳來,不絕於耳。
相比整個皇宮的熱鬧歡騰,蘇流螢無比的疲憊,從心到,都提不起一力氣來了,一個人沿著長長的宮道默默向前走著。
走到百花園的遊廊下,一團雪團掉落,砸在的上。
碎落的雪團掉進脖子冷得了子,擡頭警惕的看了四周一圈,卻一個人也沒看到。
見此,蘇流螢以爲是風吹落枝椏上的積雪掉到自己上,並不在意的繼續往前。然而,不等走出兩步,又一個雪團砸到了的後背上。
Advertisement
這一下,蘇流螢再也鎮定不了了,明顯覺到雪團的力量,不像是普通的積雪。
冷冷回,蘇流螢對空寂無人的百花園冷冷道:“誰在裝神弄鬼?”
一聲燦笑,高枝上人影一晃,下一刻,一個紫玉冠的玉面公子姿翩翩的落在面前。
面前的男子眉眼深邃,面容俊,特別是一雙桃花眼,看人時彷彿帶著三分笑意。而他此時勾脣帶笑看蘇流螢的樣子,一對桃花眼更是熠熠生輝,勾人心魂。
看著蘇流螢手足無措的樣子,紫公子勾脣笑道:“我說過咱們還會再見面。沒想到,這麼快就再見面了。”
此言一出,蘇流螢全一震,不敢相信的看著面前的紫公子,震驚道:“你……你是那日那個……”
面前之人,竟是那日將從龍圖閣救出來的鬼麪人!
驚得連退好幾步,不敢置信的看著他。
這段時間,林羽軍一直在捉拿那日闖宮進龍圖閣的刺客,沒想到他竟大搖大擺的再次出現在深宮裡。
看著神裡的張,紫公子得意笑道:“本公子的真容是不是比鬼面好看得多,是不是讓你意外驚喜了?!”
見他這般放肆大膽的曝出鬼面一事,蘇流螢反而鎮定下來。
看著他上華貴的裝扮,再看了眼承乾宮的方向,道:“公子也是來宮中赴宴的吧!公子到底是誰?”
此人不是大庸朝的人,卻能參加慧帝親設的宮宴,想必份不會簡單。
果然,他勾脣邪氣一笑,自負得意道:“名滿天下的第一男子蕭墨,就是本公子!”
聞言,蘇流螢又怔住了!
天下第一男的封號是蕭墨自負自封的,可他的另一層份卻是讓蘇流螢吃驚不已。
Advertisement
眼前這個風流倜儻,一臉不正經的人,竟是胡狄王惟一的兒子、胡狄國的太子殿下蕭墨!
心裡震驚不已,面上蘇流螢卻是按著禮數,恭敬的向他行禮請安,道:“奴婢見過殿下。”
蕭墨並不奇怪蘇流螢知道他的太子份,又是邪魅一笑,上前兩步靠近邊,低聲音道:“你知道這幾日本公子一直在想什麼嗎?”
他突然捱過來,溫熱的氣息往耳邊吹著,嚇得蘇流螢連忙向後面退開。
紅著臉,語氣帶著一慍意,“殿下是大庸的貴客,還是回去宴席上纔對……”
“你哪日在龍圖閣找什麼東西?找到了嗎?”
不等把話說完,蕭墨一臉認真的問道,好看的桃花眼饒有興趣的盯著看著。
得知蕭墨的真實份,再加上他乖張大膽的格,蘇流螢深他是一個危險人,那裡敢再與他走近,所以連話都不回他,道了聲告辭,直接退開逃離。
“我知道你是在找四年前你阿爹的案卷。可惜你沒找到。而本公子這兩日卻在龍圖閣裡找到了。”
後,蕭墨的聲音隨意慵懶,還帶著三分笑意,說出的話卻是瞬間讓蘇流螢停下了腳步。
震驚回頭,白著臉不敢思議的看著幾步開外笑得****無害的蕭墨,激到話都結了:“你……你真的……真的找到我阿爹的案卷了?!”
“騙你,本公子臉上長三天痘!”
胡狄太子蕭墨不但以俊著稱,也是出名的惜自己的容貌,所以,他此言一出,蘇流螢卻是信了。
但心裡尚有遲疑,不由狐疑道:“那****在龍圖閣都找過了,並沒有發現阿爹的案卷,殿下是如何找到的?”
Advertisement
蕭墨面上得意的笑著,桃花眼裡卻是閃過一不易察覺的寒芒,笑道:“小傻瓜,你只在一層找過,爲什麼沒想想,或許你爹的案卷被放置在別呢?”
此言一出,蘇流螢如夢初醒——
是啊,龍圖閣那麼大,阿爹的案卷或許被放置在了別,爲什麼的目就單一的侷限在慧十五年的案架上呢?
灰暗的眸裡閃過亮,蘇流螢激得子直哆嗦,迫不及待的對蕭墨道:“還請殿下帶奴婢去找到案卷!”
夜裡的龍圖閣比白日更加靜謐,守衛也越發的森嚴,特別是經過上次之事後,這裡更是加派了人手越發嚴謹的看守著。
可是,這些對蕭墨來說,都不是事。
他攜著,影如鬼魅般飄進了龍圖閣,再徑直的將帶上二樓。
龍閣圖的二樓,放著的是皇室檔以及皇室親宗的案卷。蘇流螢不明白蕭墨爲何將自己帶到這裡,不由回頭狐疑的看向蕭墨,心裡莫名的涌上不安。
風波流轉的桃花眼裡劃過寒冰,蕭墨手輕輕的彈了彈的額頭,邪魅笑道:“小傻瓜,本公子就是在這裡找到你阿爹的案卷的呀!”
在蘇流螢尚在驚詫阿爹的案卷爲什麼會被歸檔放到二樓的皇家檔案裡時,蕭墨已輕車路的去到南面的書架上找出蘇津的案卷,到了的手裡。
就著外面清亮的冷月,蘇流螢清晰的看到案卷上寫著阿爹名字。那一刻,蘇流螢激得頭腦裡一片空白,子戰慄不已,連呼吸都窒住了——
爲了這份宗卷,歷經千辛萬苦,不惜以犯險進到宮來……
而經過上次龍圖閣的空手而歸後,蘇流螢早已絕,對阿爹的案子也是不知從何下手,然後沒想到,已絕到放棄的案卷就這樣突兀的出現在了自己面前。
Advertisement
蕭墨拉著來到了最裡面背的角落裡,打亮上的火摺子幫照明。
螢螢火下,蘇流螢抖著雙手打開了案卷,瞪大眼睛朝案卷上看去!
然而,只是一眼,蘇流螢已是全劇烈一,手中的案卷拿不穩,從手中掉落下去……
蕭墨眼疾手快,瞬間出手撈住了往下掉的案卷,看著蘇流螢大驚失的形容,心裡不免也生出了好奇,眸忍不住朝案卷上看去。
只見偌大的一卷案卷上只有簡單四個字——
皇室聞!
蕭墨疑的看著臉慘白的蘇流螢,道:“你阿爹是皇室中人?”
怔怔的搖頭,蘇流螢腦裡一片混淆,卻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
爲什麼阿爹的案卷要放在二樓皇室檔裡?
爲什麼阿爹的案卷裡沒有關於四年前案子的詳細?
而皇室聞又是何意?
……
蘇流螢徹底迷濛了,以及那晚後來發生了什麼事全部忘記了,不知道蕭墨何時送回的司設局,也不知道他是何時離開的……
餘下的日子,天天呆在房間,腦裡子想的思的全是阿爹案卷上那四個字的意思。
可是,任如何想,也想不明白……
而在蘇流螢陷迷茫時,拿到佛珠的樓樾也是陷了苦思中。
宮宴結束後,在回府的馬裡,他已是迫不及待的拿出佛珠來看,依著蘇流螢所說,果真在佛珠的佛頭上看著了那個小小的‘瓊’字。
看著這個胡狄姓氏和寫法,樓樾眉頭越蹙越。
第二日,天不亮他就起程去了京郊的勿安堂。
想著他一晚沒睡都在看著那串佛珠,南山寬道:“爺,不用擔心,王妃也是胡狄人,又理佛數年,這串佛珠或許會給咱們提供線索。”
話雖這樣說,但一想起昨晚從宮裡回來後樓樾臉上繃的神,南山心裡莫名的心慌。
樓樾斂眸靠在車壁上,神裡難掩疲,冷冷問道:“四位影衛死前的所有行蹤可有查清楚?”
樓家派去保護刺客的四位影衛死得太過蹊蹺,樓樾也一直在追查此事。
之前他一直將眼放在天下能一息間解決八名高手的武林高手上,一直讓影衛在江湖殺手組織間尋找殺了四位影衛,瞬息間將刺客滅口的殺手,想依此找到幕後真兇的線索。
可查了這麼久,不論是江湖還是組織,本沒有可以一息間同時殺了八名頂級高手之人。
然而昨晚,樓樾在長信宮聽到寧嬪說起陳妃自殺之事後,腦子裡突然閃過了一個可怕的念頭——
難道,樓家的四位影衛也是自殺而亡?
閉上眸子,他一路都在細細回想四位影衛上的致命刀口,越想,卻是驚出了一冷汗。
南山爲難道:“爺,事過去有段日子了,關於影衛們私下的行蹤很難一時間查清,所以,只怕還要再等一等。”
一向沉靜的樓樾無端的心煩起來,吩咐馬伕:“再快些!”
車伕揚馬加鞭,一路急疾,半天的路竟是二個時辰就趕到了勿安堂。
勿安堂依山傍水,建在涼山蔽的山腳下。
這間白牆灰瓦的普通二進小院,安王妃在此一住就是數十年。
每次到這裡,看著母妃孤單的影,樓樾心裡都莫名的悲痛。
他不知道當年父王與母妃之間發生了何事,讓母妃決然的離開王府離開年的自己,一個人住進這孤寂的庵堂裡……
樓樾前幾日送昏迷的綠沫來過這裡,今日見到他又來了,安王妃以爲他是擔心綠沫,不由憐的拉過他寬厚的大手,笑道:“這麼冷的天,你不需天天跑來,那個姑娘爲娘會幫你好好照顧。”
點點頭,樓樾面凝重的對安王妃道:“母妃,孩子今日來找你,卻是有另一件想請你幫忙。”
見他神是難得的嚴肅認真,安王妃心裡一,道:“進屋再說吧!”
進到屋,安王妃親手給他倒了杯熱茶,待見他喝了才問道:“到底發生了何事?”
樓樾遲疑片刻,拿出了蘇流螢給他的佛珠放在了安王妃面前的桌面上,沉聲道:“母妃,孩兒想讓你幫我看看這串佛珠。”
有著暗紅麗花紋的紫檀佛珠靜靜的擱置在安王妃的面前。然而,只是一眼,安王妃卻是神微變!
猜你喜歡
-
完結1723 章
異瞳狂妃:邪帝,太兇猛!
她是21世紀第一殺手,一雙異瞳,傲視天穹。 一朝穿越,淪為將軍府廢材傻女,當這雙絕世異瞳在這世間重新睜開,風雲變幻,乾坤顛覆,天命逆改! 她手撕渣男,腳踩白蓮,坐擁神寵,掌控神器,秒天炸地,走上巔峰! 隻是…一個不小心,被一隻傲嬌又毒舌的妖孽纏上。 日日虐心(腹黑),夜夜虐身(強寵),虐完還要求負責? 做夢!
152.1萬字8 60795 -
完結1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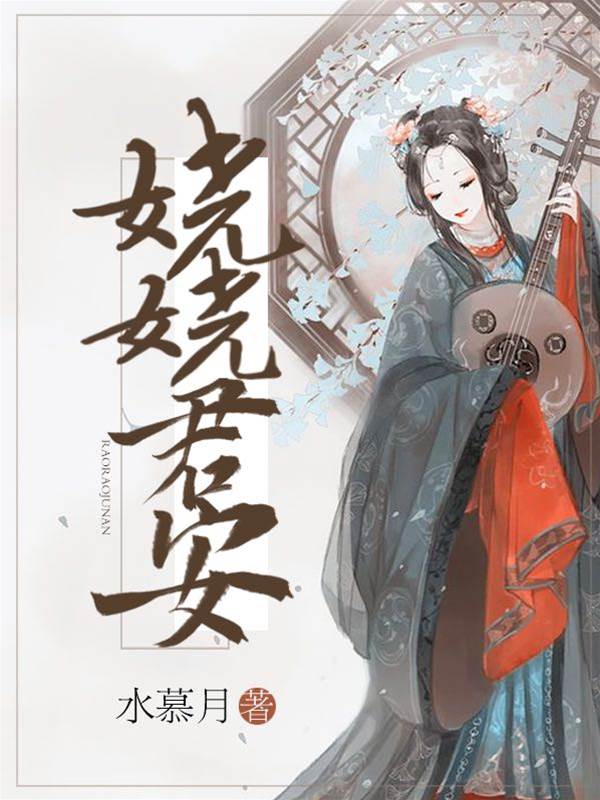
嬈嬈君安
原想著今生再無瓜葛,可那驚馬的剎那芳華間,一切又回到了起點,今生他耍了點小心機,在守護她的道路上,先插了隊,江山要,她也絕不放棄。說好的太子斷袖呢!怎麼動不動就要把自己撲倒?說好的太子殘暴呢!這整天獻溫情的又是誰?誰說東宮的鏡臺不好,那些美男子可賞心悅目了,什麼?東宮還可以在外麵開府,殿下求你了,臣妾可舍不得鏡臺了。
16.6萬字8 13911 -
完結368 章

誰敢打擾我搞事業
穿越而來的容凝一睜眼發現自己成了一個沖喜的新媳婦婆家花十文錢買了她回來沖喜,順便做牛做馬誰曾想,這喜沖的太大病入膏肓的新郎官連夜從床上爬起來跑了婆家要退錢,娘家不退錢容凝看著自己像踢皮球一般被踢來踢去恨得牙癢癢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容凝咬咬牙一個人去討生活好不容易混的風生水起,那個連夜跑了的混賬竟然回來了還想和她談談情,說說愛容凝豎了個中指「滾!老娘現在對男人沒興趣,只想搞事業!」某男人不知廉恥的抱著她:「真巧,我小名就叫事業!」
38.5萬字8.18 1417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